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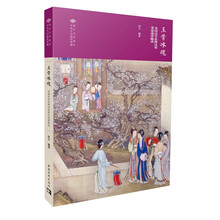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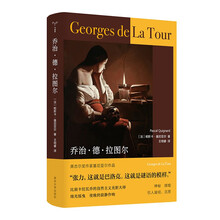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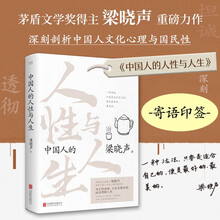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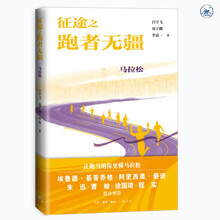


为撰写《迷信与暴力》一书,亨利·查尔斯·李从欧洲购买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和手稿等资料,现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亨利·查尔斯·李”分馆作为特殊藏品(special collection)珍藏。
作者旁征博引,记述了西欧各主要民族和国家的法律中对宣誓断讼、决斗断讼、神判断讼、刑讯逼供等各种古老司法程序的规定,并介绍了相关著名案例,同时对西方法学充斥着迷信和暴力的、不为人知的黑暗过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以往更加清晰地阐明一些渐趋消亡的旧俗和迷信的来源。
尽管作者已逝世一百多年,但作为历史和法学的重要参考书,《迷信与暴力》依然不断被再版和重印,其学术和文化价值可见一斑。
在人类摆脱野蛮蒙昧的过程中,日益崛起的理性力量与逐渐式微的凶残暴力霸权之间的斗争,可谓机锋处处。我们这一代自作聪明地嘲笑先辈的前后矛盾,其实,那正是人类螺旋式前进道路的一部分,犹如沉默的胜利奖杯般,应当得到尊重,这胜利几乎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依靠渐进方式取得的。因此,在黑暗时代,我们看到正义的实施竟要披着基督教化的迷信外衣、诉诸刀剑和运气的怪现象,但应当记住:相对于过去那种对暴力的普遍依赖,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蛮族部落被引向抽象正义,尽管道路曲折幽暗,却终能修成正果,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无论用何种方法,使强者向弱者屈膝,就已是对人性的伟大征服;而且,如果因人性弱点而必须借助迷信终结斗争,那么,当今天的我们坐享其成时,偏对这样的方式吹毛求疵,就未免有点儿无聊了。对于未开化的民族,就像对未受教育的人一样,感性强于理性,并且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于是,如果执着于保持不公的现状和凶暴掠夺的武士,能够接受用一场公平的战斗或神判来决断他的诉求,他就已经朝承认公平正义理念、放弃与人类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个人孤立迈出了一大步。正是通过这种间接方式,一个个逞强斗勇的个人被粘合起来,逐渐能够适应常设政府,并且形成了有组织的国家,开始珍视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抽象正义理念。从这样的视角看来,古老的程序形式褪去了它们荒谬的外衣,我们将其想作暴力、信仰和理性的不稳定聚合物,就如同对待瓦特的第一台简陋的发动机或者“克莱蒙特”号(Clermont)一样,当它在哈德逊湾跌跌撞撞地下水起航时——尽管确实笨重而粗糙,但是我们仍将其看作未来成功的宝贵雏形和先驱。
对于人类而言,将疑虑的重担赋予权位较高者,逃避作出决定和探索出路等困难的问题,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在刚果的偶像崇拜者与时常造访勒•诺尔芒小姐(Mlle. le Normant)沙龙的高雅的怀疑论者之间,尽管相距十万八千里,却可以通过这样共同的弱点而彼此相通;而且无论是试图追寻过去还是预测未来,其动力都是相同的。因此,在原始的“马勒姆”(部落司法会议)中,法官智慧的欠缺、证据的缺乏或双方证词势均力敌,都使判决变得非常困难,还有什么比诉诸更高权力者,并将问题推给神来做判决更加自然的做法呢?考虑到这种对抗类似战争的属性,诉诸战争之神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无论这个战神是被称为奥丁还是萨巴奥特(Sabaoth),他们在每一个案例中都特别眷顾无辜之人。在对正义的茫然索求之中,如此奇特的程序混搭,原始的巴伐利亚法律的规定可作为一个具体示例:一个人带着6名共誓人向法庭主张其对某一处产业的权利;而该处产业的占有者也有一位证人为其权利进行抗辩,且这位证人必是附近的一位地主。于是,权利主张者攻击证人的可靠性——“汝以谎言负我。我得以单打独斗,得神昭示,汝等誓言是真是假”;而且,根据决斗所决定的,既包括证人的诚实与否,也包括这片地产的权利归属。
在司法性决斗的讨论中,必须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决斗断讼是一种司法制度,而决斗的习惯则是一种几乎存在于各个种族和时代的普遍现象,两者之间有着很大区别。当荷拉斯兄弟(the Horatii)遇上库里亚斯(the Curiatii)兄弟,或者安东尼(Antony)剑挑屋大维(Octavius)以决定罗马统治权,抑或理查二世(Richard II)在1384年仗着年轻提议与对手查理六世(Charles VI)用一对一格斗结束由瓦卢瓦的腓力(Philippe de Valois)和爱德华三世发动的战争,或者古代印度人为避免战争屠戮,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这些都是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或者泄私愤的权宜之计。当亨利四世(Henri Quatre)时代的风流雅士,或者今时今日的火爆浪子,想用敌人的鲜血洗雪某种想象中的污点之时,就会进行决斗,它虽与司法性决斗更加相近,但也并非起源于此,而是源自所有古代部落普遍存在的一种私人报复权,以及封建时代绅士阶层独有的、与此相似的私人战争权。由来已久的要求“绅士式”的虚华方式,就这样既成了司法性决斗断讼这一习惯的目的,也成了其起源。私人战争(private war)的废止,刺激了决斗的兴盛,几乎与此同时,司法性决斗慢慢被废弃不用。两者此起彼伏,而且形式上近似,人们曾一度对它们的不同特性感到困惑,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要想给它们之间画一条界线并非难事:一个的目标是寻求报复,获得赔偿;另一个则是探查真相,公正执法。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位名叫约翰•范•阿克尔(John Van Arckel)的荷兰骑士,跟随布永的戈弗雷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当一些德意志武装加入这支部队后,一位蒂洛尔(Tyrolese)的贵族看到范•阿克尔的部队在他的帐前列阵,旗帜和自己部队的一样,遂下令将其扯下。这种侮辱不可容忍,但是受到伤害的骑士并未贸然寻求恢复荣誉。他将案件诉至十字军统帅们面前,寻求司法解决。一番调查之后,双方均证明了他们对同样旗帜披挂的世袭权利。为了解决冲突和互相矛盾的主张,法官们下令采取司法性决斗,范•阿克尔杀死了对方并夺取了他的盾,证明了自己对“银底两红杠”徽标的权利主张。为表达对神明的感激,范•阿克尔在巴勒斯坦八年间都扛着这样的旗帜。这不是一场拘泥于细枝末节的争吵,也不是一种反击侮辱的模式,而是一次对法律争端的审理,是那个年代别无选择时允许采用的方法。在西西里晚祷事件(the Sicilian Vespers)之后,诡计多端的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受到高歌猛进的对手阿拉贡的佩德罗一世(Pedro I of Aragon)的强力压制,并且急需时间镇压他半岛上的臣民发起的叛乱,于是他向唐•佩德罗(Don Pedro)派出一位先锋官,指控其恶意不宣而战。急躁的加泰罗尼亚人立刻中计,为了摆脱并非全无根据的指控,唐•佩德罗提出与指控者在决斗场(champ-clos)上碰面。双方都向福音书发誓,用战斗方式裁决这一指控,每方都集结了100人,来到当时尚在英王治下的中立地——波尔多。而这时,查理已经有足够时间腾出手来,轻而易举地设法阻止敌对双方会面。尽管实际上,这样的挑战与安东尼的几乎没有两样——它实质的代价是两西西里王国(the Two Sicilies)的王冠——其形式和目的依然属于司法性决斗,被告提出与控方亲身厮杀,以推翻对他的“不诚信”(mala fides)指控。同样如此的是,当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向查理五世(Charles V)挑战时,那无聊的虚张声势,并非想使半个欧洲免受战乱之灾,而仅仅是使他自己免受皇帝提出的背誓指控,并且这项指控证据确凿,因为法王确实违背了《马德里条约》。类似地,有一次同样披着司法决斗外衣的私斗,无论动机是否出于个人仇恨都可谓恶名昭彰,从而影响了骑士恶行的最后效仿者。这场有名的决斗,发生在1547年雅尔纳克(Jarnac)和拉•查斯泰那拉耶(La Chastaigneraye)之间,受到诚实的老布兰托姆(Brantöme)如此深切地悲悼,显示出两种决斗自始至终的差异。这次决斗举行了所有的司法仪式,并在亨利二世面前进行,它其实无关荣誉之事,而是使雅尔纳克能够摆脱对方的无耻指控。结果极其出人意料的是,拉•查斯泰那拉耶死去。而他是国王的宠臣,因此这位君王终止了所有合法化的决斗。但是非法的私斗不仅继续而且频繁出现,还史无前例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愈演愈烈——亨利四世(Henry IV)在22年的时间里颁发了不少于7000道特赦令,赦免违反王室敕令的决斗行为。这样一种获得“满足”的模式,与我们的时代精神如此大相径庭,以至于我们毫不稀奇地看到,它的拥护者努力使其归于古代的决斗裁断之列。尽管两者都是野蛮的遗迹,都无疑是从原始的习俗和习惯中演化而来的,却有着根本不同而又同时并存的制度;而且,无论多大程度上偶尔被暴力时代的激情混为一谈,它们其实目标各异,采用了不同的程序形式。在这里我们只须把决斗当作严格的司法程序,而不是去谈论那些为迎合当代人偏执喜好而大量涌现的奇闻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