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尝试理解经济危机的环境,我2009年开始动笔写这本书。从破产银行剥茧抽丝,扯出了宏观调控的政治失败,又转而导向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他的同事们赋予财产和自由的特殊意义。于是本书的关注焦点逐步转向了所有制。
19世纪的辉格党历史学家们将财产视为民主制度的基石,他们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认为,对生产工具的占有就是塑造社会和阶级意识的核心原动力,对于他们而言,所有制对历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如今的历史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种背景。连那些研究个人财产的遗赠和详细目录的律师,抑或消费经济和性政治的专家们,也极少在维护个人财产的需求的背景下审查他们的课题。在说英语的国家,资产的确吸引关注,个人拥有土地被毫无疑问地假定为先进社会的标志,而不是对于大多数人类而言都太陌生的奇怪变种。?
最终一切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变成了本书的焦点。我意识到这或许显得有些过时,甚至到了反常的程度。尽管如此,我替自己辩解的理由是主张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曾是以某种方式占有土地的强 烈愿望。虽然工业化已经取代了它的支配地位,但那只是近两个世纪的事情, 仅仅经过了短短几代人的时间,在某些经济体中,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多达 100亿的人口将使土地资源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我觉得这将迫使土地重新回归中心舞台。
不过集中关注土地所有制还带来了另一项优势。它把重点放在政治方面。从世界角度纵览历史的大多数尝试都优先考虑经济领域。举两个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干的例子:1966年出版的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的《独 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塑造现代世界的君主和农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t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和 2012 年出版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on Acemoglu)的《国家为什么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g :The Origins 0, P ooer,Prosperity and Povert),这两部作品都假定工业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应该是民主制度和国际地位的基础。这种分析不仅低估了前工业时代的制度的重要意义,而且不可避免地 将物质繁荣当成了文明社会的必要条件,用比尔?克林顿的话来概括政治策略,就是“这是经济问题,傻瓜”。但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成功的标准只能是它的成长。由于经济增长需要加速消费有限的自然资源,长期而言,那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然而如果你注意所有权的形式,视角就改变了。正如本书说明的,关于法律、权利和政治的问题至关重要,优先于经济。从这种角度来看,从什么对人类重要的问题中就可能提炼出不同的答案:“这是政治问题,傻瓜。”
换言之,我们有可以代替经济强加的单一的、最终行不通的可靠方法的选择。在世界各地和全部历史上,邻域已经以无数种方式获得成功。这完全取决于拥有土地的方式。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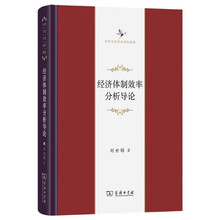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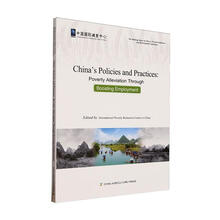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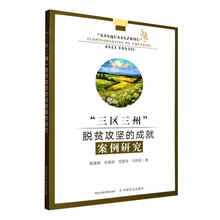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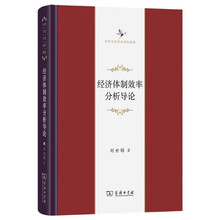






——玛格丽特·米切尔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佩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