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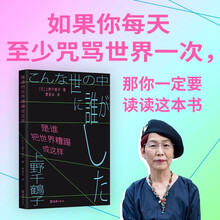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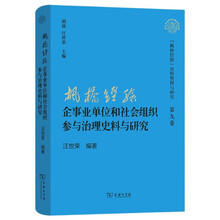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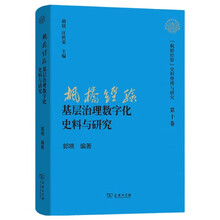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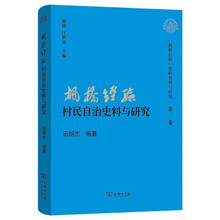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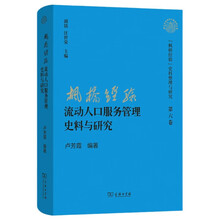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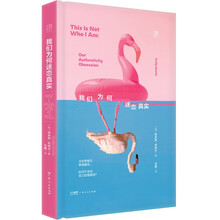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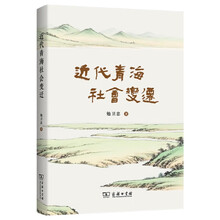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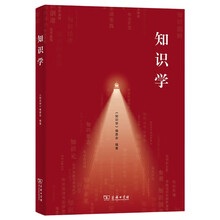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恰逢其时。
一个学科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与现实更迫切地呼唤“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政治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有待于实证研究的更好运用。就我本人而言,如果要说我是政治学出身的话,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身。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经典著作就是马列经典,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政治学著作可阅读。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学术训练,可以说,奠定了我以后独立思考并从事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
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服务的学术链接即是“政策科学真理化”的导向,它是政策人类学文化整体观视野下的继续发展与完善。政策人类学“整体性”逻辑在于其社会实践性、多元民主性与部分真理性的统一,即科学性-民主性-真理性的统一。在这一方面,它传承了政策科学的全部精髓与核心内涵,并突出地表现在政策科学的“元理论”及其“学科整体观”上。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Lasswell, H. D.)在1943年就倾向于“政策科学”的“元理论”学说。政策人类学毫无疑问首先在于突出“科学”价值,政策人类学从“内在问题导向性”出发,经由“参与观察性”“互为他者性”“公共利益性”,最终目标在于这一研究系统的“科学性”——即理论与事实相一致的“真理性”——反映了人类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实践真理检验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维,即“公共服务”的这一“科学”价值观。与此同时,政策人类学沿袭拉斯韦尔关于科学服务于民主的初衷,遵循为实现人的尊严的民主的学问的学科定位,始终坚定“民主”这一质的规定性;只有当公民们能够成为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的最后决策者与实施者,政策人类学才能实现经由民主政治与民主决策的民主化路径得以真正实现。
总之,政策人类学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部分的真理”——融合了“科学民族志”“象征民族志”“实验民族志”中的科学、诠释与民主等三种主要元素。政策人类学试图通过“科学”的检验,在多元民主实践活动中,来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实践真理、检验真理,政策人类学秉承的真理观,奠基于“实践”基础上,产生发展于“民主”参与的社会实践中,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活的运用与新的发展。
清光绪年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员在云南被杀。在当时的背景下,英国国力远胜于清王朝,要求清王朝派使臣前往英国谢罪。郭嵩焘就是这批使臣之一。郭嵩焘一行人从上海出发,乘英国游轮历经了两个月的海上颠簸到达了英国伦敦。这一路上,郭嵩焘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及与随行官员的讨论对话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到达伦敦后,他将这些文字记录整理后,写成了《使西纪程》一书。
自近代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的大门,伴随着商品的大量倾销,西方一些先进的思想文化也传入了中国。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包括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郭嵩焘也是其中之一。先进的思想家们通过言论、著作等方式让人们了解到清王朝之外的世界是如何的先进和文明,让人们认识到本我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样去解决。郭嵩焘带着这样的疑问,通过日记的形式,描写了前往英国一路上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对清朝的当权者提出了改革的建议——“正朝廷以正百官”。郭嵩焘对当时的现实政治颇为不满,他指出:“官贪吏暴,人民穷困,怨气日积,唯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治体制,国家方能有望复兴。”然而,在该书传回国内,郭嵩焘却被当时的士大夫、掌权者大骂为卖国贼,是何其可惜!
当今时代,社会科学蓬勃发展,而社会调查毫无疑问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至今社会调查依然很不规范,但是身为社会科学的分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及民族志的书写已经发展至写文化阶段,两者是严谨而规范的,具有科学性,不仅如此,民族志的通用性决定了它可与政治学等学科紧密结合,因此,各学科应该引进这一规范的调查方法。毫无疑问,政治学科更是需要这一方法进行田野调查,从实践中找出证据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政策人类学学科也就应运而生。结合政策科学和人类学两者的特性,我们认为,标准的政策人类学应具有以下五个特性,即内在问题导向性、参与观察性、互为他者性、利益公共性和政策科学性。本文就是从这五个特性的角度来简短地评述《使西纪程》一书的。
从问题导向性来说,这指的是内在问题的导向性,强调的是问题的本我性,研究者要进行自我反思,反思内在所存在的问题,对现象的根源有本质的理解和认识。这是进行政策人类学研究的第一标准。在《使西纪程》中对问题的内在进行反思,郭嵩焘认清了清王朝当时存在的内在问题。郭嵩焘一生坎坷,数次参加科举考试才中进士,在为官的数年之中,看透当时朝廷的腐败、贪污盛行,这促使他对朝堂政治进行反思。之后,郭嵩焘积极参加洋务运动,试图辅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靠武力换取天下的太平,但是却发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思想根本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后来得赴英国,历程则完全改变了郭嵩焘的政治思想,他对清王朝当时存在的问题有了内在本质的认识,主张朝廷改变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较早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先进士大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社会动荡不安,一些思想先进的政府官员开始意识到闭关锁国的错误,要求打开国家大门,与西方各国派遣使节进行友好往来而不是一味自高自大孤立于世界。郭嵩焘作为这些官员的佼佼者,意识到当时的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国力对比悬殊,于是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鸦片战争战败后,郭嵩焘致力于研究有关西方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的专著,认识到西方各国并非蛮夷之地,而是比清王朝从政治到文化都要远远先进的文明国家。郭嵩焘看到,当时的清王朝政治腐败、官吏残暴、人民穷困、怨气日积,唯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治体制,国家方能有望复兴。所以“洋患”问题该如何解决,遂成为郭嵩焘一生思考的核心。一国之发展,在于对本国国情的根本了解,对事物存在问题的本质认识。郭嵩焘先生通过出游各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发现除了大清帝国还有很多的文明国家,清王朝不仅不是世界的中心,并且已经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西方各国已迈向民主社会,制度先进。世界其他文明国家,法治社会、人人平等、启蒙思想盛行,自由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而纵观本国,落后愚昧,经济方面“重农抑商”;文化方面“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禁锢世人的思想。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才是真正落后于世界各国的原因。
从参与观察性方面来看,郭嵩焘在出使英国的过程中,一路以一个旁观者(叛逆者)的角度去观察西方的地理位置、邦交文化、政治制度等,记录下自己的所闻所感。他在英法两国两年多的时间内,不顾身弱年老,参观了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拜访了西方各界知名人士,阅读大量的报纸文献。郭嵩焘立足于这些事实,将自己的所闻所感详细记录,记叙了作为一名旁观者是如何由外而内地看待西方文明的。《使西纪程》记载了郭嵩焘从上海一路前往英国沿途的所见所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科学的民族志。在《使西纪程》一书中,郭嵩焘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深邃的目光和执着追求真知的精神,对沿途所经过亚洲五国、欧洲六国、非洲七国的自然地理、民族风情、宗教信仰以及设议会、制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均作了平实客观的详尽记叙,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详细描述了每天船行多久至何处,温度如何,到了何地地理位置如何,航线行程经过何地都有详细的描述。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船行中突遇风暴,郭嵩焘还记载了船员面对风暴是采取何种措施的。当时的清王朝,先进的文化不被待见,外国的宗教文化不予接受,只是一味沉浸在自己的儒家文化、程朱理学中而不能自拔。人们没有追求,没有理想,一味地遭人摆布,这也是一国思想文化贫穷的表现。郭嵩焘在英国期间,积极进行田野调查,不光对当地的监狱、学校,还对寺庙等进行考察,比较他们与当时清朝的不同,分析当时中国存在的弊端,找出根本问题,解决中国落后愚昧的局面。郭嵩焘通过了解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考察他们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然后详尽地记录下来,通过观察、参与其中,加入自己的感想,联系本国实际,服务于本国政治。这种注重实践,立足于“田野”的调查办法不仅在人类学中需要,在公共管理过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再说互为他者性。这一特性指的是在我们深入观察对方时,对方也在观察我们。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抱着民族多元化的心态,提倡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是不可以破坏别人的文化历史。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两种平等的文化主体,代表各自不同的文化符号,每一种文化都是由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塑造而成的,并没有优劣之分。主客体之间的互相尊重才能实现调查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田野调查是调查者观察的过程,也是调查者被当地居民观察的过程。观察者要通过观察别人对自我的看法来实现对自我的认识和定位。田野调查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交流的过程,两者在不断的碰撞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交流也使得彼此都感受到异文化的绚烂美妙。作者尊重各民族文化,从未破坏其文化,而是体验。这其中要有问题意识,带着问题研究他者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它特有的文化和符号来看待自己的问题,从中寻找它比较好的基因,变成自己的东西,来解决本我的问题。同样,研究是相互的,在郭嵩焘赴英过程中,各国人民也对清朝的政治制度、经济情况以及文化风俗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郭嵩焘批判清王朝在处理“夷务”举措上的不当,即在没有完全了解夷情的情况下,制定出有损百姓和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同时他还隐晦地指出为了使国家“自立”于世,“须先求解事者”,即要深入了解夷情夷务。郭嵩焘心怀国家社稷,因此可推断出他毅然出使英国的原因之一,即欲了解西方以寻求强国御侮之路。去他国的学习历程也体现了参与观察的特性,同时通过放下本国“天朝上国”的自负傲慢的心态,与他者进行平等的交流、沟通、学习,以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使“本我”(本国)发生质的飞跃,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另外,郭嵩焘在英国期间,对国外友人以礼相待,真挚相交,才得到国外友人的尊重和爱戴。当得知郭嵩焘先生回国在即,都纷纷前来告别,表示不舍之情与美好的祝愿。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到别的地方作调查,成功与否,是要看当调研结束之后,当地人对其评价。
从公共利益性这一点来看,为了深入了解、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教育体制,改变国内空疏、颓靡的旧式教育,提倡务实的新学风,郭嵩焘遍访英、法学校,重点考察其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设施和教学方法;又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报社,参加学会、科学研究报告会,观看科学实验,广泛接触教育界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郭嵩焘称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实学”,对其倍加赞叹:“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西洋机器,出鬼入神,其源皆自推算始也”“此邦格致之学,无奇不备,可以弥天地之憾矣”“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太西各国者”。反观中国学问和教育,其不切实用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于中国专以“时文小楷”取士制度痛加批判:“中国招收虚浮不根之弟子,习为诗文无实之言,高者顽犷,下者倾邪,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又说“学校之不修二千余年,流极败坏,以至于今”,“京师议论纷繁,其源皆由于无学”。为此,他积极倡导实学。所以作者建议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实现君民共治的和谐社会。同时,作者强调了重商主义政策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增强国力的巨大作用,人民经商不仅能帮助扩展及治理其殖民地,还能增加赋税。为了贸易的便利,必须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比如汽轮车、电报等,可以看出郭嵩焘是想从政治体制上对国家进行根本的改变,他的利益出发点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的,是出于利益公共性这个角度的。所以我们说,《使西纪程》一书极具利益公共性。通观《使西纪程》一书,郭嵩焘提出和表达的观点主要为: 西洋也有千年文明,并不是长久观点以来愚昧夷狄,这是无知的表现;西洋“政教”优于中国,而其人民与国家同其利病,故国运长久,这是其强盛之本;国家要强盛,第一要务是要改革政治制度,建立起类似于西方的政治体制,设议会改宪法;显然,依旧实行闭关锁国将西方各国拒之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的,必须对外开放,学习其立国之本,富强之术;对于西方的挑战,不能一味主战,也不能一味求和,而应该讲究应对的方法。所有这些,都是郭嵩焘忠肝义胆的肺腑之言,无不体现他浸淫于洋务几十年的远见卓识,其忧深思远之怀,力透纸背。
最后谈谈决策科学性。郭嵩焘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办理洋务、杜绝洋患也应从这一根本入手。郭嵩焘的这一论断,历史业已证明他是非常正确的。从具体举措上来讲,郭嵩焘主张扶植商贾,让他们去向洋人学习发展工商业,他认为,西洋政教优于中国。只有民主之国才能强盛。要敞开大门,学习夷狄立国之本,强兵富国之术,尚学求艺之方。西洋人才辈出,在于其教育。西洋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虽然不足为师道,但较之中国还要好一些。西洋诸国通过革新国家制度,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其中英国与俄罗斯已经对中国形成了战略包围圈,随时可能灭亡中国。但中国统治者还沉浸在“华夷有别”的观念之中而无法自拔,这种盲目骄傲的观点蒙蔽了中国人的双眼,阻碍了中国人对西方各国国力的理性认识,同时,也淡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让清王朝对于中国已被世界发展潮流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的事实视而不见且故步自封。同时作者也指出西洋诸国是通过不断地发展才达到现在的程度,因此中国政府也应该有发奋图强的心态,制定科学的、符合国情的政策实现国家的富强。
郭嵩焘的这本《使西纪程》具备了问题导向性、参与观察性、互为他者性、利益公共性、决策科学性这五个特点,可以说是经过科学调查和客观的民族志书写的人类学家的工作,并且能够为当时清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毫无疑问是值得政策人类学学者推崇的。
关键词: 民主制度重商主义夷情夷务西方实学体制变革一、 《使西纪程》概述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陷入了悲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但是,幸运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侵略并没有把中国人打倒,反而却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时代的主旋律。”(郭嵩焘,1994:“中国启蒙思想文库”总序1)清光绪年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员在云南被杀。在当时的背景下,英国国力远胜于清王朝,要求清王朝派使臣前往英国谢罪。郭嵩焘就是这批使臣之一。郭嵩焘一行人从上海出发,乘英国游轮历经了两个月的海上颠簸到达了英国伦敦。这一路上,郭嵩焘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及与随行官员的讨论对话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到达伦敦后,他将这些文字记录整理后,写成了《使西纪程》一书。
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的时期也是“门户开放”“西学东渐”的时期,也正是这个时期,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抱着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利于变革的观点;另一方面参照当时所了解的西方情况提出一些革新的方案。当时梁启超、章太炎通过日本译籍而了解西学,严复则直接介绍了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学说。他的《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当时风靡一时。孙中山则直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根据国情加以改措,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不管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之后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果都失败了,但是它们都曾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引起了人们的思索。而郭嵩焘正是清政府派往英国的首任公使,在近代中国漂洋过海、走向世界的先进士大夫中,他是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一位。
先进的思想家们通过言论、著作等方式让人们了解到清王朝之外的世界是如何的先进与文明,让人们认识到本我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样去解决。郭嵩焘带着这样的疑问,通过日记的形式,描写了前往英国一路上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并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对清朝的当权者提出了改革的建议——“正朝廷以正百官”。然而在本书传回国内,郭嵩焘却被当时的士大夫、掌权者大骂为卖国贼,是何其可惜!诚然,也有人欣赏他的魄力与眼光的独到性,在《使西纪程》寄回后,李鸿章得以先睹为快,并大加称赞道:“总署钞寄行海日记一本,循览再四,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及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界也”(李鸿章,1973: 1268)。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同上: 1283)但是,像李鸿章这样的挚友,或者说像这样思想进步的人又有多少?当时的清王朝,思想禁锢、愚昧落后,并不是郭嵩焘的一本书就可以解放的。这本薄薄的一册小书,看起来普通至极,然而放在那个时代,可谓是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了。郭嵩焘在100年前看到的问题,放在今天依然适用。
特别是,郭嵩焘对当时的现实政治颇为不满,他指出:“官贪吏暴,人民穷困,怨气日积,唯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政治体制,国家方能有望复兴。”(郭嵩焘,1994: 3)而曾、刘包括后来的李鸿章虽然也知道当时的现实政治弊端丛生,但并不认为已到了非彻底变革不可的程度,而是希望在不变革当时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尽自之力,以图中兴。郭嵩焘基于自己浸淫多年洋务的经验,认识到国家的强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纯依靠军事不可能实现自强的目的。早在1875年的《条陈海防事宜》中,郭嵩焘就对西方富强的原因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同上)认为西方的强盛不仅仅是依赖军事力量上的优势,更其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故而主张“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郭嵩焘,1994: 93)。但在当时,能察觉到这点的中国人非常少。
二、 从“五性”理论分析当今时代,社会科学蓬勃发展,而社会调查毫无疑问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至今社会调查依然很不规范,但是身为社会科学的分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及民族志的书写已经发展至写文化阶段,两者是严谨而规范的,具有科学性,不仅如此,民族志的通用性决定了它可与政治学等学科紧密结合,因此,各学科应该引进这一规范的调查方法。毫无疑问,政治学科更是需要这一方法进行田野调查,从实践中找出证据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政策人类学学科也就应运而生。
结合政策科学和人类学两者的特性,我们认为,标准的政策人类学应具有以下五个特性,即问题导向性、参与观察性、互为他者性、利益公共性和政策科学性。
……
迈向公共治理的政策人类学(代序)
/周大鸣
1椒江“常任制”改革的文化政治自觉
/陶庆顾小倩
2《利玛窦中国札记》简评
——基于政策人类学“五性”分析角度
/陈检豪张科甲
3《使西纪程》简评
——基于政策人类学“五性”分析角度
/张亦鸣徐如飞
4用“五性统一”解读《使民主运转起来》
/鲍玉兴于澍原
5政策人类学中的“生成性”政治
——以《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为例
/尹军力耿浩雪1506“霍桑实验”里的政策人类学
——基于“五性”分析《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杨蕾陈津京
摘要(英文)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