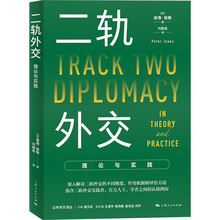二、 与一个有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超级大国相处
尽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但是在冷战后,尤其是“9·11”后的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这个当今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或者说反而变成了,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 冷战后美国的行为无疑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更为一致,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1992—1994年的《防务政策指导》(Defense Policy Guidance)读起来简直就像一部直接取自进攻性现实主义教材的教义。在这个文件里,迪克·切尼(Dick Cheney)、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以及他们的同事在这份《防务政策指导》里直言,美国的目标是,借助预防性手段——如果不是预防性战争的话——保持它的绝对优势,阻止其他国家崛起,从而延长单极的时间。 很显然,预防性战争的信条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标志(Mearsheimer 2001;Tang 2008a)。
其次,尽管历经多届政府,冷战后美国的军事行为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上文提及的切尼-沃尔福威茨的《防务政策指导》。相对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国防开支非但没有被大规模地削减,反而事实上还在不断增加。 随着北约东扩以及美国军事存在在全球范围的扩展,美国的势力范围非但没有缩减,反而已经进一步扩大(Johnson 2004)。
再次,可能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是,“9·11”后,美国政府不仅在“布什主义”中明确了预防性战争的理念【布什政府故意误导性地用“先发制人式战争”一词替换了“预防性战争”一词】,而且实际发动了一场针对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布什主义”明确支持预防性战争,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
最后,美国还通过武力推进民主输出的目标。毫无疑问,当一个国家决意以武力向外输出意识形态时,它就与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征服和荣誉的“疯狂恺撒”没有什么区别了。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说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Wolfers 1952,492)。
总之,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尤其在小布什以及支持他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掌权时期,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式的、“革命性的”国家,或者说就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Ikenberry 2002;Jervis 2003;2006;Hendrickson 2002;Cox 2004;Layne 2006b;Nelson 2005;Offner 2005;Prestowitz 2003)。 可能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尽管美国在遭遇重大的军事失利(例如伊拉克战争)之后有可能会有所收敛,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压倒性的权力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依然有可能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
由于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是这个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角色(亦即霸权国或者半霸权国),因此美国仍将有可能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这一现实对于体系内其他那些试图寻求安全的国家(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单极世界中,通过军事途径与唯一的超级大国进行直接对抗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然而,主要的地区性大国(及其他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可以设法建立一个“制约轴心”,以制约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美国将几乎不可避免地需要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某些支持,因此这些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告知美国,它的一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反过来损害到美国自己的利益。
不过,其他国家毕竟不可能在军事上制衡美国,因此最终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自己汲取教训,意识到作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再有好处,而成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才是正途。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美国真的成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那么在外部制约不再如两极结构那样强大的情况下,美国安全战略的基本指导原则就应该是自我克制(例如,Nye 2001,xii,1617,2526;Taliaferro 20002001,159160;Jervis 2006;Walt 2005)。
为此,对于美国的那些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其他非进攻性现实主义阵营中的学者和舆论制造者来说,他们正面临着一个“令人羡慕”的任务:他们不仅需要揭露在这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的谬误,还需要展示在这个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采取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他们以一种更为有力的和更为持久的方式接触美国公众和精英,以改变政策的进程。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应该对这一任务持欢迎的态度。毕竟,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对国际政治进行理论化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以“现实”的方式所从事的国际政治的实践。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