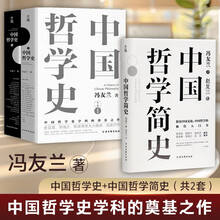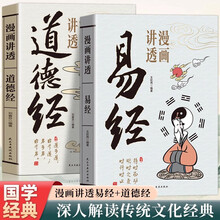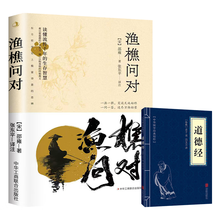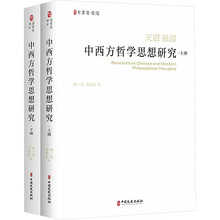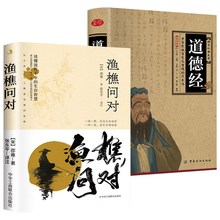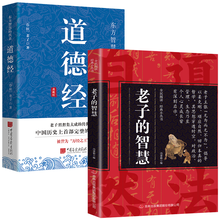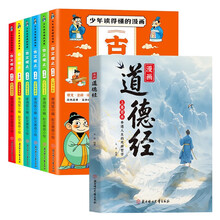《几与时: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学范式的反思与转化》:
换言之,于船山,儒家圣人、君子的内圣之学如果不借助于趋时之外王,那也就不可能于凡民之中获得普遍性。这在宋代理学中似乎不成其为一个需要特别强调与分殊的问题,譬如,在余英时先生眼中,“内圣外王”之主体本身就是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但宋代道学与船山所面对的道学在明末的民间化情况是不同的。从思想史上看,由宋初直至明末,整个道学运动应该是越来越从士大夫阶层趋向于整个社会与所有阶层之民众的。而要趋向于普通民众、贩夫走卒,则宗教化或者使用宗教的方式来传播思想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之一。根据吴震先生的研究,至明代中后期,作为道学的一个主要部分的心学甚至有与民间宗教结合而形成“劝善运动”的趋向。由此“人人皆可为尧舜”这个命题真正发展为“满街皆是圣人”的情况,而这正是船山所面临的“时”。所以,船山必然需要强调圣人与凡民之间的差别的先天性,其具体表现就是研几工夫的非普遍性与圣人专属的趋时工夫。上述分殊意味着,对于具有圣人之质的人来说,由研几而至趋时的内圣外王的工夫之成就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在另一方面,不具圣人之质的人则完全不可能承当趋时工夫而使自己成其为圣人。与道学由宋至明不断地普及化与民间化的方向不同,在此,船山的趋时与研几工夫指向一种人性论上的分殊与精英主义取向,这使得整个船山哲学都变得非常繁复与深奥,因为其本身的基础就是为君子谋之《易>。在船山看来,道德普遍性实际上必须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佛老对道学的影响。
就道学传统上说,“人人皆可为尧舜”这个命题一般被理解为:人人其实都有如尧舜那样成就其性的可能,只要他通过一定的工夫把握内在天赋之良知之性,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于船山,上述诠释其实缺乏一个变量,那就是“时”。所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话应该被理解为:在圣人趋时明道的前提下,只要人人能率性而繇之,则人人都有如尧舜那样成就其性的可能。这里,我们显然有必要去问,这个“趋时”之“时”究竟是什么?
在前文的分析中,船山将“时”的基本定义为爻位由初于上的基本次序,从根本上说,就是永远变动不息阴阳二气之神化的说展开的具体的显隐之几的基本次序。这意味着,于船山,传统意义上的单纯之内圣工夫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地在理论上使得每个人成就道德,因为成德不仅需要内在心性工夫上的超越,还需要圣人所定下的外在趋时之序。简言之,传统心性论的基本逻辑是:只要每个人都从内在心性上下功夫去成就道德,则自然会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天赋之良心,所以每个人都从内在心性上下功夫去成就道德就是完全可能的。而在船山看来,因为世间万物都是随着神化日新的,因此,我们显然必须考虑每个人在神化中所处的具体时空境遇,正如在易学上某爻之吉凶取决于其所处之具体时位一样,这与内在心性工夫一样都是成德的必要条件。同时,因为个人的禀赋气质之清浊不同,所以尽管每个人都禀赋着仁义之潜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自觉到其在神化所处的具体时空境遇的。而如果缺乏这一前提,那即便每个人都禀赋着仁义之潜能,其也并不一定能将其显现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从本体论上说,必须以圣人趋时为前提,从具体之时与几出发,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构建一个合于太和之道的具体之时位基础,以此为前提,道德实践才能获得普遍的价值与意义。因此,“趋时”或外王工夫其实依然可以被认作是一种道德工夫,它是确立道德价值的基础,只是其对于趋时之人的要求很高,趋时者必成为圣人,唯圣人可以趋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