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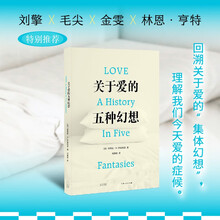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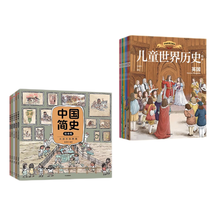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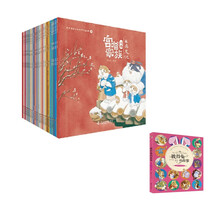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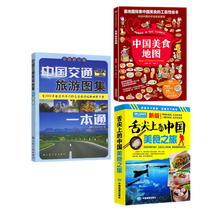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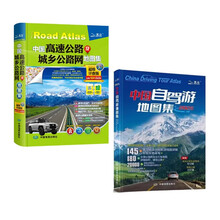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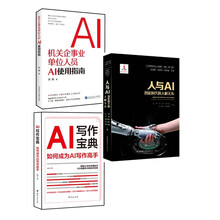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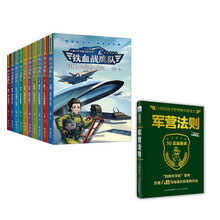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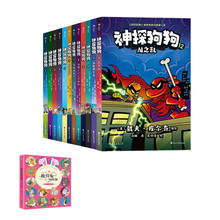
不平等的起源是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是从平等主义的狩猎一采集者进化而来,然而,为什么我们中大多数人却又在少数富裕的人的掌控之下?《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接续雅克·卢梭对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探讨,试图在人类起源、人种扩散、社群聚合、国家出现直到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以探索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社群中社会逻辑演变为主线,运用考古学研究成果把握趋势,借助社会人类学材料还原细节,系统建构了人类社会从原始人群到奴隶制、君主制乃至帝国阶段发展历程中“观念世界”发挥作用的内在规律,廓清了人类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实质。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通往奴隶制、君主制和帝国之路》作者得出结论:不平等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动态现象;基于个人成就不平等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激发社会成员的进取精神,保持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固守于世袭不平等,则不仅是对“人人生而平等”信条的公然违背,还会成为抑制创新精神的桎梏,最终制约社会的有序发展。
《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通往奴隶制、君主制和帝国之路》:
近东地区:从觅食者社群到基于成就的村落社会
在两万年前的冰河时代冷峰期间,近东地区的许多较高山区都被林木稀少的干草原覆盖。然而约旦河谷地区却是温暖的庇护所。这个山谷的地标之一是叫做加利利海的咸水湖,这个湖泊处于海平面以下六百英尺。环湖的坡地维系着生长有橡树、开心果树(pistachio)、杏树(almond)、无花果树(fig)及橄榄树(olive)等树木的地中海式林地。
湖岸的西南分布着一个史前营地遗址,以色列考古学家称其为奥哈罗Ⅱ期(Ohalo Ⅱ)。奥哈罗觅食者住在用树枝与茅草搭建的房舍里,与哈扎族人和昆族人的圆锥形茅舍不同。一些屋舍内有草床,并且还有露天炉灶等。
这些两万年前的觅食者采集的野生植物超过一百四十种。与尼罗河湾地区的采集者采集球根与块茎相反,这个地中海林地地区的居民则集中采集高热量和含糖量的果实。他们采集橡果、杏子、开心果、野橄榄以及野无花果、葡萄与树莓等果实。然而,在他们留下的废弃物考古学材料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植物是其他狩猎采集者会忽略的野草种子。这些种子中一半是雀麦草,并不是很能引起食欲的食物。其他遗存种子是碱草、大看麦娘,以及野生谷草的四类变种等。
这些禾谷草中的两类野大麦和双粒小麦是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最重要农作物的原种。因此,该阶段开始了一个类似于古代新几内亚培育西谷米、野芋、甘薯及车前草的过程:最先阶段是对野生禾谷的充分利用,随后是小麦和大麦的培育。
当一万年前冰河时代结束时,整个近东地区,禾谷植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大幅改善。回升的温度使得橡树、开心果树以及多籽谷草向更高海拔散播。冰川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地球大气层中二氧化碳量从百万分之一百八十增长到百万分之二百八十,仅在数千年间就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增长。植物在这种高浓度二氧化碳环境下生长得更好,因此是农艺试验的好时机。
起码早期的一些种子采集者曾把他们的屋舍像巴萨尔瓦人或安达曼人那样排布成圆形或椭圆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来自伊拉克北部的穆勒法特(Mlefaat)。穆勒法特地处幼发拉底河一条支流之上,高出海平面有九百五十英尺,距离摩苏尔(Mosul)城有二十英里。在一万年前,穆勒法特的觅食者们曾清理出一块长约三百英尺、宽约两百英尺的场地,并用夯实的黏土覆盖其上。在这个平面之上,他们围绕着一个椭圆形区域布置了十个屋舍,并且这个椭圆形空地可以用于跳舞或其他仪式活动(图十四,上)。屋舍体量从直径十六到二十六英尺不等,并且石器工具方面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表明了每个屋舍的不同居住者男人、女人、已婚者、未婚者如同图二中所示的巴萨尔瓦房舍显出来的广泛差别。穆勒法特的觅食者依靠叫做羊面草的野生禾谷,附带少量野生大麦、小麦与黑麦糊口。他们还采集开心果和小扁豆,捕猎瞪羚。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已被深入研究的纳图夫人(Natufian),他们生活在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及叙利亚地区,从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年前,他们已将小麦和大麦采集作为其经济的重心了。为收获谷物,纳图夫人将燧石石叶嵌入骨头或木头把手制成镰刀。为存储粮食,他们编制出篮子并造出用石灰粉刷以防潮的窖穴。为把粮食做成稀饭,将其放入石臼磨碎。
纳图夫人很快了解到野生禾谷在不同海拔高度成熟于不同的月份。在海平面高度,它们成熟于4月下旬;在海拔两千到两千五百英尺高度,则成熟于5月中旬;到海拔四千五百英尺高度则成熟于6月上旬。通过从海平面高度开始收获并逐步提高海拔高度的方式,狩猎采集者可以延长食物有效供给的时节。纳图夫人看起来最固定的聚落是在较低海拔区域,这些区域里他们的废弃物中包括有来近东地区越冬的水鸟的遗迹。而在更高的山区,他们则居住在洞穴里。这里让我们透过一系列营地来追踪一下。
随着冰河时代进入尾声,圆形茅舍构成的永久性聚落开始在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整个区域散播开来。许多情况下这些茅舍都沿着一片用于仪式活动的圆形或椭圆形场地布局。有些聚落存在带有坐台、石灰抹面或雕刻独石碑的形似男人屋的建筑,图的上面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伊拉克穆勒法特考古遗址,那里有十个茅舍排列在长约三百英尺(虚线)椭圆平面上。下部是约旦瓦迪哈梅27号遗址的一座大概是男人屋的建筑,它以一圈台凳和一块雕刻独石碑为特征;其直径为四十六英尺。
在距离地中海仅有两英里的卡梅尔山的峭壁上,有个埃尔瓦德洞穴(Cave of elWad)。纳图夫人在洞穴的入口处建起了居所,并将下面的斜坡辟作台地以增大面积。另外为获得便携的磨石,他们将悬崖上的天然岩石挖出了一个磨石坑。他们用镰刀收割谷物,用弓箭捕猎瞪羚,制作骨叉捕鱼,并且削出木套夹来捕捉毫无戒备之心的水鸟。和冰河时代的乌克兰猛犸象猎手一样,纳图夫人也养有家犬。
埃尔瓦德狩猎采集者喜欢装饰,用羚羊瞪羚骨头雕出坠饰、制作玛瑙贝串饰。然而他们…喜欢的装饰品是象牙贝,他们佩戴这么多管状海贝,会让人想起哈扎人佩戴的新娘聘礼串珠。
埃尔瓦德洞穴中埋葬有超过五十个纳图夫人,他们大多佩戴象牙贝饰。洞口附近埋葬的是四肢伸展的男性、女性和儿童。外面斜坡台地处有更多男子、女子与儿童,他们中一些人的肢体紧紧蜷曲在一起,应该是族人曾将他们成批地捆绑或把他们的身体成批地包裹在一起。这些人的骸骨当中有一部分是完整的,但另外一些则是先安葬后又挖出来合葬在自己亲属墓穴中的部分人体骸骨。
在一个保存较差的住屋遗迹下面,有两个二次葬的个体,一个戴有头巾、手镯和角贝脚饰。再往不远处是一个成年人墓,像是男性,头上戴有七排贝壳;另有两个挖出来并重新安葬的个体陪伴着他。另一个男人有精心制作的盖头和一串角贝脚饰,同时还有一串骨质项链和贝珠;他还有另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陪葬,明显是二次葬的。
现在让我们再向上去,来到距离海平面八百英尺的林木茂盛的加利利山上。这里有另一群纳图夫人居住在距离海边刚好八英里的哈尤尼姆洞穴(Cave of Hayonim)。基本与埃尔瓦德洞穴中的居住者一样,纳图夫人对洞穴内与斜坡台地都进行过修整。
在哈尤尼姆案例中,纳图夫人建造了更多的附属住屋。室内地面沉入地下,矮墙用石头不施灰浆干砌而成,屋顶用树枝构架。这五个大都有火塘的圆形房舍在这个洞穴中构成了一个集中的建筑群。在这个洞穴外面的斜坡台地上则是一个可能用于储存谷物的构筑物。
有三代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包括奥费尔?巴约瑟夫(Ofer BarYosef)与安娜?贝尔费尔科恩(Anna BelferCohen),发掘了这个洞穴内外区域的墓葬。其中的遗存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由人类学家帕特里西亚?史密斯(Patricia Smith)针对这些遗骸中十七个个体所做的分析结果表明: 八个个体(接近半数)为先天性缺少第三臼齿(或智齿)。这样一个高频度的先天异常现象表明哈尤尼姆人是在一个很小的基因库范围内婚配的。
这类近亲繁殖有几种可能解释。我们曾见到过狩猎采集社群中的一个杰出男性用自己的基因贡献了自己群体百分之二十人口的例子;我们也见过一夫多妻猎手的妻子们有时就是姐妹的情况;最后我们还了解过一些澳洲社群将适婚对象削减至占人口八分之一范围的婚姻规则。在一个小规模觅食者社群当中,任何或所有这样的处置都有可能增加了基因异常的频度。
哈尤尼姆的纳图夫人同样用角贝装饰自己,且其中还另有故事。这些角贝当中有一部分属于距离只有八英里的地中海的一个品种。而另外的角贝则属于来自南方约四百英里的红海的一个品种。后者抵达加利利,几乎可以确定是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换的结果。为何他们会为只要步行八英里就能得到的贝壳进行远距离贸易呢?答案就是,并不是贝壳的直接价值而是通过交换产生的社会关系在发挥作用。
让我们向更高海拔攀登,这次去到耶路撒冷西北二十五英里处的一个溪谷地带。在朱迪亚山区(mountain of Judea)海拔一千英尺的地方,有个苏克巴(Shukbah)洞穴。考古学家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 Garrod)在苏克巴洞穴发现有大量镰刀与火塘,但意外的是几乎没有磨谷石器和贮藏窖穴。这一现象提出了以下可能: 纳图夫人在苏克巴停留的时间仅够收获可以利用的小麦与大麦,随后尽可能多地将收获物带到较低海拔的、更持久的宿营地。
更长期、更低海拔宿营地的一个可靠例子就是约旦河河谷的艾因马拉哈(Ain Mallha)。纳图夫人居住在这里哈勒湖(Lake Huleh)边的斜坡上,哈勒湖是加利利海北部的一个淡水湖,边上生长有广袤的芦苇。该湖自身的海拔只有两百英尺,湖边夹持着长有禾谷草与橡树、开心果树及杏树的山峦。
数代考古工作者,包括基恩?佩罗特(Jean Perrot)和弗兰科瓦?R.瓦拉(Francois R. Valla),在艾因马拉哈发现有一系列重复使用过的营地。纳图夫人居住在圆形或新月形房舍中,这些房舍的下半部分沉入地下。支撑屋顶的柱子嵌在砖石干砌的墙内,砖石墙构成每座建筑物的地下部分。这些屋舍直径大小从十三到二十六英尺不等。由于发掘出的屋舍量如此之多,我们得以看出有些屋舍大得足以满足一个核心家庭所需,而另一些则可能仅适于单个人使用或许是一个二房妻子,一个寡妇,或者一个鳏夫还有一些大得足以作为单身汉们的房舍。
佩罗特发现的一座建筑,与其他建筑比较十分醒目。它的外部直径差不多有二十一英尺,有一个宽度大于两英尺的台座沿内墙布置。与典型的住屋不同,这个构筑物及其内部的台座都施有白灰抹面,室内地面用石板精心铺砌。靠墙有一个小火炉,火炉边上摆放有一个人的颅骨。我们认为这个建筑可能是单身汉屋舍或男人屋的最早例子之一。
纳图夫人的男人屋,到底是所有年轻人宿舍,还是针对少数已启蒙过的人的仪式房屋呢?艾因马拉哈的这座建筑看起来太小了,除已启蒙少数人之外,容纳不了更多人员。然而,在约旦瓦迪哈梅(Wadi Hammeh)的27号营地遗址,看来曾有过一个更大的纳图夫人仪式建筑。这座建筑直径有四十六英尺,还有一条宽十英尺、环墙而设的、明显的台座。在这座房屋的环形下沉地面上,散卧着破损的独块巨石残件,上面刻着几何图案。哈梅的这个构筑物的尺寸是艾因马拉哈石灰抹面建筑的两倍。因此,其可能的情况是: 包容性与排斥性男人屋,在这个时期的近东地区都已出现了。
除了可能的男人屋之外,纳图夫人多世代的墓地以及贝壳财货交换等,则为我们提供了宴享的证据,在这些宴享上,大量的肉食被分享了。最早的一个例子来自下加利利(Lower Galilee)的希勒孙?塔希蒂特洞穴(Hilazon Tachtit Cave)。
在这个洞穴的中央,纳图夫人建造了两个小的地下构筑物与三个埋葬坑。在安葬仪式的某个阶段,至少有三头野牛与超过七十只乌龟被煮熟吃掉了。这与一个典型的纳图夫营地居民相比,远多于其在葬礼上消费的肉食,这也暗示着牢固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
……
前言
第一部分 起点是平等的
第一章 起源与迁徙
第二章 卢梭的“自然状态”
第三章 祖先与敌人
第四章 为何我们的先辈拥有信仰与艺术
第五章 无农业社会的不平等
第二部分 平衡声望与平等
第六章 农业与获得声望
第七章 基于成就社群中的仪式建筑
第八章 仪式建筑史前史
第九章 四个美洲土著社群中的声望与平等
第三部分 使不平等世袭的社群
第十章 农耕社群中世袭不平等的兴衰
第十一章 首领社会中权力的三种来源
第十二章 美洲地区: 从仪式屋到庙宇
第十三章 无首领的贵族统治
第十四章 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的庙宇与不平等
第十五章 美国后院的首领社群
第十六章 如何将等级阶层化: 南太平洋的故事
第四部分 王国与帝国中的不平等
第十七章 王国如何缔造
第十八章 新大陆的三个第一代王国
第十九章 蝎王之地
第二十章 黑牛皮与黄金凳
第二十一章 文明的保育园
第二十二章 贪腐与扩张主义
第二十三章 新帝国如何学习旧帝国
第五部分 反抗不平等第二十四章 不平等与自然法
附录注释
插图来源
译后记
★不平等的起源是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是从平等主义的狩猎者或采集人进化而来,然而,为什么我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却在那些富裕的人的掌控之下,不管他们是民主地选举出来的总统抑或是军事领袖。在这一文笔流畅、极具可读性的调查中,作者考察了近一万年人类社会整个的历史进程,给我们找出不平等这一问题的答案。本书将会成为长期的政治发展的标准解释。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著名人类学家)
★通过详细阐明来自考古学和人种志的数据,作者展现了世界不同地方的特定文化发展的全景图;并且在选取案例时,也超过了在当下人类学教科书中司空见惯的例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必将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罗伯特·卡内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杰出人类学家。)
★本书两位作者是当代*杰出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其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极具可读性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方式,展现了两位学者在整个古代世界复杂社会的起源和进化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
——查尔斯·斯坦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