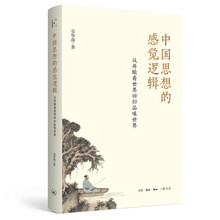康桥清夏访硕儒
早年学历 入道机缘
胡治洪:杜先生,您好。十分荣幸有机会拜访您。有关您的访谈文章,见诸报刊的已经不少。我注意到那些文章多着重于学术和思想方面,这当然也是我要请教的。但我首先想从您的生平行履、学思进程这类起始性问题进入,比如您是基于何种机缘选择儒学作为终生事业,又是如何一步步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另外,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您就基本上生活于美国,您也不止一次地声称自己是西方文化的“受惠者”。那么能否比较全面具体地谈谈哪些西方学者对您的思想影响较大,这些影响又如何促进了您的儒学研究?所有这些情况正是把握您的思想构成、评价您的思想地位的必要前提。
杜维明:我接触儒学是在中国台湾建国中学时期。当时开设“民族精神教育”课,实际上就是政治说教课,与升学没有关系,很多学生没兴趣。讲授这门课的老师名叫周文杰,当时三十多岁,是牟宗三先生的学生。他在全班五六十名学生中挑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人,进行特别讲授。一开始,他给我们讲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作品,培养我们对于古典的兴趣,然后进入“四书”。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每个周末讲一次,并要求我们细读经注,深扣字句。正是他使我初步了解到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了解到何为人、如何成人、内外打通一类问题,了解到儒家的人禽、夷夏、义利、王霸之辨,也聆受了“只管耕耘,莫问收获”的教诲。从那时起,我对儒家文本产生了亲和感,有了尚友千古的思情。
也是通过周文杰老师,我认识了当时在台湾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的牟宗三先生,后来通过牟先生认识了徐复观先生和唐君毅先生。暑假期间我与四五位学友听牟先生讲课,这些学友现在都是理工界的高级人才。正是基于上述经历和思情,中学毕业后,我报考了牟、徐二先生均在任教的东海大学。
东海大学是基督教学校,但并不强迫信仰。学校开办各种课外学术沙龙。在这种氛围中,我得以接触各种思想资源。当时对欧美现代哲学思潮兴趣较浓,尤其注意存在主义和经验主义。通过参加读经班的宗教活动,对基督教文化以及柏拉图神秘主义、斯多噶主义、圣奥古斯丁、帕斯卡等有了一定的了解。而当时中国台湾社会突出提倡的是传统文化,这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传统的义理学与词章学之间,我本来对于后者怀有浓厚兴趣,且中学时期已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但此时我尽量控制自己不向这个方面投入,而发展义理之学。东海大学的英语力量很强,我大一学年就在英文系,后来徐复观先生认为是可造之才,动员我转到中文系。英文底子为我日后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当时东海大学教师多为一时之选。牟先生擅长康德、黑格尔(他在我大三学年离开东海大学去了香港)。徐先生专精《孟子》、西汉思想、《文心雕龙》。鲁实先先生对历代文选和甲骨文字颇有造诣,他指导我们标点《史记》,对我的基本功大有裨益。还有孙克宽先生研究杜诗(后来成为蒙古史学家),梁容若先生研究白话文,张佛泉先生研究自由与人权理论,徐道麟先生研究政治学、心理学和思辨,王德昭先生研究希腊哲学与文艺复兴,戴君仁先生为马一浮传人,农学家程兆熊先生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签名者之一。当时刘述先在东海大学任助教,讲希腊哲学,还很年轻,所以我同他的关系在于师友之间。东海大学首任校长曾约农是曾纪泽之子,曾国藩之孙,他任职一年即离开,但为学校奠定了校风。继任校长吴德耀是哈佛大学博士,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人之一,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后到东海大学任职,为东海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到新加坡组建了东亚哲学研究所。吴先生也是我们家的世交,与家父是金陵大学的先后校友。
谈到家庭,应该说这方面的熏陶也是十分重要的。我的父亲由金陵大学毕业,主修英文和经济,但对中国诗词深有兴趣,发表过诗作,还喜爱西洋古典音乐。记得小时候的夜晚,父亲常常关上灯,用留声机放唱片,这培养了我听的能力。母亲出自欧阳家族,肄业于金陵女子大学艺术系,家里一直挂着徐悲鸿送她的奔马图。四姨妈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带引下,我拜见过业已闭关的印顺大师,后来还与法鼓山圣严师傅有过较多的学术交往,这是我与佛教的一段因缘,对我日后的宗教研究颇有助益。
我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唯一比较排拒的就是政治。在建国中学我曾担任“青年救国团”的分队长,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在当时是蒋经国直接关注的对象,但我主动放弃了。60年代初中国台湾“中西文化论战”期间,以殷海光、居浩然、李敖为一方的“西化派”和以徐复观、胡秋原为一方的“传统派”常常做政治文章,但那时我与徐先生的接触只限于学术方面,不卷入政治。可以说我对“政治化儒家”的防杜由来已久。我能够理鲁迅、柏杨、李敖对于儒家阴暗面的揭露和抨击,我本人也保持着对于儒学的批判意识和“隔离的智慧”。不过虽然我排拒政治,但我的民族情感却很强烈。记得1954年我第一次出国,到菲律宾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路过香港,看到一些香港人很洋化,心里很反感。不过我后来走访多次后才发现香江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港大在学术传承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1962到1966年,我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四年求学生活。 1966年我回到中国台湾,在东海大学任教,同时听徐复观先生讲课。这是我教学生涯的开端。此次回中国台湾,曾到香港牟宗三先生处住过一个月。牟先生正在写《心体与性体》,书稿由我带到台湾出版。记得当时我人还没到台湾,牟先生电报已到,嘱咐我说书稿比他的生命还宝贵。此间通过韦政通见过殷海光先生,我与殷先生一见如故,十分投契。当时殷先生已被台湾大学除名,所以一般不进台大校门。但我到台大演讲,殷先生不仅到场,而且发表了评论。这一时期,哈耶克(F. A. Hayek)曾到台湾作为期十天的访问,我担任翻译,全程陪同,其间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其一是哈耶克去见蒋介石,我表示可以陪送他到“总统府”门口,但不进去为他作翻译。后来他与蒋见面时的翻译是由当时蒋的私人译员、以后出任过“外交部长”的钱复承担的。哈耶克见到蒋之后非常兴奋,认为见到了一位“伟人”。另一件事是许倬云要我促成哈耶克与殷海光先生见面。哈耶克头一次访问中国台湾曾会见过殷,使殷受到很大鼓舞,但这次他不想见殷。哈氏的态度我又不便对殷、许直说,为此许倬云对我存有误会。这两件事反映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哈耶克同时具有来自奥匈帝国贵族传统的崇拜权威的一面。
1967年,普林斯顿大学给我提供了机会,于是我再到美国,一直工作生活到现在。不过我同中国台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年都要回去两次。
为中西交 以师友视
杜维明:事实上,在我来美国求学之前,我已经接受了儒家的基本价值,它不仅在道问学而且在尊德性方面都对我的人格发展产生了影响。正是立足于这一思想资源,所以我在美国的经历与胡适、冯友兰都有很大的不同。胡、冯与欧美文化的关系是来自落后地区的学生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关系,而我与西方学人则更多地是一种师友之间的互惠关系,是双向的沟通,是平等论道的朋友。这些师友主要有史华慈,一位继承了犹太文化解经传统的哲学意识很强的史学家;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比较宗教学家,专精伊斯兰教,我所提出的“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这一观点受他启发很大;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作者,我与他曾有数面之缘,进行过思想交锋,我切入儒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部分地受到他的激发;艾律克森(Erik H. Erikson),心理学家,他的“认同”(Identity)理论及“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对我有很大影响,我于1966年回东海大学任教,便开设了“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课,而我的博士论文《新儒学思想之旅—青年王阳明》(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有人便认为运用了“心理史学”方法。还有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其弟子贝拉(Robert Bellah),比较宗教学家及现代化理论权威爱森斯塔(S. N. Eisenstadt),提出“心灵历史”(History of Consciousness)的亨利·艾肯(Henry Aiken),韦伯研究专家本杰明·纳尔逊,西班牙神父雷蒙·帕尼卡(Raimon Panikkar),汉学家狄百瑞、孟旦、牟复礼,伦理学家史蒂文森(C. L. Stevenson),希腊哲学家保尔·德夏当(Paul Desjardin),美国当代横跨欧美两洲的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神学家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戈登·考夫曼(Gordon Kaufman)、戴维·崔西(David Tracy),诠释学大师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生态学大师汤姆斯·伯利(Thomas Berry),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欧洲近代思想家路易·哈兹(Louis Hartz),等等。对他们来说,我基于儒学提出的看法他们能够欣赏。而对我来说,他们所展现的确实不是当前儒学论域所能达到的水平,而是儒学论域可能开展的远景。与这些学者进行讨论的时候,我的心思总是向着高明的方面提升,对问题的了解也不断加深,从而新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可以说,我与西方学者的交往总是处于非常复杂艰巨的了解过程中。一方面我要直面西方文化的挑战而深入了解自己的思想资源,以便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并开拓它的可能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基于我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我要了解在这种平等互惠的交往中,我能够向西方学术界提供什么,或者说回报什么。
在此我想提请注意,我在上面使用了“提供”“回报”这样的词汇,而不用“传播”,更不用“宣传”。在我的词汇中,“宣传”的含义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它意味着一个人所知道的与他所要传播的之间存在着距离,要把他所知道的那一点夸张得很大,甚至于他所不知道的也要强为之说。就好比一个传教士,他信仰上帝,但对整个基督教的来龙去脉及其复杂面向并不理解,他仅凭强烈的主观愿望要把福音传播出去。现在有些人把我的工作也理解成这个样子,认为我在理论上多有毛病,仅仅是信念和热情值得嘉许。这至少是对我的批判,即使不说是污辱。
在与西方师友的交往中,有一个事例很有意思。爱森斯塔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来哈佛,我的好朋友贝拉介绍我认识他。爱森斯塔当时已经是研究比较宗教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权威,我当然应该向他求教。我们见面时,他问我:“你提请帕森斯修正韦伯对于儒学的理解,听说帕森斯也接受了。你为什么要作这种修正?”于是我们开始交谈。他谈话时,手边准备了一些卡片,边谈边记。谈话结束后,他记录的卡片一大堆。出来以后我想,本来是我向他学习的一个难得的机缘,结果他有很大收益,而我的收益却相对不够。不过这也表明我的资源对于西方学界具有价值。同时,随着他提问的深入,我的问题意识也加强了。
还有一个交往也很值得一提。本杰明·纳尔逊是研究韦伯的专家,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开韦伯研究课。我听过他的课。那时他已是知名学者,我则刚刚出道,在伯克利任教。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找我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说我是他找了好几年的对象。他当时正在做跨文化研究(Inter-civilizational studies),要找几位合作者。在印度哲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方面他都可以找到合作者,但在中国文化方面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合适人选,这时他找到了我。他嘱咐我无论何时到东部来,都可以打电话给他,他要与我继续讨论。后来有一次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学术会议,事先通知了他。我到多伦多后,他居然出现了,连会议主持人都感到惊讶,说本杰明·纳尔逊是多年请不到的学者,这次竟然自费来了。纳尔逊说他来就是为了继续我们的讨论。当时议定了几个论题,如基督教的“良心”(conscience)与儒家“良知”的比较,我们约定合作把这几个论题开展出来。另外他要我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他。我寄了三五篇。他要我还寄一些。然后他建议将这些论文编辑出版,并答应撰写序言。这个论文集就是《仁与修身》(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可惜1977年他到德国讲学,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68岁。这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对我是更大的损失。不然的话,通过他,我可以更深地契入西方学术界。
了解大陆 补足语境
杜维明:自从到美国求学开始,我就注意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状况,弥补在中国台湾接受早期教育所造成的茫昧,以便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把握儒学的语境。
基于这一思路,从1978年以来,我一直主动地争取回国,在我们这一代海外学人当中,这大概是少有的。1978年随美国一个海洋代表团在国内待了一个月,1980年在北师大一年,1985年在北大讲学半年多,加上其余的来来往往,国内的经历总在三年以上。这样才不至于走马观花,而可能与各方面各层次的学者坐下来谈。当时对我回国的动机有种种说法,或以为是宣传儒学,或以为是企图造成影响、甚至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实际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所谓“精英分子”都不欢迎儒学。但我的目的只不过要了解与学习。我到美国之后,接触面不可谓不广,但如果对作为儒学母国的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懵然无知,无论如何都是很大的缺憾。徐复观先生以未能参拜曲阜为终生之憾,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我回国之初带着两个问题。其一,具有思想创发意义的哲学的儒学在国内有无发展前景?其二,国内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在此须作说明,“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具有批判性和群体性的自我意识,不应误读为“群体自我批判的意识”。在北师大一年,我首先从赵光贤、白寿彝、何兹全、刘家和这些前辈那里获得很大的教益,由此认识到中国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决不会因为“文革”便荡然无存。后来,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开办了;张岱年、任继愈、庞朴、汤一介、李泽厚、蒙培元、牟钟鉴,还有年轻一辈的刘笑敢、陈来、甘阳等在当时国内人文学界比较有创建性的老、中、青学者我几乎都接触到了,还作为“内宾”参加了汤用彤学术思想讨论会和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互动问题讨论会。由此我对以上两个问题得出了肯定的答案,进而使我逐渐形成了“文化中国”的观点,意图以更加宽广的视域来了解儒家文明。
在国内我有一个感觉,有些人在辩难时,总是力图使儒学向下沉沦。这些人总是不断质疑:你是不是把孔子拔高啦?你是不是把儒家美化啦?它的阴暗面如何如何。甚至一直沉沦到柏杨所谓的“酱缸”里了,还不满足,认为你只要在讲,就是对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干扰,就是封建遗毒,就是迎合现实政治,或者是为了某种个人私利,总之是从最不健康的方面来判断你的学术动机。不过这对我倒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挑战。它可以使我避免片面执著于那种与国内语境完全脱节的、在与西方学术界论辩中形成的极高明的儒学理念。它使我能够经常以本雅明所谓“一个最高的理念在一个复杂的权力关系网里面也可以体现最残忍的面貌”的论断来审视儒学。它提醒我对于儒家的阴暗面加以深刻照察;如果没有这种照察,那么对于儒学极高明一面的认识就很可能是无根的玄想。
国内一些学者往往还认为,我们这些生活在国外的人当然要讲儒学光辉灿烂的一面,如果把儒学讲得一无是处,拿什么混饭吃呀?或者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美国的儒家”,没有感受到民族传统的阴暗面,没有遭受由此而来的灾难,体受的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优点,所以能够欣赏儒学的好处。但是事实上,假如儒学并无真正的价值,我宁愿砸掉饭碗,也不会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一己私利而维护儒学。如果为个人计,我当初就不会选择儒家事业,而可以在外文或理工科求发展。至于认为“美国的儒家”得到的都是好处,我可以举一个事例来证伪。瞿同祖先生和杨联陞先生本来同在美国。后来瞿回了大陆,“文革”期间下放,1978年才回学术界,学术上是受到了耽误,但身体搞好了。而杨先生在美国,精神和体质都垮了。实际上,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要生存发展,需要应付很大的压力,需要更大的勇气。这一点很希望国内知识分子能够理解。
胡治洪:从上述对您的学术事业均具重要影响的中国台湾、美国、中国大陆三个方面的广泛交往中,您如何厘定自己的师承?
杜维明:关于师承问题,也就是所谓“道统”问题。严格意义上的“道统”类似于原教旨主义,讲究原始教义一脉相承,这是我所不取的,实际上也难以把握。儒学史上往往以为孔子之道传于孟子,荀子则不得其传。荀子固然有“制天”“用天”思想而不尊“天”,但他的“道”则具有超越性,不能说完全超逸于孔子。又或以为孟子心性之学由陆、王继承,朱子属于别传(如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是“别子为宗”)。但李退溪恰恰认为他自朱子一系所继承的才是孔孟正统。凡此均提示我们,对于“道统”或师承,既要有真正的认同,又要有开放的心灵。
具体说到我个人的师承,严格地说,应该由学术界根据我的论著所表现的思想形态加以判断。不过我可以谈谈我的一家之言,谨供参考而已。从我衷心服膺以及学术期许来看,我确实最接近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熊、牟对我的思想震撼力最大。但在私人感情上,我与徐复观先生最亲近,徐先生那种随俗的生活态度、泥土气息以及乐观精神对我有很大影响;在这方面,徐、牟形成鲜明对照,牟先生晚年心境是很孤独,甚至很痛苦的。余敦康则认为我更像唐君毅先生,唐先生也承担大量行政工作,与狄百瑞、陈荣捷、冈田武彦等一起积极宣传新儒学,重视家庭生活,这也是一种看法。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