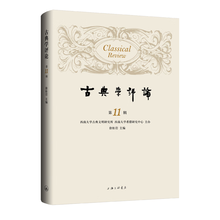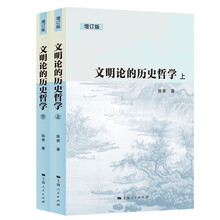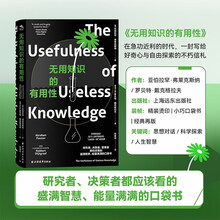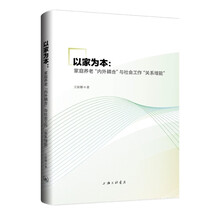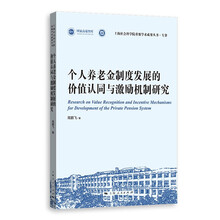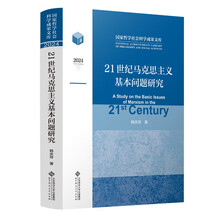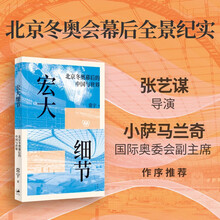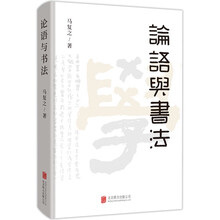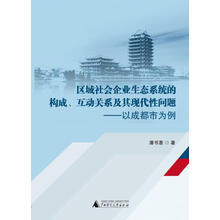比方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热衷于各种各样的考试,追逐各种各样的文凭,它说明当今社会对学习的狭隘化的理解:所谓学习就是一个人向其他有关的人证明他能学到某些东西。这是一个追求从个人确定性和与公共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确定性过程,它是适应全球化极其猛烈地追求量化的思维方式在知识这个观念中的表现。这种观念当然必然会反映到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究上。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物极必反的。自然科学思想方法霸权搞得过头了以后,从历史上某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要求用独立的方法论探究,人们越来越强调自己在方法上的研究个性。基本的理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人、社会、文化)(它们在内在性、相对于其环境的自律性以及通过行使某种意志自由从而改变社会进程的能力上都不同于自然客体)的性质,它们不能够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对一些理论家来说,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内在性、自律性和意志自由使得即便是对创立有关人、文化和社会的成熟科学的渴望也变得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合时宜。”
波普尔、阿伦特、德里达等人索性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以科学性自居会导致极权政治哲学的产生。①因为“科学的科学性,总是依赖于意识形态,一种今天的任何特殊科学,只要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够忽略的意识形态”②。这意味着,自然科学似乎可以通过获得一致见解取得进步,既定的科学家群体成员可以为科学数据、形式以及解释等问题,时不时地达成一致见解。在历史科学或精神科学中,没有或不曾有过这样一致的见解。历史科学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正如李凯尔特就此评论道:“只有当人们考虑到道德和权利的历史形态,从而只有当人们不再试图达到一种普遍的、按照自然科学方法或者普遍化方法形成关于权利的类概念时,才能获得一些普遍有效的、内容充实的伦理规范或者权利规范。”④实际上,在人文领域中,在后现代主义的名义下,整个人文科学运动的主要特征便是支持一种向叙事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支持人文科学回归像历史学家讲那种故事的方法。
今天人们在两重意义上谈论着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首先,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感到,正在丧失与科学之间的源本关系。人们回忆起韦伯所引发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讨论时,就会对科学及其意义真正地产生怀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