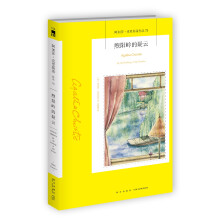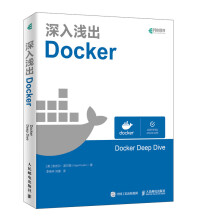活着的喜悦——凝视阴影,才能遇见光明
人们说我们都在追寻生命的意义。
我不认为那是我们真正追寻的。
我认为我们追寻的是一种活着的体验……
这样我们才能感觉到活着的喜悦。
——约瑟夫·坎伯
约瑟夫·坎伯花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探索宗教、神话与艺术中埋藏的智慧。在他悠久学术生涯的尾声,名记者比尔·莫耶斯问他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坎伯的回答让莫耶斯很惊讶——他说人类长久以来追寻的不是意义,而是他所谓“活着的喜悦”。多年来,坎伯不仅研究,还参与了各种有组织的宗教传统与原住民仪式,这让他认为每个人——不管是来自古希腊、非洲部落或现代美国——并不是渴望拥有特别的使命或拯救地球的任务,或是在学术上探索何谓开悟,我们想要的,其实是活生生而浓烈的活着的体验。如果为人类服务或寻找内心的渴望是来自对生命着迷的投入,那么我们的奉献与追寻就会开花结果;但我们若想从一口干井中去爱、去带领、去工作或去祈祷,那我们只能提供一杯苦水给身边的人,而且从未真正活出我们被赐予的生命。
当看到电视传道牧师涨红的脸孔,或是游行抗议的愤怒社运人士僵硬的身体时,我真想把这些人拉到一旁,按摩他们的肩膀,抚平他们皱着的眉头,喂他们可口的食物,逗他们笑。我想说:“不用这么紧张、这么激烈、这么严厉。你可以设法减轻社会的病状,同时爱这世上所有的哀伤与美丽;你可以感觉活着的简单喜悦,并让那种喜悦成为你的北极星;你可以被一种平静的喜悦引导。”
为了喜悦而活,看起来像是少数人士才拥有的自私之举,或享乐主义的华丽辞藻。其实不然。喜悦不是自私的情绪,它是纯然的感恩,自由地流经身体、心灵——感恩什么?感恩呼吸、色彩、音乐、友谊、幽默、天气、睡眠与觉察;它是自愿投入生命整个混乱的奇迹。世上的苦难大多是由不快乐而沉闷的人想做好事所造成的,而不是那些怡然自足的人。
到头来,当来世上工作时,唯有对自己感到自在的人——那些爱这个受伤的世界与它破碎的家庭的人——可以移山填海。宗教的创始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疗愈与唤醒群众的能力,首先来自他们自己破碎重生的体验。过去或现在每一个伟大的英雄都踏上艰辛的自我觉察旅程,然后找到他们的喜悦。佛陀花了多年时间坐在森林中,独自与痛苦搏斗,而他的开悟照亮了百万人的道路;耶稣打破传统,离开家庭与族群,进入沙漠40个昼夜,就像在他之前的希伯来先知一样。在森林中、在沙漠里,他们面对内在的恶魔,然后找到了自己。他们想要为这个世界导正的,先在自己的心里这样做,如此一来,也获得了谦逊与真实。他们深入黑暗之中——深深地接受并改变自己犯下罪恶的能力——出来时带着一种喜悦,永远不会消失。
很奇怪,我们若排斥痛苦,只会找到更多痛苦,但如果拥抱内在的一切——如果无惧地凝视阴影——我们就会遇见光明。“有一次,我们在讨论受苦时,”比尔·莫耶斯谈起他与坎伯的对话,“他同时提到了《尤里西斯》的作者乔伊斯与伊瓜卡朱。‘伊瓜卡朱是谁?’我几乎念不出这个名字。‘噢,’坎伯回答,‘他是加拿大北部卡里布因纽特人的心灵大师,他告诉来访的欧洲人,真正的智慧是远离人群的,存在于极端的孤独中,只能透过受苦才能获得。’”
极端的孤独就像毛毛虫所承受的那样,它把自己裹在茧里,展开漫长的蜕变过程,从虫蛹变成蝴蝶。而当过去已知的生命告终——当我们觉得当个毛毛虫并不真实,却还不知道应该变成什么时——我们似乎也要经历这样的时期。我们只知道某种更伟大的事物在召唤我们改变,虽然必须独自踏上旅程,而受苦是唯一的同伴,但很快地,我们就会变成蝴蝶,品尝到活着的喜悦。
我的冰箱上贴着一张卡片,上面是一个女人崇敬地站在打开的冰箱前说道:“真奇妙!又有了完美的冰块。”这就是我说的简单喜悦。我知道我们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像个傻瓜一样站在冰箱前赞叹冰块,但你可以问自己这个好问题:如果完美的冰块、夕阳或收音机里的一首老歌最近都无法让你心动,这是为什么?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无法在明亮的房间中找到答案。要想拥有浓烈的生命,你必须进入黑暗,你内在想要活着的那一部分,会在漫长的孤独之后出现——就像我一样。
转变的旅程有数百种不同的名称:奥德赛、追寻圣杯、大灌顶、死亡与重生过程、终极之战、心灵暗夜、英雄旅程。这些名称都描述了对极端困境臣服的过程——让痛苦将我们打破,然后重生,变得更强壮,更有智慧,更仁慈。所有宗教经典中都有沉沦与重生的故事,从乔纳被鲸鱼吞进肚里,到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从印度史诗中的战争英雄阿朱那,到放弃一切成为佛陀的悉达多王子,在我们之前,这些伟人都曾经踏上这段旅程。当比尔·莫耶斯问约瑟夫·坎伯关于英雄旅程时,坎伯说:“传奇英雄通常是某种事物的创始者——新纪元、新宗教、新城市、新生活方式的创始者。”
莫耶斯反问:“这不是让我们这些平凡人望尘莫及?”
“我不认为有所谓的平凡人,”坎伯回答,“听到有人说‘平凡人’时,我总觉得不自在,因为我从来没遇见过任何一个平凡人,不管男女老幼……你可以说,某种生活的创始者——你的生活或我的,如果我们过着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模仿他人的生活的话——也是源自一趟追寻。”
我对这种追寻有自己的称呼——我称之为“凤凰涅槃”,是为了向那只有着金色羽毛、流传千古的神鸟致敬。人们把那只鸟称为凤凰,相信每隔500年它就会重新追寻一次真实自我。凤凰知道只有在旧的习性、防卫与信仰死亡之后,新的才会诞生,于是用肉桂与没药做了一个柴堆,点燃后把自己烧死。然后,它从灰烬中升起,成为新的生命——融合了以前的自己与新生的自己。一只新的鸟,但更接近自己;有所转变,但还是那永生的凤凰。罗马诗人欧维德是这么说凤凰的:“大多数生物是被其他个体所生,但有一种生物会自己生自己。”
你我都是“凤凰”,同样可以从困境的碎片中重生。每次遭遇内在与外在世界的改变时,我们的生命就会要求我们打破自己,然后重生。当我们一路往下坠入失败的深渊,带着敞开的心,在黑暗与痛苦中耐心等待时,就能带着生命的甜美与内在成长的喜悦回到上面;当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时,我们会找到真实的自我——无缺、丰足的自我,不再需要他人来定义自己,或是让自己完整,而只是在旅程中彼此相伴。
这才是活出充满意义与希望的生命的方式,拥有真正的快乐与内在的平静。这就是凤凰涅槃。
要点火必须先有火星——利用余烬、火柴,或是稳定地用一样东西摩擦另一样东西。一旦点燃了火,你需要一种不同的热度,来将逆境的烈焰变成凤凰涅槃的智慧。我们毕生都会经历改变与失去——透过重大且剧烈的生命地震,以及较小、较惯常的方式——要花费一番功夫才能利用危机与压力工具实现转变。本书这部分的所有故事都是关于其他人的生命如何被点燃,以及他们如何艰辛地把火焰变为凤凰涅槃,而下一部分则是我自己的凤凰涅槃过程。我的故事没有接下来的几个故事那样创痛,但寓意是一样的。我在离婚后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不建议把心与家庭的破碎当成转变之道,我仍然感激在路上所学到的功课。
每个人的凤凰涅槃都不一样,因此这是一趟未知之旅。把某人的旅程与其他人的相比较,这样做不但是错的,甚至没有帮助——所有的旅程都不一样,也没有任何一趟旅程比其他的更深刻或更重要。重大状况——例如失去子女、重病、国家灾难——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比较没那么创痛的事件也可以。重点在于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无常本质,如何勇敢地接纳发生的任何事,如何倾听火焰中的信息,从灰烬中挖出宝藏。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每个人都在灰烬中寻找同样的宝藏。我们都在寻找自己最真实、最有活力、最丰富且最有智慧的自我。阻挡在自我与我们之间的事物,会在火焰中燃烧。我们的妄想、僵硬、恐惧、怪罪、缺乏信心和分离感,这些强度与组成各不相同的一切都必须死去,更真实的自我才能升起。若想把痛苦的事件变成凤凰涅槃,就必须找出自己内在需要被烧掉的部分。我在工作坊中观察到学员在设法找出他们凤凰涅槃的特定元素时,与各式各样的问题搏斗。有些人明白必须被烧掉的是他们的恐惧——对自身力量、对改变、对失去,以及对他人的恐惧;有些人找到的是失去感受能力、严重的讥讽、羞愧感,以及愤怒的态度。
我注意到对很多女性而言,当她们向自己承认,她们厌倦了做所有事情都只为了取悦他人时,凤凰涅槃过程就开始了。这些女性了解到,她们很不尊重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法,而在危机的火焰中,她们突然明白什么必须被烧尽。当新的凤凰升起时,她们也获得了正面的力量。这些女性了解并信任自己,因此对他人而言,她们也更为可靠、更值得信任。而男人之所以会进入火焰中,通常是因为变得麻木,或者因为无法感受到爱与怜悯,只能半死不活地过日子。他们内在拥有珍贵的宝藏——未曾被感受的欢愉与悲伤——等待着火焰的热来解放;当他们从灰烬中站起来时,会得到坦然、同理心,以及生而为人更多的经验作为礼物。
当然,你自己独特的过程不在于性别,而在于性格、成长背景、时机与需求。我们每个人的沉沦与重生都跟我们的相貌一样独一无二。在一生之中,我们每一次改变与成长,都会带着自己不同的部分进入火焰,然后每一次升起都将得到新的礼物。
虽然我了解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但是当我经历困难或痛苦的转变时,总能在其他人的故事中得到极大的力量与安慰,因为他们从凤凰涅槃的火焰中生还且茁壮。这些人在看似无法忍受的经验中破碎重生,让我获得启发,因此我想告诉大家这些故事。
包袱里的心灵功课
人类最终的自由,
在于选择以何种态度面对任何情况。
——维多·傅朗克
我最好的朋友的父母亲曾经历纳粹大屠杀,虽然侥幸逃过,但除了他们的性命之外,没有太多东西留下来。我朋友的母亲名叫鲁思,她是她家中唯一幸存的人。她在19岁时抵达加拿大,认识了朱利叶斯,他后来成为她的丈夫与我朋友的父亲。朱利叶斯身材高大,很有幽默感且威风凛凛。他比鲁思年长很多。在集中营里,他不仅失去了父母与兄弟姐妹,还失去了他的首任妻子与5岁的孩子,但我朋友等到她父亲年老临终时才知道这件事。
大多数逃离纳粹来到美国的人都带着悲伤与记忆,他们把这些都紧紧绑在一个包袱里,藏在某处,如此他们才能融入20世纪50年代的积极气息中。朱利叶斯把他的记忆放在一个高高的架子上,没人找得到,然后继续过日子。他赚了很多钱,让自己身边围绕着朋友与美国生活的快乐事物;他尽一切力量带着家人前进,远离过去的阴影。
鲁思则努力把她的记忆深藏在心中。她是个娇小美丽的女子,有着精致的五官与清透的皮肤。她来自波兰一个富裕有教养的犹太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纳粹开始集中犹太人,把他们迁移到华沙的贫民区时,鲁思的父亲想出一个让家人生存下来的计划。他付钱给他认识的一个天主教徒——此人曾经为他工作——在他房子的地下室建造一个房间,然后鲁思与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会一个一个地从贫民区逃出来,藏身在那个房间里,而那位天主教徒与他的妻子会照料这一家人。
鲁思是第一个逃进地下室的人。她母亲把钻石缝入她外套的折缝中,给她伪造的文件,上面是新的姓名与天主教徒的身份。她父亲叫她要勇敢,说其他家人都会随后而来,然后就带她来到贫民区边缘,由一位抵抗军偷偷带她离开。
鲁思在地下室待了几周,等待她的家人。他们从未出现,但有别人来了。某天早上,那个抵抗军过来寻找鲁思外套中的钻石。他对天主教徒与他的妻子说,鲁思若不把钻石给他,他就会把他们都交给纳粹禁卫军。那对夫妻吓坏了,要求鲁思离开。于是当德军开始轰炸华沙时,鲁思就躲在街上,而她的父母与兄弟姐妹全都死在了贫民区或集中营里。
纳粹后来还是找到了鲁思,把她送进天主教孤儿的劳动营。她没有对我朋友多谈在劳动营的岁月,只说她在一个农场工作,而当战争终于结束时,她来到某个难民营,直到一个远亲资助她前往加拿大。她在那里认识朱利叶斯,他娶了她,然后带她到纽约,帮助她将过去抛在脑后,“放在它应该存在的地方。”她这么说。但她的眼神诉说着不一样的故事——一个更残酷的故事,而几年前,她把故事带进了坟墓。
鲁思曾对女儿说过一个快乐的故事——是她小时候听到的、关于一个男人和皮箱的笑话。这些年来,我朋友跟我经常提起那个笑话,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否弄对意思,或者我们认为那个笑话的含意,跟鲁思以为的是否一样。鲁思过世的几年前,我朋友跟我曾经请鲁思再说一次那个笑话。
“噢,那不是个好笑话。”她先声明,“有个男人在拥挤的火车上对他旁边的乘客发脾气,因为他不肯从座位上移开他的行李。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笑话。”鲁思挥着手说道,仿佛要赶走这个故事。
“它对我们有更深的含意。”我解释道。
“更深的含意?笑话能有什么含意?”
“再说一次,我们就会告诉你。”我朋友说。
“好吧。有个男人在火车上,”鲁思开始说,“火车很拥挤,他要邻座的人移开行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