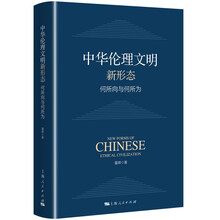《反启蒙与现代西方思想进程》:
如果无法回到原始状态,人就必须寄身于民间社会。如何在民间社会中生存?卢梭在《论教育》或《爱弥儿》中提出的自己的方案。他承认,理性能令我们理解道德,但理性又通常使我们放弃“义务”(duties),即放弃彼此之间承担的义务,放弃有关怜悯的“义务”。理性教我们大兴土木,令我们生活惬意,但是,听到某人在房子外面哀号,请求我们救助,我们会首先想到自己,而不是他人。我们总是自利(self-interest)为先,助人在后。在《论教育》中,他认为我们应该重造“怜悯”之情,以“怜悯”之情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不应自私自利,我们应该于他人有益,把自己的行动置于他人的语境(context of others)之下,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他人考虑。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因为寄身于民间社会,而不是自然状态,我们总是烦恼不断。我们烦恼不断,皆因欲壑难填。欲壑难填,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足,劳作不力,或天道无常,灾害不断,而是因为欲望本身。在他看来,无知无欲,才能断绝一切烦恼。他赞美佛教的简朴,反对科学。他反对医学,不是因为当时的医学与巫术无异,而是因为医学本身。他认为,如果我们罹患疾病,自然自有其应对方式,我们不能违抗自然的旨意。即使因此而死,我们也要无怨无悔,而不是以种种方式加以阻止。要像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的母亲那样,认定“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坦然受之。
由此可见,与其说卢梭是启蒙运动阵营的一员,不如说他发出了反启蒙运动的先声。或者说,他“组织上”属于启蒙运动,但思想上属于“反启蒙运动”。或者干脆说,他背叛了启蒙运动,是启蒙运动的“叛徒”,因为他拒斥知识和科学,主张无知和无欲。卢梭开启了反启蒙的先河,代表着欧陆思潮的一大范式转移。从此之后,启蒙与反启蒙的冲突从未中断,且反启蒙一直处于“高压态势”,压得启蒙运动抬不起头来。
尽管在其他方面存在分歧,但在对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上,所有启蒙哲人的步伐有着惊人的一致:全都对它嗤之以鼻。他们相信,第一,就人的身份(human identity)的建构而言,社会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第二,人的社会性是天然的存在,人一出世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性。社会性不只是人的身份,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心理倾向。卢梭则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孤立的存在,他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和福祉。社会和语言与大自然无关,是人类逆大自然而动的结果,当然也要品尝由此带来的恶果。走向自然状态,步人民间社会,人类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人本不具有社会性,却不得不具有社会性;一旦具有了社会性,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保持的自尊,必须转化为攻击性的自私,并最终酿成残酷的战争。一旦洪水和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迫使人采取集体行动,人就会意识到他人的存在,于是开始比较;因为比较,彼此的天然差异就会显现;差异导致竞争,甚至酿成战争。卢梭认为,自然是和谐的,但人类并不和谐,自然的和谐并不适用于人类。有人以为“看不见的手”能把“私人罪恶”转化为“公共美德”,进而形成商业社会的新道德。在卢梭看来,这种乐观主义肤浅可笑,缺乏根据。一边是自然秩序,一边是社会秩序,两者间的差异一望便知。不难发现,卢梭与霍布斯对人性和社会的看法大致相同,都充满着悲观主义。但卢梭异乎寻常之处在于,他把“秩序”植入了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认定启蒙运动恶化了本来就不和谐的社会秩序。启蒙哲人的天真幼稚使他们无视社会生活中固有的张力,他们大力传播哲学和科学,对宗教及宗教制度进行怀疑和攻击,又危及了本已脆弱不堪的社会道德,使社会跌人霍布斯所谓的战争状态,使宁静祥和的社会生活遥不可及。总之,启蒙运动罪莫大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