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若想严格地检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与真正的审美观众有多亲密,抑或自己在何种程度上属于苏格拉底式的具有批评倾向的人群,那么,他能够做的只是真诚地追问那种感觉,就是他在看到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奇迹时的感觉:他是否觉得在这里,他那以严格的心理因果性为标准的历史感受到了伤害,他是否以一种善意的妥协态度,承认这种奇迹仿佛是一种儿童能弄懂、却与他格格不入的现象,抑或是否他在这里遭受到某种别的东西呢?因为他以此即可衡量,他在多大程度上毕竟有能力来理解神话,理解这种浓缩的世界图景。而作为现象的缩影,神话是不能没有奇迹的。不过,大有可能的是,在严格的检验之下,几乎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被我们教化中那种批判的[1]——历史的精神深深地败坏了,以至于只有通过学术的途径,通过中介性的抽象,我们才能相信昔日的神话实存。不过,要是没有神话,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失去自己那种健康的、创造性的自然力量:唯有一种由神话限定的视野,才能把整个文化运动结合为一个统一体。唯有神话才能解救一切想象和阿波罗梦幻的力量,使之摆脱一种毫无选择的四处游荡。神话的形象必定是一个无所不在、但未被察觉的魔鬼般的守护人,在他的守护下,年轻的心灵成长起来,靠着它的征兆,成年人得以解释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甚至国家也不知道有比神话基础更强大的不成文法了;这个神话基础保证了国家与宗教的联系,以及国家从神话观念中的成长过程。
现在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没有神话引导的抽象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道德、抽象的法律、抽象的国家;让我们来设想一下那种无规矩的、不受本土神话约束的飘浮不定的艺术想象力;让我们来设想一种文化,它没有牢固而神圣的发祥地,而是注定要耗尽它的全部可能性,要勉强靠所有外来文化度日——这就是当代,是那种以消灭神话为目标的苏格拉底主义的结果。如今,失却神话的人们永远饥肠辘辘,置身于形形色色的过去时代中,翻箱倒柜地寻找本根,哪怕是最幽远的古代世界,人们也必得深挖一通。不知餍足的现代文化有着巨大的历史需要,把无数其他文化收集到自身周围,并且有一种贪婪的求知欲——这一切如果并不表示神话的丧失,并不表示神话故乡、神话母腹的丧失,又能指示着什么呢?我们要问问自己,这种文化如此狂热而又如此可怕的骚动,是不是就无异于饿汉的饥不择食和贪婪攫取呢?——这样一种文化无论吞食什么都吃不饱,碰到最滋补、最有益的食物,往往就把它转变成“历史和批判”,若此,谁还愿意给它点什么呢?
倘若我们德国性格已然与德国文化不可分解地纠缠在一起了,实即与之一体化了,其方式就如同我们在文明的法国惊恐地观察到的那样,那么,我们也必定要痛苦地对德国性格感到绝望了。长期以来构成法国的伟大优点、构成其巨大优势之原因的东西,正是那种民族与文化的一体化,看见这一点,我们便不禁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这种十分成问题的文化都是与我们民族性格的高贵核心毫无共同之处的。相反,我们的全部希望都渴求着那样一种感知,即:在这种不安地上下颤动的文化生活和教育痉挛背后,隐藏着一种壮丽的、内在健康的、古老的力量;诚然,这种力量只有在非同寻常的时刻才能强有力地发动一回,尔后重又归于平静,梦想着下一次觉醒。从这个深渊里产生了德国的宗教改革:而在它的赞美诗中首次响起了德国音乐的未来曲调。路德的这种赞美诗[1]是多么深刻、勇敢和富于感情,是多么美好而温存,有如春天来临之际,从茂密的丛林里传来第一声狄奥尼索斯的迷人叫唤。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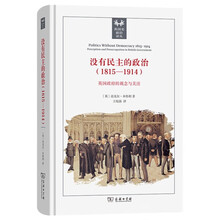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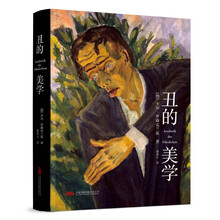




——冯至
★尼采哲学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尼采不仅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激进批判者,而且更是一位关怀当下、指向未来的大哲。
——孙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