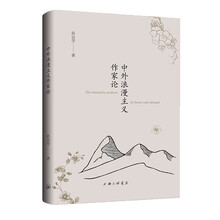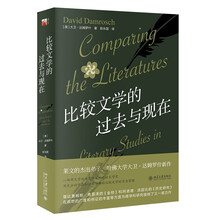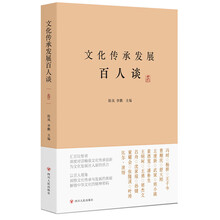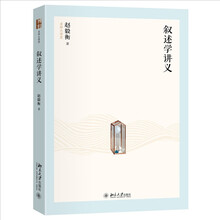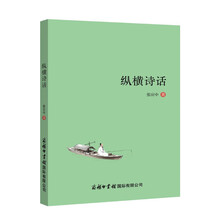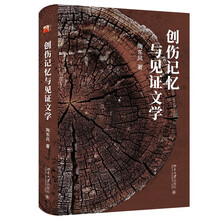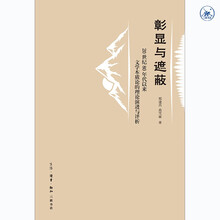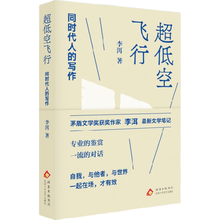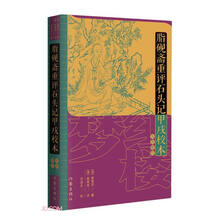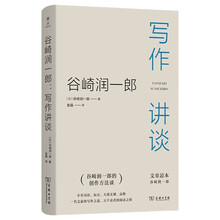I.1 符号学的两个意义
“符号学”既指专门的人类符号过程,也指一般符号科学。
按照第一意义来看,符号学和人类具体的元符号过程能力相关。在包含符号过程的生命世界里,人类的符号过程具有元符号过程的特征——即反思符号的可能。我们可将符号作为解释的对象来处理,它们与我们对它的反应无异。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符号:悬置我们对它的反应,从而得以对它进行审视。
在《形而上学》开头,亚里士多德正确指出,探求知识是人的本性。从他这一说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探寻符号是人的本性。人类符号过程是以符号学而呈现的。作为人类符号过程的符号学在整个宇宙中都可以探寻可以看作符号的意义。然而,人类思想史告诉我们,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符号学,那就会出现使人类符号过程“绝对化”、过于简单化地将人类符号过程视同符号过程本身的危险。
按照第二意义来看,符号学是有关符号的研究。有些学者视符号学为一门学科或科学(索绪尔),有些学者视其为一种理论(莫里斯),还有一些学者视其为一种学说(西比奥克)。符号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可以包括有机体的世界,或曰生物界(西比奥克),或者也可以包括整个充满符号的宇宙(皮尔斯)。在这样的情况下,符号学就是一种“总体符号学”。或者反过来,我们可以将其研究范围局限于言语和非言语的人类符号过程。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陷入到有局限的、人类本位主义的符号学研究的危险之中。
符号过程就是某物充当符号的过程、关系或环境。符号与符号过程不可分离。要使某物成为符号,必须有其他某物在场。这第二件事物叫作解释项。解释项本身就是符号,因而和另一解释项相联系,依此类推,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无限的解释项链(见I.3)。
这一切意味着:对于每一个符号来说都有一个符号过程。每一个符号是其符号过程的一部分,无法从中分离。这类似于细胞与细胞所形成的细胞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每个符号过程又和其他符号过程相联系。所有符号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根无限的链;对符号来说,符号过程形成了一种网络。正如符号是符号过程的一部分,符号过程也是符号网络的一部分。
符号的研究已经沿着各种不同方向、在各种不同的领域获得了发展。以下仅仅是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些研究视角(及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语言符号学(索绪尔、叶姆斯列夫);语言—人类—文化符号学(雅各布森、洛特曼);心理符号学(弗洛伊德、布勒、维果茨基);哲学符号学(皮尔斯、维尔比、奥格登与理查兹、维特根斯坦、莫里斯、卡西尔);文学批评符号学(巴赫金);生物符号学(罗马尼斯、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与托尔·冯·乌克斯库尔、雅各布、莫诺);数学—拓扑学符号学(托姆)。因为符号学已经拓展至很多不同领域,所以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研究视角则显得与众不同。
鉴别符号学各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异的一种方法是:就考察一个术语symbol。这个术语已经被用作sign(符号)的替代性术语,具有好几个不同意义(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意义)。该术语无论在日常话语还是在哲学—科学话语(包括符号学话语)中都是多义词。
在《符号形式哲学》(Cassirer,1923—1929)中,恩斯特·卡西尔将symbol用作sign的同义词。人通过符号建构文化,因此是一种符号动物。符号与符号形式相关联,这催生了卡西尔的符号理性批判,或者说,对文化的不同方面(包括语言、神话和宗教)的批判。
对于奥格登和理查兹来说(Ogden与Richards,1923),symbol也表示sign。他们的符号模式是从符号(他们称为symbol)、思维(或指称关系)与指称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呈现意义的。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一个symbol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事实上,对于弗洛伊德和后来具有精神分析倾向的思想家来说,一个symbol就是一种特别的符号,就揭示无意识而言,它是表示各种精神的或梦的活动的符号。无意识以被象征物的符号表现意识,与此同时产生一种屏蔽和保护功能。
对于皮尔斯来说,symbol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它是一种“由于习惯(我使用这个术语包括自然倾向)的缘故”所导致的符号(CP 4.531)。
在查尔斯·莫里斯看来,一个symbol是代替另一符号的符号,是可以作为行为向导的符号[参见Morris,1971(1946),I:8]。
在约翰·杜威的陈述中(Dewey,1938,导言),一个symbol就是一种任意性的或规约性的符号。
对于费迪南·德·索绪尔(Saussure,1916,第一章)来说,symbol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但索绪尔认为,符号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因此有别于言语符号。相对于言语符号,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总是有点规约性(如同标志司法正义的不同级别一样),从不是完全任意的。
据阿福林切夫(Averinchev,1971)提供的百科词条“symbol”,米哈伊尔·米·巴赫金(Bakhtin,1974)从同一性与异他性或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考虑,将symbol描述为一种最需要应答性理解的符号。这种符号包括统一性的神秘之温,自我与他者的并列,爱之温与无关之冷,并列与比较。符号不可能局限于一个直接的语境;相反,它与遥远的语境相关,这便解释了它对异他性的开放性。
由于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研究,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符号学思潮——可以称为“总体符号学”(Sebeok,2001a)或“生命符号学”(Ponzio与Petrilli,2001;2002)的思潮——逐渐发展起来。西比奥克扩展了传统符号学——亦即符号论——的边界,传统符号学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言语范式,因而犯了部分代替整体的错误。西比奥克给这一符号学概念贴以“次传统”的标签,而他要推动的是他称之为“主传统”的符号学的发展,该传统由约翰·洛克和皮尔斯所代表,由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关于符号与症状的早期著作所代表。
西比奥克对符号生命的全局式研究方法与符号学“主传统”是吻合的。西比奥克是基于自己对人类本位主义和语言本位主义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批评而提出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在对符号科学或符号“学说”边界的探索中(参见其1976年出版的《对符号学说的贡献》一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比奥克不再关注符号学究竟是“科学”,还是“理论”,或是“学说”的争论,他将符号学领域进行了扩展,包含了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是西比奥克于1963年提出的一个术语),甚至包含了更为宽泛的生物符号学和内符号学。在西比奥克的概念中,符号科学不仅仅是“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的”科学(索绪尔)——即对文化交流的研究——它还是从生物符号视角对交际行为所作的研究。
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巨大的宽泛性。这种普泛性研究符号学的方法体现于最近一部对当今符号学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符号学:自然与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第一、第二卷分别出版于1997年和1998年,第三、第四卷出版于2004年)。这部由西比奥克和罗兰·波斯纳、克劳斯·罗伯林主编的作品共计四卷,三千多页,呈现了来自35个国家175位作者的178篇文章。它代表了描写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的最新研究现状;它已不仅仅是单个学科甚至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文集。其触角伸向了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数学、逻辑学、语法学、文体学、诗学、音乐学、美学、哲学等等。该指南依据第一至第三章的文章所阐述的总体符号学总的原则,收录的文章不仅仅局限于跟人类文化(包括社会机构、日常人类交际、机器信息加工、科学研究中的人类认知过程、文学作品、音乐和其他各种艺术的生产与阐释,等等)相关的符号过程的研究。除了这些方面(即人类文化的研究)以外,该指南还呈现了涉及人类以外动物的、涉及有机体新陈代谢的、涉及所有生物行为的符号过程和交际活动的研究。
I.2 主角:符号
我们要讲述一下“符号”在符号学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符号学流派中的历程。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给我们的主角提供一个“人像拼片”(虽然我们意识到,如果皮尔斯所言不虚——符号学的中心概念不是符号而是符号过程——那么,“主角”就是一个幻觉。参见Fisch,1978:41)。诚然,符号很难界定,唯有同意西比奥克的说法:“符号就是符号。”
我们已经注意到,符号与符号过程(即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关系的过程和环境)不可分离。
当然,有不同的符号概念。符号可以是索绪尔意义上的二元(能指/所指)符号结构或是皮尔斯意义上的三元(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符号结构中的一个因素。
在我们的术语中,构成符号的基本概念包括被解释项和解释项,其中解释项使得被解释项成为可能。符号得以存在,就必须既有一个被解释项符号,也有一个解释项符号——换言之,必须有一个物体充当解释项的被解释项。皮尔斯认为,某物能够充当符号的最基本的关系是三分结构,涉及以下方面:(1)某种客观的东西(未必是一个具体有形的物体),它是预先存在的、自在的,在这一意义上相对于解释来说是“物质的”(即皮尔斯的“对象”);(2)被解释项,即“有意义”的那一物体(皮尔斯的“符号”);(3)解释项,对象只有通过它才获得意义。符号被简约为最基本的术语,呈现以上三方面的内容。当我们下面再谈起“被解释项—解释项”关系时,我们指的是一个(简约的、抽象的)三分结构关系,被解释项暗含了解释的对象,因此,这一表达总是理解为“对象—被解释项—解释项”。
被解释项因为受到解释而成为一个符号成分,但反过来,解释项也是一个符号成分,是一个可以生成新符号的符号成分。因此,正如皮尔斯的“无限符号过程”概念(即:一个解释项到另一解释项无限延展的符号链)所描述的那样,哪里有符号,哪里就立刻有两个符号;由于解释项可以生成新符号,马上就有了三个符号;依此类推。
从解释的对象(即被解释项)开始来分析符号,就意味着从第二层次开始。换言之,从被解释的对象开始就意味着从符号链的某一点开始,这一点不可能被看作符号过程的起点。我们无法对被解释的符号进行理论上的抽象化,从而解释符号过程的运行。
例如,皮肤上的一个斑点如果可以解释为肝脏疾病的一个症状,那它就是一个符号。这在解释过程中已经是第二层次了。如果往前追溯到最初层次,皮肤官能紊乱才是机体本身遭受异常并对其作出反应的解释。皮肤官能紊乱本身已经是一种解释性响应。
当我们说符号首先是解释项的时候,我们是说,符号首先是一种响应。我们也可以说,符号是一种反应——但前提是:“反应”得理解为“解释”(这是查尔斯·莫里斯的行为主义所确立的,它与机械论相对立)。
为了避免字面的联想,我们倾向于使用“诱发—响应”这对术语,而不是“刺激—反应”。即使是对某一刺激(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诱发)所作的“直接”响应,也绝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因为这种响应要以解释为“中介”。除非我们是研究“反射作用”,否则的话,表达响应就意味着识别诱发,将其置于某一语境,使之与已知行为参数相关联(这些行为参数可能涉及简单的行为类型,如猎物—捕食猎物者模式,也可能涉及人类世界中更为复杂的与文化价值相关联的行为)。因此,符号首先是一种解释项,是一种响应,通过这种响应的解释,另外某种东西才能被看作符号,从而成为被解释项,而且,还能够生成一个开放的、由其他符号组成的符号链。
符号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多义性和单义性。信号可以定义为相对单义的符号,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种多义程度较低的符号。
I.3 配角:解释项
假如符号是符号过程中的主要演员,那么,解释项就是其必不可少的配角。
皮尔斯在其符号学理论框架中引入了解释项概念。皮尔斯认为,符号过程是一个三元过程,其成分包括符号(或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在真正的三分结构中,一个符号或再现体是第一性的,它与第二项、即对象相关;这样它就能决定第三项、即它的解释项,假定了解释项和它本身﹑以及对象在同一个三分关系中是与同一个对象相关的”(CP 2.274)。因此,符号代表某物(其对象),这种代表关系依靠的是“中介决定作用”(CP 8.343),“[这种代表关系]并不体现于所有方面,而仅仅是通过思想”(CP 2.228)。然而,符号仅仅在决定了解释项之后才能代表某物,该解释项“立即被那个对象决定”(CP 8.343):“符号在解释项符号和其对象之间作中介”,条件是,第一个符号在某一方面或思想或基础上被其对象决定,并决定着解释项,“从而让解释项与对象发生关系,对应于它本身与对象的关系”(CP 8.332)。
一个符号的解释项是另一个符号,是前一个符号在解释者心中创造的符号。这就是“一个等价的符号,或者也许是更为发达的符号”(CP 2.228)。因此,解释项符号不可能等同于被解释项符号——它不可能是一种重复——恰恰因为它是经过中介作用的、解释性的,因而是新的符号。对于前一个符号来说,解释项是一种响应,因此,它开始了一个新的符号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是更为发达的符号。解释项作为符号决定着另一符号,这另一符号反过来又充当解释项:这样,解释项通向新的符号过程,发展了符号过程,新的符号便出现了。的确,每当出现新的符号的时候,除了“第一符号”以外,还有“第三符号”,即经过了中介作用的符号、一种响应、具有解释性的新符号、一个解释项。因此,一个符号本质上就是一个解释项(参见Petrilli,1998e:I.1)。解释项(第三符号)可以是符号(第一符号),而符号(第一符号)也可以是解释项(已经是第三符号),这一事实使得符号置身于一个开放性的解释项网络之中。于是,我们就得到了皮尔斯的无限符号过程的原则,或者叫无限解释项的原则(参见CP 1.339)。
所以,符号的意义是一种响应,是一种唤起另一响应(另一解释项)的解释项。这向我们揭示了符号和符号过程的对话性。一个符号在另一个符号中获得意义,因为这另一符号对其作出了响应;而这另一符号又会得到新的符号的响应和解释,依此类推,直至无穷。
在我们的术语中,三分结构符号过程中“第一符号”——即获得意义的对象——是被解释项,而给予意义的符号是解释项。解释项主要有两类:用作识别符号的解释项叫做识别解释项,它与信号、符码和符号系统相关联;相反,符号的具体解释项——解释符号实际意义的解释项——是应答性理解解释项。第二类型的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它还表达被解释项恰当的符用意义,使被解释项逐渐介入和参与到表意过程之中。该解释项对被解释项表明立场并做出响应。
解释项这一双焦点概念吻合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皮尔斯符号学与他的实用主义密不可分。在1904年致维多利亚·维尔比的一封信(有关皮尔斯与维尔比之间的通信,参见Hardwick,1977)中,皮尔斯写道,当我们以广义看待符号时,其解释项未必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也许是一个行动或一种经历或仅仅是一种感情(参见CP 8.332)。在这一特定语境中,符号是从严格意义上去理解的。在现实中,解释项作为一种响应,它能够表意,能使得某物有意义,从而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符号,即使解释项是一个行动、一种经历或一种感情,它也必然出现了符号,出现了符号行为。我们此处讨论的是“应答性理解解释项”,因而讨论的是符号。皮尔斯在对解释项进行分类时总是偏爱三分法,区分了感情、实施和符号三个方面(参见CP 4.536)。在他一份手稿中(MS 318,其中一部分出版于CP 5.464—496,参见Short,1998),他进一步区分了“情感解释项”、“能量解释项”和“逻辑解释项”。这一个三分法和另一个三分法——“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或许是皮尔斯对解释项进行分类的最著名的两个三分法。
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对于符号类型学来说具有符号秩序意义,对于推理与论辩类型学来说具有逻辑秩序意义。究竟是像似符,是指示符,还是规约符,取决于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组织关系。由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也是根据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所以,“试推、归纳、演绎”的三分法同样取决于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