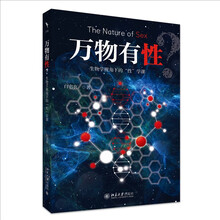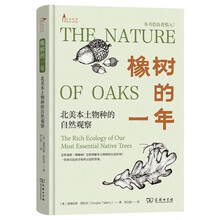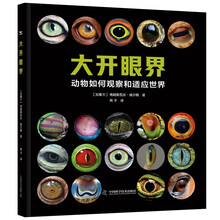世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喜爱大自然,一类不喜爱大自然。当然,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喜爱或者声称喜爱,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人应当归在第二类当中。
我属于第一类,虽然并非总能做得好。人各有志,我喜欢我的,你喜欢你的,井水不犯河水。
我在东北长白山的山沟里长大,小时候一直保持着与大自然良好的接触。在父亲并非刻意的指导下、在一本有插图的《赤脚医生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70年)的帮助下,认识了山里的许多植物,特别是当地的草药。顺便指出,类似地,奥勃罗契夫主编的《研究自己的乡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也没有过时,重视“地方性知识”的建议在当下看仍然是“先进”的!
那时,出门就是山,采蕨菜、大叶芹(鸭儿芹)、刺嫩芽,挖荠荠菜、小根蒜、孛孛丁(蒲公英)、曲麻菜(长裂苦苣菜)、山胡萝卜(羊乳)、山凳子(大花卷丹)、党参、细辛、龙胆草,捉喇蛄、狗虾、鲫呱子(鲫鱼),摘笸笸头(牛叠肚)、山葡萄、山里红,拣地甲皮(地皮菜),打山核桃,套长尾巴帘儿(灰喜鹊)等等,每项活动做起来、想起来都是那样有趣。那是“干活儿”、生活,也是游戏。有些活动还可细分,如拣蘑菇包括拣杨树蘑、小青蘑、松树伞、扫帚蘑、黏团子(牛肝菌)、玉皇蘑、榛蘑、猪嘴蘑等等,哪一片林子何时出产哪一种蘑菇,小小的我都一清二楚。并非我有什么特别本事,相关知识山里人都知道。山里人随时上山采集,就像城里人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取东西、从这家商场到那家超市购物一般。家与周围的自然世界没有严格的区分,大自然是家的延伸。冬季一到,就要上山割柴。在高山上往下放爬犁,积雪飞溅,树丛向后面快速倒去,真是刺激、好玩。那时上山从来不带水,随处可见的山泉、树液、野果、冰雪都能解渴。小时候也干些农活,用背拉犁杖(耕犁),锄草,栽土豆(马铃薯)、地瓜(红薯)、茄子、西红柿、辣椒,种苞米、烟草、韭菜、花生、向日葵、豆子(大豆),年年都要做。
儿时,我对土地就颇有好感,这种感情始终保持着。我固执地以为,人世间的一切价值最终都依附于土地,离开了土地,个人、人类就不能存活。这可能是朴素的土地情结、农民情结。读博士后,知道了拉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和利奥波德土地伦理思想后,这种感情上升为一种信念。
细想起来,当时家里的生活还是蛮艰苦的,收入很少,口粮不够吃。为防止变成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那时候山里有土地却不允许“开小片荒”(指自己开荒种地)。大自然是如此丰饶,日常所需除了按“卡片”(户口本)供给的之外,都到山上寻找。
从小长在山里,方圆十几公里的山谷、林地可以随意跑,一直到现在也不喜欢城里。后来到市里住校读高中,甚至在高考前,我也时常到中学后山上闲逛,讲给老师的理由是:到山上“背政治”效果好一些。仗着学习成绩还好,老师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二参加过一个地学夏令营,全国的总营长是地学大师侯仁之先生,吉林分营的营长是长春地质学院的董申葆先生(后来调入北京大学)。两位都是学部委员(院士)。董先生亲自带队,夏令营生活有趣极了:采化石、观玄武岩节理、量沉积岩产状、寻找水晶晶体等等。玄武岩的英文basalt就是董先生在伊通一个火山口处教我们的,自然记得颇牢。高考时毫不犹豫就报了地质学系。
我顺利考上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专业是“岩石矿物及地球化学”。1984年9月初入学,马上就赶上国庆阅兵、游行。本科期间,地质学专业学得还凑合,听了大量各学科的讲座。社会活动也没少参与,比如担任过班长、系学生会主席,与同学合作在全校创办了北大学生摄影学会。不知道为什么,几年下来,我却变得与大自然隔膜了,对数理和纯哲学发生了兴趣。由本科而硕士、博士,竟然差不多把大自然忘却了。1987年在一教听了力学系黄永念教授主讲的一门研究生课《浑沌与稳定性理论》,决定考研1988年考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阶段我关注科学意义上的浑沌(chaos)、分形(fractal)和复杂性,而这最终又把我从虚幻的理想世界引回到五彩缤纷、复杂多变、坚实可感的现实世界。1994年我博士毕业后,童年时全身心投入大自然的记忆被唤醒,再次找到亲近大自然感觉。我一直在琢磨科学哲学、科学史如何与博物学深度结合。十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意周围的花草;一有空闲,我便上山看植物。如果有一阵子没有上山,就会浑身不自在。一点一点地我发觉,还是在大自然中,我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因而也喜欢与同类人打交道。我招研究生,就明确写出了要求:首先要真的喜爱大自然。
我们的祖先是热爱大自然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有着浓厚的博物色彩。也可以不无夸张地说,中国人本来是靠博物而生存下来的。只是在最近两百年里,由于中西碰撞,受外在的压力,我们迅速抛弃了传统、遗忘了自己的文化。抛弃传统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我们的文化不够科学、没有力量,因而没有竞争优势。这套逻辑成立吗?
2011年6月我们在四川雅安的一个偏僻古镇,冷清的小街上个性鲜明、坚固而雅致的“花础”,依然散发着明清时浓浓的文化。那时的建筑,哪怕只是一个普通小村庄的建筑,也是十分讲究的。现在有多少人能解析其雕刻的含义,甚至有多少人知道那东西叫“花础”?
两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已经很难称中国人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陌生起来,空具一身皮囊。现代学校培养出来的高中生、大学生,基本读不了中国古文,读洋文也不轻松。好在我们当今使用的汉字,虽经简化,依然部分保持了原有的博物特点。比如“草芸芋艽莪芍芨荭芎葛苞荠茶荞荨菱荷萧葚菔蕨”。无需专门解释,这些汉字与认知和文化有关系,包含着分类的信息。
博物学的基本功是分类,分类也是人类所有知识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
分类,未必是当今课堂上某某学问中讲的科学分类。从知识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看,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分类,必有其依据。如今我们思考那些分类,就涉及名物学、博物学、知识社会学。看一个例子,有一组植物:茄子、椰子、梨、榆叶梅、樱花、辣椒。对此能有哪些分类呢?可以很多,比如按产地分、按用途分、按草木分、按“科”分。中间四种是木本,椰子是檄木(中国古人的一种分类),梨和樱花为乔木,榆叶梅为灌木。茄子与辣椒为茄科,椰子为棕榈科,其余三者为蔷薇科。
只钻研历史而忘却了现在,只顾及理论而不亲自实践,不划算、不聪明。
阿加西(Louis Agassiz,1807-1873)曾说:“Study nature, not books.”他的意思并非不要读书,而是不要成为书呆子,博物学家要尽可能直接探究大自然。比较平衡的说法是杂志、纸书、电子书要读,大自然这部大书更要读,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关注博物学,最好一阶与二阶同时进行,知行统一。二阶探讨指史学、哲学、社会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一阶则侧重个人体验和自然科学探究。光说不练,当然也可以,只是有些遗憾。把日常生活与花鸟鱼虫等分类结合起来,便能开拓自己的视野,找到无穷的乐趣。分类是第一步,分类与其他工作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分类能够沟通宏观与微观、人为体系与自然体系,由分类最终必然进入“演化论”(进化论),站在无机界和有机界综合演化的层面看待结构、功能、知识、目的、价值、伦理、神性等等问题。
2011年4月30日我在新浪博客中游荡,发现山东济宁一位小伙子的博客上写着:博主“闲时嗜观鸟,以观为主,以探索其习性为乐”。他是一位鸟类爱好者,列出自己观察过的“我的鸟种”:“白头鹎、白鹡鸰、斑嘴鸭、小、夜鹭、麻雀、喜鹊、灰喜鹊、云雀、达乌里寒鸦、大嘴乌鸦、灰椋鸟、珠颈斑鸠、山斑鸠、红隼、纵纹腹小鸮、大天鹅、绿翅鸭、白秋沙鸭、大山雀、棕头鸦雀、乌鸫、金翅雀、戴胜、环颈雉、家燕、绿头鸭、北红尾鸲、棕背伯劳、池鹭、青脚鹬。”我相信,在中国热衷观鸟的年轻人会越来越多。
在北京大学校园也能看到许多鸟,因为自己在观鸟方面不在行,相当多不认识。也认得若干鸟,比如喜鹊、家麻雀、灰椋鸟、鸳鸯、绿头鸭、红嘴蓝鹊、乌鸦、戴胜、灰喜鹊、灰头绿啄木鸟、大斑啄木鸟等。对于认得鸟的人,我都很羡慕。谁比我多认识一种,谁就是我的老师。只要留心,就容易发现我们生活的社区、学校,生物多样性通常比我们想象的要多。2011年据我初步统计,北京大学承泽园(仅限于铁栏和围墙圈起来的范围)共有37科70种(species)植物,特色植物有流苏树、石榴、大花野豌豆、蜡梅、君迁子、枸杞、大丁草、雀儿舌。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植物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如学生一般有的走了有的来了。
分类、博物,颇在乎名字。行博物一道,为何如此在乎名字?类似的事情,我被问过无数次。北京水毛茛、偏翅唐松草、川赤芍、金莲花、高乌头、牛扁、云南翠雀花、野棉花、白头翁、长瓣铁线莲、铁筷子,等等,都是些什么东西,简直不知所云!为何要知道这些?只是为了“显摆”一下?回答是,如果没有这些名字,恰好“不知所云”!名字是入口、是敲门砖、是钥匙。有时,当场说出几种小草的名字,就能赢得一些信任,甚至交上朋友。打个比方,就好像同学、同事在讨论美女,而你没听说过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不知道梦露、奥黛丽·赫本、费雯丽、莎朗·斯通、莫妮卡·贝鲁奇,也不晓得林徽因、章子怡、张曼玉、林凤娇、林志玲,或者你只是听说过若干名字,却把貂蝉、梦露的风流韵事错误地安排在了林徽因、林志玲头上。设想一下,那会怎样?植物与美女,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小众话题,一个是大众话题。这样看问题,是否贬低了人物而抬高了植物?非也!上述植物分属于毛茛科的11个不同的种,而上述美女都属于人科的1个种!
如果再追问下去,知道了名字又怎样?干脆的回答是:“也不怎么样!”作家狄勒德其实已经讲过了:“我想做的,并不是去学得这山谷中各种蓬勃生命的名称,而是要让自己对其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要尝试让自己时时刻刻感受其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最大力量,并留下印象。”(狄勒德,2000:166)这一回答适用于植物,也适用于美女。愿我们有同样的兴致谈论美女和植物。当然,首先要清楚谈的是哪一个、哪一位。
名称十分重要,但所有名称不过是由头、代号,是途径、方法、手段。目的吗,你知,我知。藉由名称,人们明确指称,事物的内容,以及人生理想。
对于博物学爱好者,或者对于有此意愿的朋友,可提出一项建议:按名称排列,建立自己的自然档案!用5年、10年,甚至一生的时间不断扩充之。题材可以任意选择,但不宜多。一开始,必须只能选择一个具体的题材。有收缩才有扩张,以窄见宽,稳步拓展自己的世界。只要尝试一下,就会验证这决不是虚言。
在当今时代,不鼓励采标本,但鼓励拍摄、绘画、笔记。绝对有必要购买一部还过得过去的相机。一开始,不要幻想拍得多么艺术,而是要拍得清晰,把对象的分类特征拍出来。第二步是把片子拍得漂亮一点。拍出满意的照片相当困难,可能一年当中也拍不出一张像样的片子,这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不是职业摄影师。天气不好时,要不要拍摄?一定要拍,机会可能只有一次。但要记住,好片子一定是光线组合恰当的片子,我们要尽可能找好天气外出拍摄。不要迷信在电脑上后期调整,要把功夫花在按快门的瞬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