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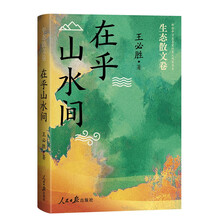


第一章
连续性
在三十二条最为神秘与奇妙的智慧之路上,上帝刻下其名号: 以色列万军之主,永生之神,仁慈而亲切,崇高,至高无上,永世长存。他用三个希伯来语同根词——数字、创作和说话——创造了这个世界。数字有十个,就像生命之树的十个圆周,还有二十二个字母,这些是所有事物的基础。
犹太人的连续性永远取决于说出与写下的词语,取决于扩展的阐释迷宫、争论和异议,还取决于独特的人类交往。在犹太会堂、学校,尤其是在家里,它总是围绕着两三代人的深入交谈而展开。
我们的连续性不是血统线,而是文本线。亚伯拉罕和撒拉、拉班•约哈南、哈梅尔恩的格里克尔以及当下作家属于同一谱系,这是种实在的感觉。这一连续性近来有些争议: 我们被告知,在现代空想家迂回地臆造出“犹太民族”之前,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好吧,我们不予苟同。并非因为我们是民族主义者。本书的目的乃是改造我们的祖辈,但还有一个目的:解释什么样的祖辈在我们看来值得加以改造。
我们并不谈论石头、氏族或染色体。你不必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或遗传学家来追溯和证实犹太人的连续性。你不必是遵守传统习俗的犹太人。你不必是犹太人。或者,因为那一缘故反犹。你只需要是个读者。
在他那首美妙的诗《犹太人》中,已故犹太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写道:
犹太人不是历史的民族。
甚至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民族,犹太人
是一个地质学意义上的民族,带有裂痕
塌方、熔岩和炽热的岩浆。
他们的编年史必须要予以衡量…
以一种不同的尺度。
地质学意义上的民族,这一独特的比喻或许也说出了其他民族的深刻真谛。这并非只是针对犹太人的。但是当我们把犹太人的连续性主要视为文本连续性时,它便强烈地与我们产生了共鸣。“历史的”、伦理的、遗传的犹太民族性乃是一个饱含裂痕与灾难的故事,一片充满地质灾害的风景。我们能否断定,比如说,罗马时期加利利犹太人的生物谱系年代?我们表示怀疑。在我们的血脉里或许流淌着许许多多皈依者、敌人、哈扎尔人与哥萨克人的血。另一方面,当今的遗传学家似乎认为某些基因已经伴随我们很久了。
这一点很有意思,但与我们的观点毫不相干。
是有血脉传承。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编年史可以衡量。但是我们“不同标准的尺度”由词语构成。这是本书所要讲述的。
……
即使精通现代希伯来语的人也会曲解《圣经》中许多词语的原意,因为这些词语在我们词汇表里所起的作用与在古希伯来语中的作用显然不同。取《诗篇》第一百零四篇第十七节“鸟在其上搭窝,鹳以松树为家”(hassida broshim beiyta)这一优美意象为例。在当今以色列人听来,这三个词语的含义是“鹳在柏树上造自己的家”。顺便一提,这使得你思考古希伯来语那迷人的简约。古希伯来语中经常凑成三词短语,将其译成英文则需要三倍数量的词语。三个词语中的每一个都是那样生动而充满韵味,它们都是名词,意蕴丰富!总之,回到我们的要点。你知道,在当今以色列,鹳并不在柏树上为自己造窝。鹳无论如何很少在这里筑巢,成千上万只鹳从欧洲迁徙到非洲,沿途需要夜间栖居时,它们显然不会选择叶子呈针状的柏树。
因此我们一定是搞错了: 要么hassida一词不是鹳,要么brosh一词不是柏树。没有关系。这个短语非常优美,我们知道它说的是一棵树和一只鸟,是对上帝伟大创造的赞美之词的一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是在赞叹自然之美。《诗篇》第一百零四篇赋予希伯来语读者的广博的意象、密集而格调优美的喜悦,可与瓦尔特•惠特曼的诗歌魅力媲美。我们不知道译文能否具有同样的感染力。
扣人心弦,妙趣横生,每页文字都在挑战人类成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马里奥•略萨
《犹太人和言语》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之间的对话,充满美妙的幽默感,以及对语言、人类和文学热情而有力的分析。真诚闪耀在这部作品的每一段文字中。
——希伯来大学学者 耶胡达•鲍尔
巧妙地将超过5000年的祈祷、歌曲、故事、争论、赞美、诅咒和笑话塞进了一只薄薄的手提箱里,这里面是一页页的什么呢?历史?人类学?文学批评?神学?所有这些,以及更多。
——美国作家 乔纳森•萨弗兰•福尔
我看到了一种传承,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思想,所有关于世界的思考都可以通过文字形式,通过美的形式传达出来。
——作家 梁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