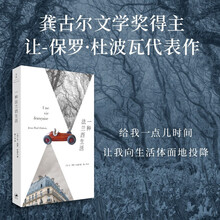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
格雷戈尔
这完全是可能的,格雷戈尔想,前提当然是如果你没有受到威胁,那么你会将一排排挺立的松树当作帷幕。就像是这样:将浅色的树干作为旗杆,在灰色天空下无声飘动着的黯绿色的旗帜,直到从远处望去,它们筑起一面酒瓶绿色的墙。几乎是黑色的、落满澳洲坚果的路可以被视为两幅幕布的接缝。如果你沿着这条路骑自行车,你就可以拉开帷幕。几分钟后,帷幕会自己打开,并将奉献给你一幅美景:城市和海岸.
但是如果你正受到威胁,格雷戈尔想,一切就都是雷同的。这些东西完全都只享有它们自己的名称而已,没有任何超出其名称的意义。
因此,只有一个事实:松林、自行车、街道。如果走过了森林,你将会看见城市和海岸一一没有表演的舞台,而是威胁的现场,将一切速冻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一栋房子还是一栋房子,一个巨浪还是一个巨浪,不多也不少。
只有到了威胁地带的那一边,离海岸七英里,到一艘驶向瑞典的船上一一假如还会有开往瑞典的船的话一一,那么海,比如说这大海,才又能与鸟的翅膀相比,或与从冰冻的深蓝飞出的巨大翅膀相比,它们在晚秋飞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至此,海只是海,一堆运动着的物体,人必须检验它是否适合承担逃亡。
不,格雷戈尔想,我是否能逃脱并不取决于海洋。大海能承担。这取决于水手和船长,取决于瑞典或丹麦的海员,取决于他们的勇气或他们的贪财,还有,如果没有瑞典或丹麦的海员,那么将取决于雷里克的同志们,取决于同志们及他们的渔船,取决于他们的洞察力和想法,甚至取决于他们的洞察力所窥见的一次历险和他们的想法所能够实施的一次简单的、扬帆的行动。格雷戈尔想,如果这件事只是取决于海,而不是人,那倒简单了。
少年
往内地去也达不到目的,少年想,他坐在河畔的柳树下。哈克贝利.芬当时是有选择的,他可以去大森林以捕猎为生,或消失在密西西比河,他选择了密西西比河。但是,他同样可以去森林里。这儿却连一片可以让人消失的森林都没有,这儿只有城市、乡村、田野、牧场和一小片树林,即使你已经走出去很远、很远。其实这一切都是扯淡,少年想,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复活节时我已经小学毕业了,而且,我已经不再相信狂野的西部故事。不过,哈克贝利.芬并不是狂野的西部故事,而人们总是千方百计想要学他的样。人必须出去。
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人必须从雷里克走出去。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在雷里克,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儿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不会遇到什么事,少年想。他看着秋天黄色的柳树叶在特雷讷河上缓缓地漂离。
赫兰德
克努岑会帮助我,赫兰德神父想,克努岑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抱怨。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一定会帮忙。
外面没有传来回声。世上没有比深秋的格奥根教堂广场更空旷的地方了。赫兰德向着空地用心地默默祈祷了片刻。向着三棵光秃秃的椴树,它们生长在耳堂和东面祭坛的那个角落,向着沉默的暗红色砖瓦墙,这墙的高度从他的工作室的窗口望出去,无法测量:格奥尔根教堂的南侧耳堂。广场地面的颜色比教堂砖头的深红褐色略浅一些,也略浅于神父寓所和紧挨着的低矮房子的色彩,那些用烧砖砌成的老房子,那些有小台阶式的外墙和釉彩空心砖屋顶的房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