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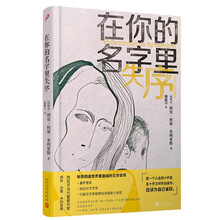



塔哈尔·本·杰伦是摩洛哥法语作家,《神圣的夜晚》是他的小说代表作,获得一九八七年度龚古尔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四十三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他也是现任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之一。他的作品都与他的阿拉伯世界有关,在用法语写作的阿拉伯作家中,他是获得较大成功的小说家,也是极力在西方世界用笔和书籍来沟通两种文化、抵抗西方对伊斯兰偏见的重要作家。
埋葬了父亲之后,女主人公离开了家,开始漫游摩洛哥,去寻找自己的女性身份。由于父亲的自私和文化习俗的禁锢,她从出生就被女扮男装养大成人,直到二十岁时,垂危的父亲才在那个“神圣的夜晚”将她解放还原。她起先在父亲葬礼上被一位王子般的骑士掳掠走,被带到一个仙境国度,但这个魔法世界很快中断。她离开王子,进入了残酷的现实生活:在树林里遭到强奸。来到海边城市阿加迪尔后,她遇到一个女人,女人有一个兄弟,从小就眼睛失明,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但嫉妒却让女人疯狂报复,导致女主人公将她杀害。她被判入狱,却毫无悔过之意,而借助重重迷梦逃走了,然而来到家中,姐妹们依然要求她扮演男性的角色……
一番忏悔之后,说书人又不见了。没有人试图挽留他,或者和他探讨。他起身收起那些经月光漂洗已发了黄的手稿,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
听他讲过故事的人此时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清楚这位一向深受爱戴的名艺人今天是怎么回事。他开讲了一段以后就撂下不管了,不是接着往下讲,反说他不该讲这个故事,因为他是个被灾星缠身的人。
有些听众已不像原先那样着迷。他们疑惑不解。他们不喜欢他这种失魂落魄、默默无语、像是在期待什么的神情。以往他们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可如今却对他失去了信任。他们确信他已失去记忆,只是不敢承认而已。这个说书人诚然已记忆衰竭,但却不乏想象力。请看证据:他仿佛突然从沙漠中走来,脸晒得黝黑,嘴唇因炎热与干渴而开裂,双手因搬运石块而变得粗糙,声音沙哑,仿佛喉咙遭受了飞沙走石的侵袭,两眼凝望高远深邃的天空。他似乎同高栖于云端宝座之上的无法看见的某个人在谈话,他朝向他,像是请他作证。听众追随他的手势和眼神。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想象那是一位骑骆驼的老者,他挥手表示不愿听艺人的叙 述。
他叽里咕噜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这并不奇怪。他讲故事的时候经常夹杂一些不知属于什么语言的词汇,还居然能巧妙地让人明白他的意图。大家也都笑了。可是此刻他尽说一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句子,舌头像许多拌有唾沫的小石子在滚动,而后又打起结来。说书人羞红了脸,他明白他并非丧失理智——他并不迷恋理智,而是丧失了听众。有一对夫妇一言不发地起身走了。接着有两个男人也嘟哝着拂袖而去。这是不祥之兆。布沙依布的听众从不中途退场。他们从未不欢而散。他把目光由高远的天际移到退席者的身上,悲哀地望着他们离去;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走,为什么不愿听他说下去。他们不再相信他了。这叫他无法接受。身为说书大师,大广场的一代名优,他曾是国王和王侯们的座上客,新一代说书艺人的宗师,而且还在麦加圣地呆过一年,他怎能去挽留那些离席的听众,或者请他们回来呢。不,布沙依布决不低声下气,屈尊俯就。“让他们去吧,”他心想,“我的忧伤没有尽头;它化成了一袋石子,我将背负它直至进入坟墓!”
我站在那里,裹在旧长袍里注视着他,一言不发。我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友情呢?我须怎样动作才不至于泄露其中的奥秘?何况我自身又是这奥秘的具体体现!我知道得太多,我在这儿露面也决非偶然。我从遥远的地方归来。我俩的目光相遇了。他的眼中闪烁着令人畏惧的智慧的光芒。他的眼神如痴如醉,难以捉摸。他顿住了。他认出了我就是那不幸年月里幽灵的化身。他倒背双手,来回踱步。我却镇定自若,像贤人般耐心等待。他越来越不安地凝神注视我。他是否认出了我?他从前并未见过我。不过他曾想象过我的脸、我的轮廓以及我的气质。那是一个充满幻觉的年代。在他的构思中,我是倔强的,难以把握的。疯狂已在他的记忆里扎了几个窟窿。疯狂或者欺诈,反正都一 样。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波折,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令我惊奇、让我反感的了。我于前一天抵达马拉喀什城,决心见见那位因讲述我的故事而断送前程的说书人。我凭直觉来到了他所在的广场,认出了他的听众。我等着他,如同人们等待一位背信弃义的朋友或一个有罪的恋人。我在谷物市场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宿了一夜,屋里满是尘埃和骡尿味。我在晨光熹微时醒来,在清真寺的池子里洗了脸。什么都没有变。一切还是老样子。长途汽车站里黑洞洞的,犹如烘面包的烤炉。咖啡馆依然没有门。侍者的胡子刮得很马虎,身上那件礼服熨了大约有上千次,油渍斑斑,亮晶晶的,头发油光可鉴,蝴蝶领结有点歪。这个侍者也装作认出了我。对顾客直呼其名是他的职业习惯。他总是那么自信。他朝我走来,像个老相识一样招呼我:
“一杯热腾腾的桂皮咖啡,外加一块玉米饼,法蒂拉大妈,老规矩……”
他走了,我甚至来不及对他说:“我不叫法蒂拉;我讨厌咖啡里放桂皮,也不喜欢你的玉米饼,而爱吃大麦 饼……”
我在一个沙乌亚地区的长途卡车司机身旁坐下吃早点,他吃着蒸羊头,一面喝一大壶薄荷苦艾茶,吃罢连连打了几个饱嗝,一边感谢真主和马拉喀什赐给他如此丰盛的早餐。他望着我,似乎想同我分享他的快乐。我微笑着挥手驱散迎面飘来的印度大麻烟的烟雾。一个骑轻便摩托车的少女从我们跟前驶过,他捋了捋小胡子,那神情仿佛在说:在这么顿美餐之后,若再有位姑娘作陪,最好是黄花闺女,那就心满意足了。
他剔完牙,把头骨架扔给了一群小乞丐,他们挤到一个僻静处,大嚼起残羹来。卡车司机上了车,掉转车头开到咖啡馆前:
“下星期见,夏洛!”他朝侍者喊 道。
走出店门的时候,我问侍者这是什么 人。
“一个粗人!他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见我这套衣服太肥,他就管我叫夏洛,他把餐桌弄得肮脏不堪,还随地吐痰。可他还自以为是招人喜欢的美男子。这都是因为有一天一个来旅游的德国女人上了他的卡车。他们干了一些肮脏的勾当,完了他整整吹嘘了一年。从那时候起,他来去经过这里都要停下来大嚼一顿羊头肉。您瞧,法蒂拉大妈,这号人最好永远不要下 车……”
广场上空无一人。犹如剧场里的舞台,人物将陆续登场。首先到达的是一些来自撒哈拉沙漠卖各种粉剂的商贩:五香粉、散沫花粉、野薄荷粉、石灰、沙子和其他一些精心研磨成粉末状的神奇的东西。接踵而来的是旧书商,他们把一些发了黄的旧书摆在摊上,并点燃了 香。
也有的人什么买卖也不做。他们席地而坐,盘起双腿等待着。说书艺人最后到达。他们各有各的规 矩。
一个干瘦的高个子男人开始解缠头巾;他抖擞了几下,一些细沙子从上面掉下来。此人来自南方。他在一只胶合板的小箱子上坐下,尽管一个听众也没有,却径自开讲起来。我远远看见他在自言自语,指手画脚,仿佛听众已围成了圈,坐得满满当当。我走过去,听见他正说道:“一群狗正在舔时光的味道。我转过身去,我看见了什么?你们说说,忠实的伙伴们,猜一猜,好人们,我面前那位骑着银色母马、威风凛凛、神气十足、身经百战的美男子是谁?时光淡而无味。面包也不新鲜。肉变了质。骆驼奶油有了哈喇味……像我们的时代一样有哈喇味。哦,过路的朋友……据说这就是生活,可是突然,孤独的秃鹫冒了出 来……”
我是唯一的听众。他打住话头朝我走来,用推心置腹的口气对我说:
“假如您在找什么人,我可以帮忙。再说也许我就是您想要找的那位。我的故事很动人。现在开讲为时尚早。我再等一等。您要找的是儿子还是丈夫?要是找儿子,他大概在印度或者中国。要是丈夫么,更好找一些。他想必上了年纪,上年纪的人喜欢在清真寺或者咖啡馆里消磨时间。不过我看您对两者都不感兴趣。您默默无语,说明……说明什么?啊!说明您心底藏着一个秘密,您不愿意再被人打搅。您是那种重视荣誉的人,不喜欢跟人饶舌。朋友,那么您走好,我招呼听众 去……”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因为我注意到一个年轻人正在打开一只箱子,动作优雅利落。他从里面拿出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边拿一边还评头品足,仿佛要再现某人的生平、某一段往事、或者某个时 期:
“我这儿有几件人生历程片断的见证。这只箱子好比一座房子。它曾经容纳过好几个人的衣物。这根拐杖已无法充当岁月的见证。说不清它已存在了多少年,它原本是古老的核桃树上的一根树枝。它大概为不少老人和独眼人引过路。它沉甸甸的,但并不神秘。现在请看这块表。上面的罗马数字已经很淡。短针停在了中午或午夜12点,只有长针在转。表面已经发黄。它的主人是生意人、征服者还是学者?这些七零八碎的鞋又是怎么回事?它们是英国制造的,主人穿着它们,走过那些不沾泥、不带土的地方。您再瞧瞧这个白铜水龙头。这准是某个大户人家的。箱子不会说话,那么只有我来问它了。现在请看这张照片。上面留下了岁月的足迹。这是一张全家福,写明‘1922年,摄于拉扎尔’。中间那位是父亲——也许是祖父。他的礼服很漂亮。他两手扶在银手杖上,两眼注视着摄影师。他的妻子缩在一边,看不太清楚。她的裙子很长。一个小男孩穿着旧衬衫,系着领结坐在母亲脚跟前。旁边有一条小狗,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一个少妇站在那儿,显得有些孤独。她长得很美。她在恋爱,正想着心上人。他不在此地,在法国或者安的列斯群岛。我喜欢想象这位少妇和她恋人的爱情故事。他们住在盖里茨高级住宅区。父亲是殖民当局的文职监督官。他和本城的帕夏1、赫赫有名的格拉维过从甚密。您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来。照片的背面写着‘某日下午好……1922年4月’。您再瞧这串念珠……这上面有珊瑚、琥珀,还有银子……大概是某个伊玛目2的,说不定夫人曾把它当项链……这儿是几枚钱币……一个带窟窿的里亚尔……一个生丁。……一个摩洛哥法郎……还有一些不再通用的钞票……这儿还有一组假牙……一把刷子……一个瓷碗……一册明信片……我不再往外拿了……把这些叫您厌烦的东西一件件往回放也够啰嗦 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扔到他的箱子里。年轻的说书人仔细看了看,又把它还给了 我:
“留着你的戒指吧!这是件稀世珠宝,来自伊斯坦布尔。我看出一些名堂,不过我不想说出来。这是一枚名贵的戒指;它饱经沧桑,满载往事,周游四海。你为什么不想留着它?它莫非是不祥的见证?不,如果你想给点什么,就请打开你的钱包,要不,就什么也不用给。你最好还是请便 吧!”
在众人不安的注视下,我默默走出人圈。我常常在路上遇见一些人,他们对我的到来、我的姿态或手势反映强烈。我心想我和他们想必具有同样的素质,同样的敏感性。我并不怨恨他们。我默默离去,确信我们的目光将会在同一激情的驱使下重新相 遇。
我正想着这家被零零碎碎从箱子里抖擞出来的法国殖民者的命运,只见一个女人在原地转圈,以便展开那当长袍穿的长长的白裹毯。用这种舞蹈姿势袒露身姿的做法有些淫荡。从她臀部几乎没有节律的微微抖动中,我顿时觉出了这一点。她慢慢举起双臂,胸部几乎也跟着颤动。看热闹的人马上围成了圈。她年纪还轻,而且很漂亮。浅褐色的眼睛大大的,皮肤呈暗棕色,双腿纤细,笑起来透出一股机灵劲儿。她到广场这个男人和几个老丐婆的天下来干什么?我们正在纳闷,她拿出一盘柏柏尔人1的音乐磁带放进了收录机里,踏了几下舞步,然后又拿起带电池的话筒对我们说起 来:
“我来自南方,来自黄昏,我从山上走下来,走呀走,我曾在枯井中歇宿,我曾穿越黑夜和沙漠,我来自时间之外的季节,我被载入了一本书里,我就是这本从未打开、从未被阅读的书,先人们把它写成,光荣归于他们,是他们派我来告诉你们,通知你们,同你们说,同你们讲。不要太靠近我。让微风去读那头几行字吧。你们什么也听不到。大家肃静,且听我道来:从前有一个以沙漠为家的贝都因民族2,他们浪漫、粗犷、豪情满怀,驼奶和椰枣是他们的食粮;在谬误的驱使下,他们臆造了本民族的神夷……他们中有些人担心有失体面,害怕蒙受羞辱,就设法摆脱那些女性后裔;他们让幼女出嫁,或者将她们活埋。这些人被罚永世受地狱之苦。伊斯兰的教义揭露了他们的罪行。真主说过:‘在你们周围的贝都因人和麦地那3的居民中,有一些执迷不悟的伪君子。你认不出他们;而我们,我们却能辨认。我们将加倍惩罚他们,他们将受到严厉的惩处。’我今天之所以用韵语隐晦曲折地同你们说话,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尽听见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它们并非记载在哪本书上,而是来自那使谬种得以流传的黑 夜……”
人群中产生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有人惊愕,有人莫名其妙。一些人低声嘟哝,旁的人耸耸肩膀。有一人高声 说:
“我们是来听音乐和看您跳舞的……这里又不是清真 寺……”
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插话 道:
“我很愿意听您讲,夫人。您不用去理他们;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同贝都因人沾亲带故!”
另一个年轻人说:
“讲故事就讲故事,不用说教!再说,从什么时候起,女人还没有上年纪就敢这样放肆?难道您没有父兄或者丈夫来管束管束 吗?”
这类议论似乎早在她意料之中,她用甜甜的、但带讥讽的口吻对这个家伙 说:
“我没有兄弟,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兄弟?要么你就当那个放纵肉欲,以至沉溺在黏糊糊、毛茸茸的大腿中间完全忘乎所以的丈夫?或者当这么个男人,他专门收集淫秽照片,冷寂难挨的时候就拿出来解解馋,压在他那性欲无处发泄的身子底下揉得皱皱巴巴的?啊!也许你是那位被狂热和羞耻断送了性命的父亲,是他这种邪恶的情感迫使你远走他乡,流落到南部荒漠?”
她笑着俯身拾起裹毯的一头系在腰上,请那年轻人拿着另一头。她缓缓地原地转圈,几乎不见双脚在挪动,直到把裹毯全都缠到了身 上:
“谢谢!真主保佑你改邪归正!你的眼睛很美;你得刮刮胡子;阳刚之气在别处,不在躯体上,大概在灵魂里!别了……我还有别的书要打开……”
她看见我,吃了一惊,对我说:
“你一声不吭,是从哪儿来的?”
不等我回答,她就扬长而去,无影无踪了。
……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梦萦魂牵,让人难以忘怀,甚至常常是引起幻觉的一部作品。——《洛杉矶时报》
这是具有诸多独创性的一位作家。——《芝加哥论坛报》
“诗一样精致的语言,阿拉伯音乐一样曼妙的韵律,神奇的意象,大悲悯的阿拉伯民族故事。完美的翻译。”——网友
“一部看过近十年都没有完全忘记的小说。”——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