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夜色慢慢加深。降临。已经开始弥漫山谷。一旦它注满谷地,流淌在平原上,一切都将变得暗淡。有一会儿,没有一点儿光亮,无论在谷地或是山谷之外。有一阵儿,山冈的微光似乎足以返照上下;随后,那些山冈也都沉入黑暗之中。
在这样的黑暗中,只有言语还能显示自己的存在。在这儿,不再留下任何负荷或实体。黑暗所能提供的唯一实体,似乎就是让它本身可以被言述。在两个人之间。两堵墙之间。
于是,开始解开衣服,如此一来,在夜的折磨中,伤口也许愈加刺痛。
坚实的年轻肌体将进入夜晚。
松软的肌体在夜间将变成一滩烂泥。
只有舌头会叙说山冈之光和地下宫殿之光。只有言语会讲述游于光亮中的单细胞生物。
越来越暗了。黑夜在我们的五脏六腑间升起,一直升到心脏和眼睛。
2
中午刚过,第一批夜工就出现在街上。虽然只是寥寥数者。
他们的工作是为夜晚降临做准备:比如,挖掘洞穴,以此作为夜色顺利聚合之处。
他们的工作也是为让人们准备夜的到来:带来年轻的肌体,让他们习惯去在夜晚需要的时候脱下衣服。为让他们适应最漫长的夜晚,用冰冷的细金属棒刺入他们赤裸的肉体,或是射入炽热的铅弹。
到了傍晚,每个人都能轻易地辨认出夜工。他们手持工具,漫步在各条街上,人数越来越多,准备入夜,准备夜的到来。
他们携带的工具,有的用铸铁制成,有的取自精心鞣制的皮革,有的用上等木料切割而成,或是用适于加工的松脂塑形而成。这些玩意儿用于捶击、撕扯、穿刺、凿挖、扭拧或击断。也可施于燃烧或破碎。
这些工具旨在专门用于年轻的躯体。
3
中午过后,这些夜工就开始四处晃悠,尽管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他们。
有传言说,夜工们喜欢方方正正的面包。也许这座大城市里不仅是他们喜欢方形面包,可是面包店师傅、烟草店老板和杂货商都认为,所有想要方形面包的人想来必定是夜工。
商店里出售各种形状的面包,圆圆的,长条的,长方形的,各样都有。下午三四点以后,孩子们放学了,生意开始忙碌起来。售出的面包越来越多——圆圆的,长条的,长方形的,椭圆形的,方方正正的。各种各样的手——纤小的,大大的,瘦骨嶙峋的,柔软的,脏兮兮的,干干净净的,长满老茧的,黏糊糊的——拿走了面包。
夜工们行走在小街深巷,查访哪些人家有圆形、长方形、椭圆形和长条面包。虽说他们的行动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但如果有人仔细观察一下,时不时就能发现他们之中的某个家伙走向某扇房门,在门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做一个并不显眼的记号。这敏锐的观察者自是大惑不解。那些被做了记号的人家,从来都不食用方形面包,不过记号并非根据面包形状的线索而标定。说实话,那些在房门做的记号多少有些随意而为。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4
其中一座山冈——不是最高的那座,也不是最显眼的那座,而是它旁边那座——矫正者蛰居于此。生活在缄默之中。
这矫正者的孤独无法估测,尤其是黄昏之后。他从窗口望出去,等待夜色铺向整个大地,暗夜先是进入洞穴,尤其是夜工挖掘的洞穴,然后铺向旷野。随着夜色逐渐变暗,他时时刻刻观察着。他看着微光从大地表面褪去,瞥向那些房屋的窗户,仍是黑黢黢的。
要阻止黑夜啮噬白昼是不可能的,但他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想着怎样去阻挠那些夜工,怎样防止光明在大地上消逝。
一个人也许不愿意相信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可是当他不得不接受现实时,生活也可以继续下去,不至把人搞得心碎神离。事实上,矫正者的孤独之苦与日俱增,如同大地每一处表面都隐入黑暗,那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在沉思良久之后仍然感觉无助,也无力解决问题。
此时此刻,唯一能够在黑暗中存活的实体,如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语言。舌头……懂得矫正者的孤独,故而言说。
更确切说,是暂时能够言说。一旦黑暗降临,笼罩了包括舌头在内的一切,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飞越这夜晚,除了猫头鹰,除了蝙蝠。除了它们的尖啸和窸窣声,什么都听不见。然后矫正者的孤独就将他封闭,犹如置于井壁。
猫头鹰,蝙蝠,以夜晚为生,乃昼盲者。
5
舌头开始苏醒,首先,要扔掉羁束……
有好长时间,它们忍着什么也不说,可是现在,它们松绑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它们的言说分若干层面。
比方说,在最低一个层面,它们说,夜工为何戴着那么奇怪的头盔?
可是如果舌头上面那双眼睛仍然能让世界进入,那么它们或许就会说起不同的话题。
头盔一直都是环闭式的,但经过一点点调整,几乎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现在的式样。头盔后部遮住了所有的头发,以及一半的脖颈。(由于衣服领子越来越高,夜工们看上去都没有脖子了。)加长的两侧只有耳垂露在外面,而前面下延至眼部,完全遮住了双眼。与此同时,夜工们还留起了髭须和络腮胡。
由于头盔遮住了脸庞的一半,髭须和络腮胡又掩盖了脸部其余部分,每一个夜工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即使没有头盔、髭须和络腮胡,他们也认不出自己的同事。不过,像他们现在这副样子,就连他们的父母也难以辨认。他们想要的就是不被人认出,除了对他们这份可怕的工作的敬畏,他们不想在人们心中引起别的认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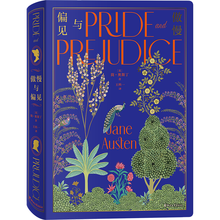


我们是现代人,这位启迪性的土耳其现代主义作家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对不确定性忍受到什么程度。他那种散点式小说对于不确定的地点、时间、声音、性别、行为人、行动和结果,都能在任何语境中引起某种联想。卡拉苏这种对比强烈的嵌镶式拼图,这种恐怖境况中有声有色的叙述,看上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博尔赫斯、贝克特和库切,然而,最主要还是得益于他本身对于“边缘照明”式写作,对于转弯抹角、旁敲侧击手法的不拘一格的天赋。真是个一锅乱炖又毫无违和感的世界!
——理查德·霍华德(美国著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
在土耳其文学的丰富宝藏中,卡拉苏的小说——讲述塞维姆(土耳其语的意思是“爱”)与塞温奇(土耳其语的意思是“欢乐”)试图在一个噩梦般的城市里存活的故事——如同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的开头部分那样唤起人们心中的感触,赋予人们官能的享受。
——玛丽·李·塞特尔(美国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