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一:
精神的界限
“您得小心些。”一位好心的朋友听说我准备谈谈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后,这样建议我。他恳切地跟我说,尽量少谈奥斯维辛,多谈思想问题。他还认为,可能的话,应该放弃把奥斯维辛放到标题里:公众对这个地理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概念过于敏感。毕竟已经有足够多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各种各样的奥斯维辛档案,讲述暴行的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我不确定我的朋友是否正确,所以我不会听从他的建议。我不觉得关于奥斯维辛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比如像说电子音乐和波恩的联邦议会那么多。我一直在考虑,把一些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作为必读书目引入高等中学的高年级是否没有必要,在处理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是否不需要总是有很多顾虑。真的,我在这儿不打算单纯地谈论奥斯维辛,不想提供什么文献报告,而是计划谈论奥斯维辛与思想的对峙。但我不会完全围绕人们所说的暴行,围绕那些事件过程。面对它们,布莱希特说过,心肠是硬的,神经是脆弱的。我的主题是:精神的界限。这些界限刚好沿着让人厌恶的暴行延伸,这不是我的过错。
我想要谈论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或者按以前的叫法,那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den geistigenMenschen),首先就必须对我的对象,也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加以定义。按照我所使用的含义,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肯定不是每一个进行所谓脑力劳动的从业者。正规的高等教育也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律师、工程师、医生,很可能还有语文学家,他们虽然聪明,甚至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非常杰出,但鲜有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一个知识分子,如我理解的,是一个在广义上的精神脉络里生活的人,与其相联系的是一个本质上人本的或者说人文学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审美意识,秉性和能力驱使他进行抽象思考。思想史上的一系列景象在每一个合适的时机都会在他脑海中浮现。如果有人问他,哪个名人的名字以“ Lilien”开头,他想到的不会是滑翔机设计者奥托·冯·利林塔尔(Otto von Lilienthal),而是诗人德特勒夫·冯·利里恩克龙(Detlev von Liliencron)。给他一个关键词“ Gesellschaft”,他理解的不是世故、善社交,而是社会学。引起短路的物理过程他没有兴趣,对宫廷田园诗人奈德哈特·冯·罗恩塔尔[1]他却了如指掌。
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个这样的人,伟大诗篇的诗行烂熟于胸,对文艺复兴和超现实主义的名作了如指掌,对哲学史和音乐史如数家珍 —我们把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置于如此境地,在那里他所面对的,要么是证明自己精神的现实性与效力,要么将其看作一无是处,那是一个极限处境,那是在奥斯维辛。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于此。我曾经以双重身份,作为犹太人和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伯根-贝尔森和其他一些集中营,除此之外还在奥斯维辛,准确地说,在附属集中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Auschwitz-Monowitz)待过一年。所以在本书中,只要我愿意的话,“我”这个小词必然常常出现,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将个人经历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
在我们的语境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与所有人,包括那些脑力工作的从业者特有的外部处境。一个糟糕的处境,以极为戏剧化的方式在强制劳动下面临的生死抉择的问题中凸显出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中的工匠,只要没有被以一个这里用不着细说的随便的理由赶进毒气室,就会得到相应的职业分配。比如有个锁匠被赋予了特权,因为当时待建的染料工业集团工厂[2]需要他,他就有机会在有遮挡的、无须暴露在恶劣天气中的工棚里干活。电工、装修工、造家具的和盖房的有同样待遇。谁要是裁缝或者鞋匠,也许就有机会到专门侍奉党卫军的房间里去干活。泥瓦匠、厨师、无线电工人和汽车技师也有最微小的机会,获得一个可以忍受的工作岗位,从而幸存下去。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遭遇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境。等待他的是和商贩一样的命运,他们都属于集中营里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会被分进一个小组,挖坑、埋线缆、搬运水泥袋和钢梁。在集中营里他成了没有职业资质的工人,不得不在野外干活,多数时候这相当于已经对他下了判决。肯定也存在差别。在前面提到的那些集中营里,化学技师仍然能从事他的本职工作,像我的狱友,来自都灵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他写了一本关于奥斯维辛的书《这是不是个人》(Ist das ein Mensch?)。医生也有可能在一个叫作医护所的地方栖身,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如此。例如来自维也纳的医生,如今已是著名心理医师的维克多 ·弗兰克(Viktor Frank)曾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长年挖掘土方。一般而言,脑力劳动者在集中营里的工作处境极为恶劣。许多人因此试图隐瞒他们的职业。谁如果掌握一点小手艺,会做些工艺,就会大胆地装成一个手工匠人。当然,一旦他说的谎暴露出来,就得担上丧命的风险。多数人把自己说得身无所长,想借此撞撞运气。人文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在被问到自己的职业时,会胆怯地说“老师”,生怕招惹党卫军士兵和牢头的羞辱。律师装成普通的书记员,记者可能谎称自己是排字工,在必须提供自己的技能证明时这样做危险较小。大学老师、律师、图书馆员、艺术史学者、国民经济学家、数学家,他们拖拽着铁轨、钢管和木材,大多数时候他们笨手笨脚,体力透支。极少数情况下,苦力劳动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他们被带离工地,送到邻近的主集中营,那里矗立着毒气室和火葬场。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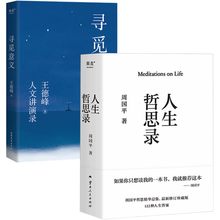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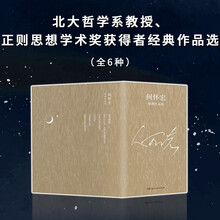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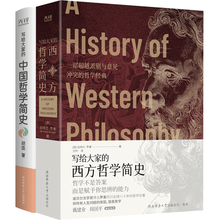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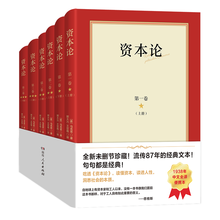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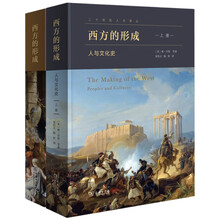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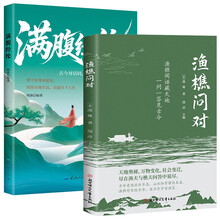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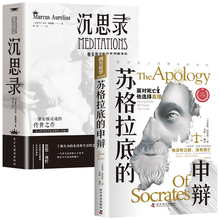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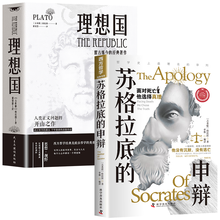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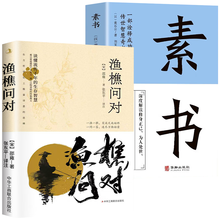
——欧文·豪(美国著名文学家、社会批评家)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道德勇气的回忆录。带着诗人的耳和小说家的眼,埃默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哲学家的奇迹,一个在纳粹统治及其大屠杀拼出的“黑暗谜语”之下的生存奇迹。
——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