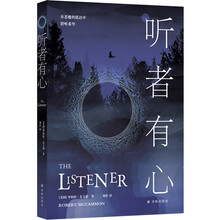《漂》:
由于流亡,我的孩子们从来就不曾是我的生命或是历史的延续。他们分别叫做帕斯卡尔和亨利,看上去也不像我。他们头发的颜色比我要浅一些,白皮肤,浓睫毛。凌晨三点,他们匍匐在我胸前吸吮,我却体会不到期待中作为母亲的喜悦。直到度过许多不眠之夜,洗了无数脏尿片,看到他们出其不意绽开的笑容,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欣喜,我母爱的天性才慢慢苏醒。
直到那时,我才真正理解在逃难的轮船上,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母亲的爱。她怀抱着的婴儿,头上长满疥疮,散发着恶臭。好几个昼夜,那个画面就定格在我眼前。船上只有一个小灯泡,悬挂在船舱上方一枚生锈的钉子上,发出毫无变化的微弱光亮。在船舱底部,你无法分清是白天还是夜晚。这缕持续的光亮保护着我们,把我们与无边的大海和广阔的天空隔离开来。坐在甲板上的人们告诉我们,大海与蓝天之间没有界限。没有人知道我们是驶向天堂还是会葬身海底。天堂与地狱同时拥抱着我们的船身。天堂,承诺人生的转折,一个崭新的未来,一段新的历史;而地狱,却展示出我们的恐惧,害怕海盗,害怕饿死,害怕吃了被机油泡过的饼干中毒,害怕断水,害怕再也站不起来,害怕在一只只手传递过来的红色尿壶里撒尿,害怕婴儿头上的疥疮会传染,害怕再也无法踏足陆地,害怕再也无法看到父母的脸庞——他们正坐在黑暗里的什么地方,消失在两百个陌生人当中。
我们的船半夜从迪石海边起锚,此前,大多数乘客只害怕一件事情:北越。这也是他们逃离的原因。
可当船只被清一色的蓝色天际所环绕,这种恐惧就变成了一头百面怪兽,锯掉了我们的双腿,让我们不再感到肌肉因长久不动而导致的麻木。恐惧中,我们被吓得一动不敢动。头上长疥疮的婴儿的尿水溅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再闭起眼睛:旁人呕吐的臭味不再让我们捂住鼻子。我们麻木了,被四周这个人的肩膀或那个人的大腿压得动弹不得,被内心的恐惧所禁锢。我们彻底瘫痪了。
恶臭弥漫的船舱里,人们都在说,有个小姑娘,在船边行走时失去平衡,掉进了大海。这故事像是麻醉剂或是欣快剂,让船舱里唯一的灯泡成了北斗星,让在机油里泡过的饼干成了奶油甜点。机油的味道停留在我们的喉咙里、舌头上、脑海中,让我们随旁边一位妇女哼着的摇篮曲昏昏睡去。
我父亲曾经打算,一旦全家被北越部队或是海盗捕获,他就用氰化钾让我们像睡美人一样长眠不醒。
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想问他,为什么没有考虑过由我们自己来选择,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生存的可能性。
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我便停止了这种追问。荣医生是西贡当年非常有名望的外科医生,他曾告诉我,他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孩子们逃亡的:五个孩子,一个接一个,从五岁的小女儿到十二岁的大儿子,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被送上了五艘不同的难民船。他把他们送到海上,远远地躲开可能面临的灾难。他以为自己肯定会死在监狱里,因为他被指控在做手术的时候杀死了几名共产党同志,可实际上,那些人从未踏足他的医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