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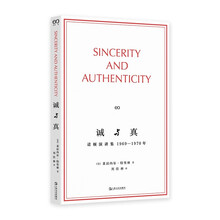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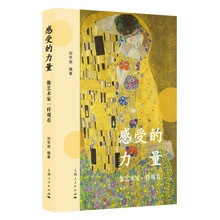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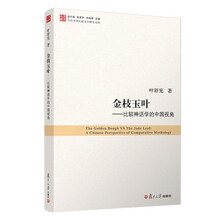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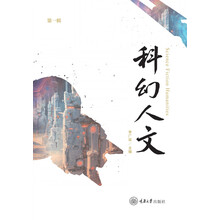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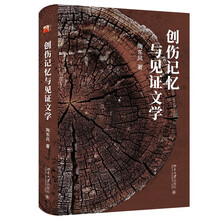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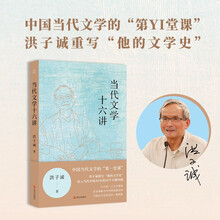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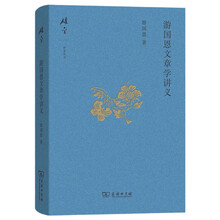
四七社是一个商标。汉斯·维尔纳·里希特于1947年创办的这个松散的作家团体人尽皆知。正是这个团体发明了文学公开活动的形式,持续而深远地影响了二战后德国的政治面貌。
你所不知道的四七社主要成员
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四七社创立者
君特·格拉斯1965年获毕希纳奖,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因里希?伯尔1967年获毕希纳奖,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保罗?策兰1958年获不来梅文学奖,1960年获毕希纳奖,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极有影响力的德语诗人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2002年获歌德奖,被称为德国“文学教皇”的评论家
君特·艾希1959年获毕希纳奖,1968年获席勒纪念奖
马丁·瓦尔泽1980年获席勒纪念奖,1981年获毕希纳奖
英格博格·巴赫曼1957年获不来梅文学奖,1964年获毕希纳奖,1968年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
彼得·汉特克1973年获毕希纳奖,1987年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1988年获不来梅文学奖,1995年获席勒纪念奖
马克斯·弗里施1958年获毕希纳奖,1965年获席勒纪念奖
汉斯·埃里希·诺萨克1961年获毕希纳奖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1963年获毕希纳奖
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1966年获毕希纳奖和不来梅文学奖
赫尔穆特·海森比特尔1969年获毕希纳奖
乌韦·约翰逊1971年获毕希纳奖
彼得·魏斯1982年获毕希纳奖和不来梅文学奖
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1983年获毕希纳奖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986年获毕希纳奖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2011年获毕希纳奖
于尔根·贝克尔1987年获不来梅文学奖,2014年获毕希纳奖
伊尔莎·艾兴格尔1955年获不来梅文学奖和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
恩斯特·云格尔1956年获不来梅文学奖,1974年获席勒纪念奖,1982年获歌德奖
西格弗里德·伦茨1962年获不来梅文学奖,1999年获歌德奖
亚历山大·克鲁格1979年、2001年获不来梅文学奖,2001年获席勒纪念奖,2003年获毕希纳奖
阿尔诺·施密特1973获歌德奖
1947年,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集结了一群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创办了四七社。很快,在四七社的旗帜下汇聚了当时德国乃至欧洲极具实力的一批作家和评论家,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马丁•瓦尔泽、英格博格•巴赫曼、保罗•策兰、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等举世瞩目的文学家在这里相继崛起,佳作如云,交相辉映。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两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多人获得毕希纳奖,四七社成为战后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学摇篮和思想重镇,一道绚丽的文学风景。德国著名评论家赫尔穆特•伯蒂格在这部饱受好评的著作里,通过深入研究几乎全部的相关作品和大量全新发现的档案文献,并访问在世的亲历者,首次深度、全面地追寻了四七社的历史风貌及其对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影响,重现了四七社创设的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准确地描绘了那些卓越人物的人生和心路历程,探索了战后德国乃至欧洲社会重建与精神重建的艰难与努力。
格拉斯文学上的成功始于四七社,而邀请他参加年会的人正是赫勒雷尔—在《音调》杂志出版格拉斯诗作之前他就向汉斯·维尔纳·里希特推荐了格拉斯。在报纸文章当中他彻底隐瞒了自己的帮助和身份。他这几年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寻找未成名的年轻作家,希望发掘新声音,他发现这位来自卡舒布地区,过着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的雕塑家、爵士乐手和诗人格拉斯是一块未经雕琢的宝石,他开始对格拉斯进行系统打磨。1955年格拉斯获邀参加四七社在柏林卢本霍恩之家举行的春季聚会还只是一个开始。纪念四七社成立50周年时曾经在柏林举办过一场专家论坛,格拉斯回忆道:“于是我就去了,之后被一群出版商围着,他们低声说了一些充满魔力的词语,比如说‘费舍尔出版社’和‘苏尔坎普出版社’,我当时想,黄金时代来了。不过我也有点疑神疑鬼的,当我离开聚会的时候,外面站了一个人,他刚刚叫了一辆出租车,他问我:‘您要去哪里?’当出租车载着我们出发的时候,他说:‘我是赫勒雷尔。我会印发几首你的诗歌。’我暗自想:‘你也就是说说而已。’不过他是唯一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其他的出版商很久都没有再联系我,直到卢赫腾汉特出版社来找我。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诗集就出版了。但是第一个在文学上认可我的人是瓦尔特·赫勒雷尔。”
50年代末,格拉斯有三年时间住在巴黎,他不时为钱所困,靠给德国广播节目写稿子勉强维持生计。而《音调》杂志一直在出版他的诗。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回忆起他在1955年与格拉斯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他看起来很鲁莽,有点儿潦倒,我感觉他绝望地就像一个乞讨的吉普赛人。”里希特一开始想“赶他出去”。两年以后,里希特再次见到格拉斯,觉得“他看起来像样一点儿了”,不过格拉斯仍然说自己“‘穷得像狗一样’。他还用文件包带了一些素描作品,要在四七社年会上出售”。里希特认为格拉斯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肯定没有机会,可是他惊讶地发现,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姆已经购买了格拉斯的一幅素描。
从这个时期开始,赫勒雷尔和格拉斯之间开始频繁通信,一直延续到赫勒雷尔2002年去世。1958年2月5日,赫勒雷尔给格拉斯写了一封信,语气不太符合他一贯的导师角色:“亲爱的君特,如果你不想让文学杂志、报纸和出版社的所有编辑都发狂的话,请你看在上帝的面上一定要习惯比较明智的校对符号。我面前摆着你诗作的样稿,印刷机很忠诚地把你标注的所有的方括号都打出来了。总共有40个之多。下次如果咱们能见面的话,我要好好给你上一堂关于校对符号的课。”
格拉斯这个绝佳的例子代表了50年代的自由职业作家如何艰难求生,利用本来就很少的机会。现在文学界很普遍的资助措施、奖项和奖学金,在当时连想都不要想。每次到了年会的时间,格拉斯就会依靠沿路搭车的方式回到德国,一家挨一家地去问电台,讨要合同。赫勒雷尔还记得,《明镜周刊》在夏天还向他证实过“这种不得安宁的租户生活状态”:“如今的诗人还一直住在阁楼里。”
自由职业作家的社会状况在四七社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有些人接到邀请之后会拒绝参会,尤其是住在北德和柏林的作家,因为年会地址大都选在南德的小城市里,交通非常不方便。阿明·艾希霍尔茨作为媒体报道记者从很早开始参加活动,他在《新日报》的一篇文章里报道了1951年在劳芬米勒举行的秋季会议,他曾经谈到与会者的经济状况:“来看看打地铺的那40个人状况如何:橡胶鞋跟、彩色袜子,可爱的领带都在脚下,有时能看到某人肚皮上的褶子,几位女士在同一天已经换上了第二条裙子……”他发现大多数人的情况“比四年前要好”。有几个人作为自由作家获得了成功,从出版社能拿到固定的工资或者“依靠尚能运转的销售系统卖故事”—也就是说,他们四处派发一些适合报纸周末特刊的故事,慢慢地积攒出一些固定客户。“专职”作家绝对是少数,埃希霍尔茨列举了几个典型的例子:瓦尔特·延斯在图宾根大学教古代哲学,阿诺尔德·鲍尔是电影评论家,汉斯·格奥尔格·布伦纳在阿伦斯巴赫民意测验研究所工作。弗兰茨·约瑟夫·施耐德在第二年,也就是1952年说服了自己的公司成为赞助商,并且开始了一个对于作家来说很有前途的工作:他在美国迈卡恩公司编写脚本。埃希霍尔茨若有所思地确认道:“为一家烟草公司写广告词的时候,他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在推敲一个句子,不过假如他能把这句话卖出去,那么每个词给他带来的收入都超过三本书的总和……”
……
引言位于市场、权力和媒体之间的文学
序幕巴恩瓦尔德湖的魔女
第一章“我们期待,耶稣基督,在黑暗的岁月里。”
战后德国文学政治概况
第二章“被世界历史唾弃。”
团体初期的混乱状况
第三章军人阶层和香槟酒的紫铜味道
1947年11月海尔林根的第二次聚会
第四章“你们醒来吧,你们的梦想很糟糕!”
作为四七社的标志性人物的君特·艾希
第五章锲而不舍的新手
里希特、安德施和媒体中的网络式联系
第六章卡夫卡小姐
艾兴格、巴赫曼、策兰:一次无法预测的新的入门经历
第七章直来直去
《文学》的小插曲和流亡者的角色
第八章“民众必须欣喜地投身于艺术!”
杂志《音调》和《文本与符号》以及重要的局外人沃尔夫冈·克彭和阿尔诺·施密特
第九章节日必须到来
奇尔切奥海角的聚会和一次始料未及的新流亡运动
第十章“你的腰间缠绕着青藤。”
从原始森林中走来:四七社庆祝成立十周年,进入新大陆
第十一章伴随着牛铃铛和鹿角,战后时代走到了尽头
君特·格拉斯令四七社成为联邦德国文学界的核心机构
第十二章巨大的棺材,巨大的矮人
吉泽拉·埃斯纳和克劳斯·罗勒的故事
第十三章“他谈到你的时候就像在说一种新的疾病。”
文学评论的胜利
第十四章从真实的袖子里钻出来
西柏林作为德国文学之都
第十五章“秘密的帝国作家协会”
《明镜周刊》事件作为四七社的转折点
第十六章兔子·刺猬·恩岑斯贝格
四七社“主导理论家”的道路
第十七章“这闻起来像是名牌货。”
德国文学国家队做客瑞典的西格蒂纳
第十八章人生历程
1965年:在社会民主与饥饿的年轻作家之间
第十九章失能的描述
通俗文学从四七社的精神中诞生:普林斯顿,1966
第二十章历史的警棍
炮仗和普尔沃米勒:最后的日子
第二十一章不合时宜的庞然大物
春天过后是寒冬:四七社也许会永存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四七社聚会列表
人名索引
译后记
在这本书里,四七社不单纯是一代人的杰作,而是展现了几代人或重叠,或相互交织在一起,有时陷入矛盾的各种政治导向和美学原则。伯蒂格塑造了彼得·魏斯、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亚历山大·克鲁格这些对四七社影响巨大的人物,他们和创建者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在文学方面的理解完全不同。在这个团体里,年轻作家不只是被批得体无完肤,像胡贝特·费希特和彼得·汉特克就通过这些论战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像赫尔穆特·海森比特尔这样的先锋派也能成为四七社奖的热门候选人;四七社里居然还出现了社会民主党选民组织的议会外反对派。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活动进行的分析令这幅群像更加丰满。本书的高潮部分在文本整理和作家肖像上。伯蒂格擅长处理数量庞杂的奇闻异事,很多重要场景塑造得尤为精彩,例如英格博格·巴赫曼1954年参加年会的趣事。作家借由读者和评论家的感受以及文学手段讲述了德国1945年之后如何对文学进行了新的塑造,以及文学公众活动这种形式是如何发明的。
——莱比锡国际书展奖颁奖词
迄今为止关于四七社的著作中*好的一本。
——约阿希姆·凯泽
有关四七社的首次视野开阔、可读性强的全面描述。让人信服,因为评论公允,既没有被敬畏束缚,也没有陷入恶意的论战。
——《世界报》
赫尔穆特·伯蒂格用他的专著证明了将真相与传说区分开来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新苏黎世报》
伯蒂格在四七社成立六十五周年之际推出了以其发展历程为研究重点的专著。让人耳目一新之处是伯蒂格将四七社的成功归于“以一种新的高超手段与媒体打交道”。
——《时代周刊》
通过伯蒂格对作家、作品和四七社从创办到1967年间活动的描述,评论家们收获颇多,那些年会甚至可以反应出联邦德国民主化的成果。另外,四七社还确定了文学经典作品的标准,塑造了包括文学评论和文学市场在内的文学生活的一种新形式。
——《南德意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