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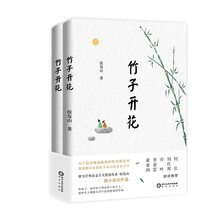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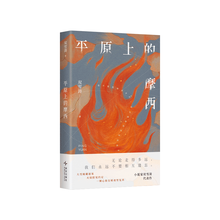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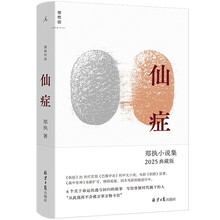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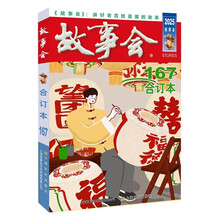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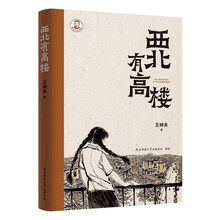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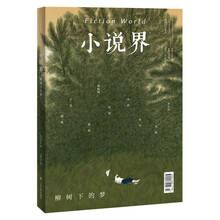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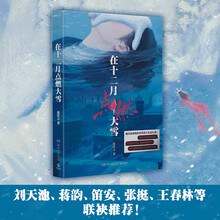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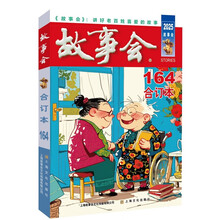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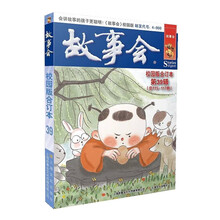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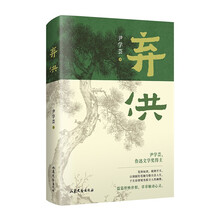
“这些短篇小说是英语文学的奇迹。”
★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国内首次完整结集
★ 炉火纯青的小说技法 幽暗跌宕的现世寓言 萦绕一生的记忆回响
★ 轻松跨越巴别塔的文字魔法师
★ 他捕捉世界瞬息万变的光影,在这个时代无人能及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本书为其短篇小说作品在国内首次完整结集,被称为“英语文学的奇迹”。
68则幽暗而充满魔力的故事中,纳博科夫完美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技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智力游戏,以及对生命中无从躲避的暧昧和失落的迷人洞察。夜晚书桌前的男人被一位不速之客惊扰,原来是来自故乡的木精灵;失散已久的儿子与母亲重逢,却现身在无比尴尬的时刻;名为“剃刀”的流亡理发师给曾经迫害过他的男人刮脸;新郎在蜜月结束后不得不向岳父报告新娘的死讯;羞涩的梦想家与恶魔做了灵魂的交易……纳博科夫一生中所关注的命运主题:怀旧与讽刺、时间与死亡、流亡者的日常、对故国的纪念、隐晦的童年创伤、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此一一呈现。
被称为“少有的用天赋写作的作家”,纳博科夫独有的风格令人过目难忘。他保持了俄语的母语特性,又全力融合英语的活力,开辟了新的书写路线。他以令人炫目的双关,隐喻,戏仿,反讽……搭建文字的自由国度,以此反抗人性中愈演愈烈的平庸与残暴。“自莎士比亚之后,没有第二个作家对语言的浇铸与运用能够如此灵动、慧黠和创造力十足。”《每日邮报》如是评论。
厄普代克盛赞:“想象的伟力再难找到如此活力充沛的代言人。”
炉火纯青的小说技法,幽暗跌宕的现世寓言,萦绕一生的记忆回响。欢迎来到纳博科夫的小说世界。如果文字能唤起至纯的感官享受,那么舍此无它。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是文学大师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作品在国内首次完整结集。68则风格各异的短篇小说,由纳博科夫之子德米特里按照年代顺序编辑而成。夜晚书桌前的男人被一位不速之客惊扰,原来是来自故乡的木精灵;失散已久的儿子与母亲重逢,却现身在无比尴尬的时刻;名为“剃刀”的流亡理发师给曾经迫害过他的男人刮脸;新郎在蜜月结束后不得不向岳父报告新娘的死讯;羞涩的梦想家与恶魔做了灵魂的交易……在这些幽暗而充满魔力的故事中,纳博科夫完美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技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智力游戏,以及对生命中无从躲避的暧昧和失落的迷人洞察,被称为“英语文学的奇迹”。
云堡?湖
我的一位代理人—— 一个谦逊温和的单身汉,办事很有效率——在一次俄国流亡人士举办的慈善舞会上中了一张旅游券。那是在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年。柏林的夏季雨水太多(又湿又冷的天气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眼看着四周枉自绿意盎然,甚为可惜,只有麻雀一直欢叫)。他实在无心出游,但他跑到旅游局的办公处要退掉他的旅游券时,人家告诉他,要退券必须得到运输部的特许才行。到了运输部,又变了说法,说他先得到公证处领一页盖了章的文头纸,在上面写一个复杂的申请报告。另外,还得到警察局去领一个所谓“夏季未曾离城的证明”。
他颇为感慨,决定参加这次旅游。他从朋友那儿借来一个铝质水瓶,修理好自己的鞋底,买了一根皮带和一件式样奇特的法兰绒衬衫——是一种一洗就缩的蹩脚货。再说他是个小巧玲珑的男人,这样的衣服他穿太大了。他的头发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目光亲切睿智。我一时记不准他的名字了。我想,大概叫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吧。
出发前一夜,他睡得不好。为什么睡不好呢?因为他必须早起,非同寻常地早。于是床头柜上嘀嗒作响的手表便进入他的睡梦,每个梦里都有那个精致的表盘。不过,主要原因还在于一睡下就无缘无故地开始想这趟旅行。这趟旅行是一位身穿低领礼服的命运女神强行塞给他的,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会不会带来美妙刺激的快乐呢?这样的快乐和他的童年颇有共同之处,也有点像俄国抒情诗在他心中激起的兴奋,还有点像一次梦里见过的夜空美景,再就是像那位女士,别人的妻子,他已经无望地爱她七年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旅行说不定比这一切还要丰富,还要有意义。此外,他觉得人生真要有意义,就必须把某件事情或某个人作为奋斗的目标。
上午是阴天,但闷热,太阳不见出来。旅游集合点在火车站,很远,一路坐着电车晃荡过去,也挺开心的。到了一看,一起要去的有好几个人呢。他们都是谁,这些打瞌睡的人?仿佛芸芸众生对于我们而言仍是未知的。旅游券上附有说明,让上午七时到六号窗口。他按照说明过去,看见了这几个人(他们已在那儿等候,他迟到了大约三分钟)。
一个瘦长的金发年轻人,穿一身蒂罗尔服装(注: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服装,一般为粗布上衣,皮短裤,旅行靴,缀羽毛的帽子),立刻站了出来。他皮肤晒成了鸡冠花色,有一对砖红色、长着金黄色毛发的大膝盖,鼻子看上去像上过漆似的。他是旅游局派来的领队。新来的人一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一行有四个女人,四个男人),他就马上带我们朝一列藏在别的火车后面的列车走去。他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却一点也不显得吃力,脚下穿着平头钉靴子,叮叮当当走得很稳。
在一节无疑是三等车厢的空车厢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座位。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独自坐下,往嘴里放了一粒口香糖,打开一本丘特切夫的诗集。这位诗人的诗他一直想再读一遍,但现在大家要求他放下书,和大家一起说说话。一个戴眼镜的邮局老职员,头皮、脸颊、上唇都刚刚刮过,泛着青,好像是专为这次旅行把刚长出来的又密又硬的须发刮了一遍似的。他一见大家就马上宣称他去过俄国,还会点俄语——比如会说patzlui(注:拉丁文转写的俄语,吻。正确拼写应为potzlui,此处讽刺其发音不准) ——他还回忆在察里津的一些艳遇,说时挤眉弄眼的,气得他的胖太太在空中做了个反掌抽他的手势。一伙人越说越吵闹。同一个建筑公司的四名职工正在互开玩笑,闹得不可开交。其中一个是中年男人舒尔茨,一个是年轻一点的,也叫舒尔茨,另外两个是年轻女子,大嘴大屁股。红头发的那个是个风趣的寡妇,穿着一条运动裙,也知道些俄国的事情(如里加海滨)。还有一个叫施拉姆的小伙子,皮肤黑,两眼无光,人和举止都软塌塌的,有点讨人嫌。他常把话题扯开,引到此次要去的某个景点上去。他第一个发出信号,让大家说些高兴的事情。后来才知道,他是旅游局专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
机车的弯管飞转,列车疾驶入一片松林,然后舒缓地行驶在田野间。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到现在只是隐隐意识到此行的荒唐和恐怖,也许还想说服自己一切还算不错吧,所以他就尽可能地欣赏沿路飞过的景色。说来也是,窗外的风光实在迷人。大自然像旋转木马一般翻腾,多么美好啊!太阳悄悄地爬上车窗一角,突然间阳光洒满了整张黄色长椅。列车的影子紧贴在长满青草的斜坡上,疯狂地奔驰,坡上盛开的鲜花融成了一条条彩带。在一个岔道口,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等候,一脚支在地上。树木有成林的,也有独秀的,平稳冷静地闪过,展现着最新的风采。一道峡谷幽深潮湿。一段爱情的回忆,化成了一片绿茵。云朵舒卷——犹如跑在天上的灰狗。
我们两个,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和我,遇上一片风景,却不知其的地点名称,这让我们颇为感慨。这是一种对心灵的莫大威胁。看见了一条路,却没有可能知道它通向何方——瞧啊,灌木丛多么诱人!远处斜坡上,或林中空地上,偶尔出现一片迷人的景致—— 一片草坪,一块梯田——停留了片刻,如同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在肺中存留片刻一般。如此亲切善良、尽善尽美,令人不禁想停住火车,走到那儿去,永远陪伴你,我的最爱……然而上千棵山毛榉树早已疯狂地闪过车窗,在一摊灼热的阳光中旋转,于是幸福的机会又一次消失了。
每到一个车站,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总会看看一些毫无意义的小东西,观察其外形特征。也许是月台上的一摊污迹、一颗樱桃核、一截烟蒂,然后会自言自语,说他永远永远都记不起这三样小东西相互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尽管此刻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还有一次,他注意到等车的一群小孩子,他总会竭尽全力从中挑选出哪怕一处非同寻常的命运轨迹—— 一把小提琴,或是一顶花冠,或是一个螺旋桨,或是一把里拉琴。他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直到这群乡村小学的学生仿佛出现在一张旧照片上;照片上右排最后那个男孩的脸上现在打了个小白叉: 一个英雄的童年。
不过窗外的景致只能断断续续地看到。旅游局给大家发了带有歌词的音乐单,歌词如下:
别担心,别发愁,
拿起多节的手杖,站起身,
到户外大步行走,
和健壮的好伙伴一起!
踩着乡下的青草和残茬,
与健壮的好伙伴一起。
消灭了隐士和他的忧患,
让疑虑和叹息见鬼去吧!
在石楠花的乐园里,
田鼠尖叫,死亡。
让我们与结实坚韧的伙伴
一同前进,一同流汗!
这是一首大家合唱的歌。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不但不会唱,甚至连德语的歌词也念不清楚。他趁合唱声盖过一切之便,只是轻轻晃着身子,张张嘴巴,好像真的在唱一般。可是细心的施拉姆打了个手势,领队一见便突然让大家都停下来,斜眼看看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要求他一个人独唱。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清清嗓子,怯生生地唱了起来。这样独自受了一分钟罪后,大家又合唱起来。不过,他往后也就不敢不唱了。
他随身带着从俄罗斯商店里买来的自己爱吃的黄瓜,一大块面包,三个鸡蛋。傍晚时,红日西沉,照遍整个车厢。车厢像船一样颠簸,又脏又吵,每个人都被要求把自己的食物交出来,好让大家分着吃。这很简单,除了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外,大家带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们个个笑话黄瓜,说这东西吃不得,便扔出了窗外。这样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贡献不多,他分到的香肠也就比大家的少一点。
有人叫他去打牌。有人拉他到一旁,问他问题,考查他能不能在地图上指出这次旅行的路线——总而言之,所有的人都有事找他。起初还是出于好意,后来变得居心叵测,快到晚上时更加居心不良了。两个姑娘都叫格蕾塔;红头发的寡妇不知怎么的活像一只公鸡首领;施拉姆、舒尔茨,还有另一位舒尔茨,邮局职员和他的妻子,这些人渐渐凑到一起,组成了一个集体,人多手杂,想躲也躲不开。这个集体从四面八方压向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不过在某个车站上,这帮人突然全部下车了。天色已暗,但西边还挂着一缕粉红色的长云;沿着铁路的远处,射来一道刺目的光,一盏灯星星一般抖动在机车缓缓喷出的烟雾中;蟋蟀在黑暗中鸣叫;不知什么地方传来茉莉和干草的香味;我的爱。
他们在一个破败的小旅馆里过夜。一只成熟的臭虫令人生畏,不过柔软光滑的蠹虫动起来倒有几分优雅。邮局职员跟他妻子分开歇息,妻子被安排跟寡妇睡,他则跟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睡。两张床占据了整个房间。被子在床上,夜壶在床下。那职员说,不知怎么的他就是不困,于是讲开了自己在俄国的冒险经历,比火车上说的更详尽。他是个强壮汉子干劲十足,性子倔强,穿着一条长长的棉布衬裤,肮脏的脚趾上长着珍珠母色的爪子,肥硕的胸膛中间覆着熊一样的毛。天花板上一只飞蛾窜来窜去,和它自己的影子嬉戏。“在察里津,”邮局职员说道,“现在有三所学校。一所是德国人的,一所是捷克人的,一所是中国人的。话说回来,这都是我姐夫说的。他当时去那里造拖拉机。”
第二天,从一大早直到下午五点,他们都在一条公路上扬尘飞驰,起起伏伏过了一山又一山,然后上了一条绿色之路,两边是茂密的冷杉树。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负担最轻,便分到一块大大的圆面包,必须夹在臂下。真恨死人了,每天的口粮!不过,他见多识广的眼睛依然没放过应该注意的事物。衬着冷杉树昏暗的背景,一片干枯的针状叶悬垂在一根看不见的线上。
他们又挤进了火车,然后那节无隔间的小车厢又空了。另一个舒尔茨开始教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弹曼陀林。到处一片笑声。他们厌倦了这种玩法时,又想出了一种好玩的游戏,让施拉姆担任监督。游戏是这样玩的: 女人们各选一张长凳,在长凳上躺下来,长凳下面则是事先藏在那里的男人。凳子下面时不时会探出一张红脸和两只耳朵,要么伸出一只摊开的大手掌,手指头做出要撩女人裙裾的样子(这时会吓出一片尖叫声),然后就知道凳子上下谁和谁配成了一对。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三次躺在黑暗肮脏的凳子底下,每次爬出来时,都发现凳子上空无一人。大家公认他游戏玩输了,逼他吃了一个烟蒂。
他们在一间谷仓的草垫上过夜,一大早又徒步出发了。一路上是冷杉、峡谷、激流飞溅的溪水。天气热,还要不停地高声唱歌,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累得筋疲力尽。中午小憩时,他倒头就睡,直到他们开始拍打他身上其实并不存在的马蝇时,他才醒了过来。又走了一个钟头后,他曾在梦中隐约见到的美景突然出现了。
这是一个纯净、碧蓝的湖,湖水非同一般地清澈。湖中央真真切切地倒映着一大片云彩。湖对岸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茂密,郁郁葱葱(那种翠绿越是幽深,越是诗意盎然)。山头上高耸起一座黑色的古堡,一层层参差地显现出来。当然,在欧洲中部,这种景致是常见的了。但唯有这一处——云、堡、湖三个主要景致和谐相配,独一无二,妙不可言。它的笑容,它神秘的纯净,啊,我的爱!我称心如意的最爱!——如此独特,如此熟悉,允诺已久,仿佛懂得观赏者的心情。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不禁伸手按胸,像是要看看心还在不在,好一把掏出来。
远处,施拉姆正用领队的登山杖往空中指来指去,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景致或那个景致。大家已经在草地上四散歇息,摆开业余快照的各种姿势。队长坐在一截树桩上,背对着湖,正在吃零食。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沿着湖岸静悄悄地走,来到了一所小旅馆模样的房子前。一条相当年轻的狗迎接了他,肚子贴在地上,嘴巴大张着,尾巴热情地拍打地面。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跟着狗进了屋。这是一幢斑斑驳驳的两层楼房,凸出的瓦檐犹如眼睑,一扇窗户在下面眨眼。他找到了店主,一个高个子老头,隐约像是俄国退伍老兵。他德语说得很差,柔声细语地拖着腔调,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便改说自己本国话了。但那个人听得恍惚如梦,还在说他自家的话。
楼上是一间供游客住的客房。“你知道吧,我后半辈子就要住这儿了。”据说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一进房门就这样脱口而出。房间本身并无特别的地方。相反,是再普通不过。红地板,白墙壁,墙上画着雏菊。一面小镜子,一半映着花,黄黄的一片——但眺望窗外,能清晰地看见湖,那湖上的云,那湖边的古堡,它们平静,完美,与幸福关联。如此引人入胜的美景,其真实就是它的力量。这力量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以前从没有领教过,现在一见,不用推理,不用考虑,完全被它折服,仅此而已。他灵光一闪之间,明白了就在这间小屋里,看着那片美得令他几乎落泪的景色,在这里生活,才是最终随了自己素来的心愿。真在这里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会发生些什么,这他当然不知道,但他觉得住在这里有益,充满希望,能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要住到这里来。他马上盘算开了,如何安排才能不回柏林,如何取来他的一点点财物——也就是几本书,一套蓝西装,她的照片。这样一算,事情多么简单啊!作为我的代理人,他挣了不少钱,够他维持一个流亡俄国人的中等生活。
“朋友们,”他一边叫,一边跑回到湖边的草地上,“朋友们,再见了。我要永远住在那边的那幢房子里了。我们不能一块儿继续旅行了。我不往前走了。我哪里都不去了。再见! ”
“这是怎么啦? ”领队停了片刻,怪声怪气地问。就在领队停顿的片刻间,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唇上的笑意慢慢消失了。坐在草地上的人都直起了身子,目不转睛地用冷峻的目光盯着他。
“可是为什么呀? ”他结结巴巴地说,“正是在这里……”
“住嘴! ”邮局职员突然发力,大吼道,“清醒过来吧,你这喝醉的猪! ”
“等一等,先生们。”领队说,转向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舌头舔遍了上下嘴唇。
“你可能喝醉了吧? ”他平静地说,“要不就是神志错乱了。你正在和我们一道愉快旅游呀。明天,按照预定的行程——你看看旅游券——我们就要返回柏林了。任何人——也就是说你——不和大家一起走,那是想也不要想的。我们今天还一起唱了个歌呢——想想那歌词是怎么唱的。不要再闹了!好了,孩子们,咱们继续前进。”
“到埃瓦德有啤酒,”施拉姆用亲切的声音说道,“坐五个钟头的火车。再走一段,有一个狩猎木屋,还有煤矿。有趣的事儿多着呢。”
“我要抗议,”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哀号着,“把我的包给我。我有权待在我想待的地方。可是这,这简直就是个斩首之邀! ” (注: “斩首之邀”是纳博科夫一九三八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书中主人公莫名其妙地入狱,等待着遥遥无期的死刑通知。)——他告诉我,他们抓住他的胳膊不放,他气得直喊。
“必要的话,我们就拖你走! ”领队厉声说道,“可那样一来就闹得不愉快了。我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不管你是死是活,都得带回去。”
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被连推带搡地带上了一条林中小路,像是一个可怕的童话故事一般。他连身子都转不动,只觉得身后的湖光在渐渐远去,被树木遮挡,最后彻底消失了。四周昏暗的冷杉焦躁不安,却也无可奈何。每个人都进了车厢,火车一开动,大家便动手打他——打了好久,还创造了好多打法。他们想到的花样之一是用螺丝开瓶器钻他的手掌,钻完手掌再钻脚掌。那个去过俄国的邮局职员找了一根棍子,缠上皮带,做成一根俄式刑鞭,下手之狠,好不熟练。好家伙!别的男人更喜欢用他们钉了铁片的鞋跟踩他,女人们则喜欢掐他,扇他耳光。人人打得好不过瘾。
回到柏林后,他来见我,变化太大了。他平静地坐下来,双手按膝,讲了他的故事。他口口声声说非辞职不可,求我放他走。他一口咬定干不下去了,他没有力气与人类为伍了。我当然让他走了。
一封永远没有寄达俄国的信
我那远方的美丽、亲爱的人,我以为你我分离八年多来,昔日的一切你都无法忘记,只要你还能记起我们逃学到苏沃洛夫博物馆相会时那个一点也不管我们的满头灰发、身穿天蓝色制服的门卫。那是彼得堡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去的那地方落满灰尘,非常小,太像一个精致的鼻烟盒了。就在一座士兵蜡像的背后,我俩有过多么热烈的拥吻啊!过后,我们从那古老的灰尘中出来,塔夫里切斯基公园里银色的亮光照得我们多么晕啊!彼得堡一条大街的中央立着一个稻草扎制的德国士兵模型,士兵们摇摇摆摆走在结冰的地面上,一声号令,便扑向前去,举起刺刀插入那个模型的小腹,同时发出热烈欢快的低吼声,听起来多么奇怪啊!
是的,我知道自己在以前的信里发誓不再提起过去,尤其是不提我俩共同经历过的琐事。我们这些流亡在外的作家按说应高度重视笔下话语的纯正性,然而,我在这里起笔几行,就违背了这一点,致使话语纯正性荡然无存,也让那些沉重话语影响了你轻松怀旧的雅兴。亲爱的,我真的不愿对你说起过去。
现在是夜晚。每到夜晚,人才会特别专注地观察物体的静默状态—油灯、家具、装在相框里摆在书桌上的照片。看不见的水管里时不时传来流动不畅的汩汩水声,就好像房子的嗓门上涌来呜咽声。晚上我常出去散步。街灯映在柏林潮湿的沥青马路上,光影缓缓流动,路面就像是涂了一层薄薄的黑色油脂,起皱的地方存下了小小水坑。零零星星的火警报警器上闪着暗红色的光。电车车站旁立着一个装满液体的玻璃柱,闪着黄光。不知为何,每当深夜空荡荡的电车从街角拐弯驶来、呼啸而过时,我心中总会涌起一种既幸福又忧伤的感觉。从车窗望进去,一排排棕色的电车座位在明亮的灯光下清晰可见,车上只有一个售票员,斜挎着一个小黑包,在座位间独自来来去去。每当向电车行驶相反方向走动时,他就会摇摇摇摆摆,看上去有点紧张。
我在这幽静、漆黑的街道上漫步时,喜欢听到有人回家的声音。尽管夜色中看不见那人,也事先不知道哪一家的大门会有了动静,迎接开门的钥匙。可我听得见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旋即开了,推住稍停片刻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里面又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离开房门玻璃窗很远的门厅深处闪起柔和的灯光,持续了不同寻常的一分钟。
一辆小轿车驶过,打出两道湿漉漉的光柱。是一辆黑色轿车,车窗下有一道黄色条纹。粗哑的喇叭声灌入黑夜耳里,车影从我的脚下掠过。直到现在,街上都是空无一人—只有一只老狗,爪子轻轻敲打在人行道上,好像极不情愿地陪着一位没戴帽子、打着伞、无精打采的漂亮姑娘出来散步。姑娘从一个暗红色灯泡底下走过去(灯泡在她左侧,就在火警报警器的上方),伞面上唯一一块绷紧的黑幔变成了潮湿的红色。
拐过弯,远处人行道上—太出人意料了!— 一家电影院的大门如镶了宝石一般流光溢彩。进门一看,长方形的月白银幕上能看到或多或少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哑剧演员。这时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女孩的特大脸盘,一双亮闪闪的灰色眼睛,黑色的嘴唇上几道裂缝闪闪划过。画面渐次放大,女孩凝望着昏暗的放映大厅,一行长长的晶莹泪水奇妙地从腮边滚滚而下。有时候(真是神奇一刻! )银幕上会出现真实的生活场面: 突然聚起的人群,波光粼粼的水面,一棵无声无息却看上去沙沙作响的树,让人觉察不出那是在拍电影。
再往前走,来到广场一角,一个身穿黑皮衣的矮胖妓女缓缓地走来走去。她偶尔会在一个光线刺眼的商店橱窗前驻足观望,橱窗里有一个蜡制的红唇模特,向夜色里的过客们炫耀着身上如水般湿润流淌的翠绿长裙和桃红色的鲜亮丝袜。我喜欢观察这位文静的中年妓女,只见一个留着八字胡须的老男人朝她走去,先从她身旁走了过去,然后回头望了两眼。他是这天上午从帕彭堡来此办事的。她会不慌不忙地带他去附近的一栋楼房。那栋楼在白天和周围的楼房没什么两样,都是普普通通的建筑。楼房没有亮灯的前厅里有个老门卫,彬彬有礼,但面无表情,彻夜守候在那里。一截陡峭的楼梯顶端站着一位同样面无表情的老太太,她会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打开一间空房并收取入住费。
对了,你知道吗,当火车从街道上方的桥上急驰而过时,所有的车窗灯火通明,传出欢声笑语,那是多么热闹的景象啊!那火车也许只驶往郊区,可就在那一瞬间,漆黑一片的桥下原本黑暗的世界充满了强有力的金属乐,令我不禁浮想联翩: 我在平静地、轻松愉快地等着办理签证手续,一旦盖好额外的几百个印章后,我就可以踏上奔往阳光大地的旅途。
我心情实在轻松,有时候甚至喜欢看人们在当地的咖啡馆里跳舞。我的许多流亡同伴义正词严地(愤慨之余也有一丝快乐)指责这些时下流行的丑恶现象,包括流行舞。不过流行时尚是人类平庸能力的创造物,也算生活的一个层面,平等的庸俗化身,那么,谴责它也正意味着平庸也能创造出值得关注的东西,不论那是一种政府形式还是一款新发型。当然了,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舞其实压根就不现代: 它们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的督政府时期,那时的妇女和现在的一样,衣服就是紧贴皮肤而穿,乐手也是黑人。流行时尚每个世纪都有: 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清一色地流行拱形裙,后来烟消云散,代之以紧身裙和贴面舞。我们跳的那舞,毕竟是极其自然、极其纯真的。有时候—在伦敦的舞厅—单调中体现着完美的优雅境界。我们都记得普希金这样描述过华尔兹:“单调而又疯狂”。万事莫不如此,道德堕落也不例外……这里有我在达格利寇侯爵的回忆录中读到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小步舞更颓废的了,可在我们的城市里,大家都认为跳这种舞是无伤大雅的。”
所以说,我喜欢看在咖啡厅里跳舞的人,再次借用普希金的一句话:“他们一对一对地婆娑而过。”眼妆画得很有趣,闪烁着最简单的人间快乐。穿着黑色裤子和浅色长筒袜的腿相互碰撞。脚步来回转动。与此同时,门外等候着我忠实的、孤独的黑夜和它潮湿的影子,还有喇叭鸣响的汽车,滚滚的寒风。
前言
纳博科夫手拟篇目单
木精灵
这里说俄语
声音
振翅一击
众神
纯属偶然的事情
海港
报复
仁慈
落日详情
雷雨
威尼斯女郎
巴赫曼
龙
圣诞节
一封永远没有寄达俄国的信
斗
乔尔布归来
柏林向导
一则童话
恐惧
剃刀
旅客
门铃声
事关面子
圣诞故事
土豆小矮人
昆虫采集家
风流成性
倒霉的一天
博物馆之行
忙人
未知的领域
重逢
嘴对嘴
菠菜
音乐
完美
海军部大厦塔尖
列奥纳多
纪念希加耶夫
循环
俄罗斯美女
婉言相告
滞烟
新遇
一段生活
菲雅尔塔的春天
云?堡?湖
被摧毁的暴君
利克
O小姐
瓦西里?希什科夫
极北之国
单王
助理制片人
“那曾是在阿勒颇……”
被遗忘的诗人
似水流年
谈话片段,一九四五年
符号与象征
初恋
连体怪物的生活情景
费恩姐妹
兰斯
复活节之雨
词语
娜塔莎
注释
附录
想象的伟力再难找到如此活力充沛的代言人。——约翰·厄普代克
货真价实的魔术师。——保罗·贝利
多么荣幸,他选择使用我们的语言并使之焕然一新。——安东尼·伯吉斯
纳博科夫的感受力之强大、丰盈和多姿多彩,在现代小说家中无可匹敌,鹤立鸡群……
如果文字能唤起至纯的感官愉悦,那么舍此无它。
——马丁·艾米斯
他对小说创作的各色招式驾轻就熟,还发明了属于自己的新技法。——彼得·阿克罗伊德
自莎士比亚之后,没有第二个作家对语言的浇铸与运用能够如此灵动、慧黠和创造力十足。——《每日邮报》
这部全集把读者们带向他的魔法……那些知道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而忘了他的短篇故事的人们,如今得到了一件珍贵的礼物。
——《洛杉矶时报书评》
我们时代*原创性和创造力的作家。——《金融时报》
纳博科夫的天赋不仅在于他能将一切主题都转化成清晰的视觉意象,还有近乎放肆的幽默感,任何悲剧在他笔下都能荒诞毕现。——《观察者》
鲜活的记忆萦绕其中,面对命运的恶意嘲讽,或游戏其间,或与之抗争……纳博科夫幽暗跌宕的故事之中闪烁着救赎的微光。——《新闻日报》
这些短篇小说是英语文学的奇迹。——《旧金山纪事报》
他所使用的语言是一件神奇的工具,微妙至极,却又充满力量:我们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作者,包括乔伊斯,能像他这样,捕捉世界瞬息万变的光影。——《波士顿环球报》
天才之作……遣词造句,精雕细琢,奔泻无隘,直抵始终如一的独造意象,于无形中将思维的逻辑演绎到了极致。——《沃斯堡星报》
任何一个认为人、人的思想及缺陷极为重要的个体,自能发现其中的意趣。——《里士满时讯报》
纳博科夫极致丰富的描写,令人炫目,他亲切地呼唤着过去,并着力刻画意识的奇谲之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塑造个人经历并赋予其意义上,心灵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纳博科夫对其刻画之生动、探索之灵活有力,无人能出其右,由此推及,对于理解和包容个人的经历,亦无人能与他比肩。——《华盛顿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