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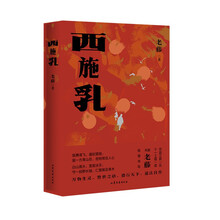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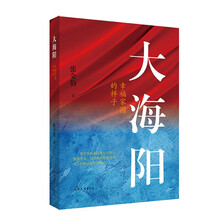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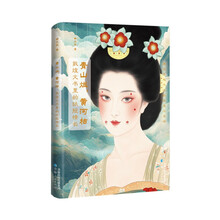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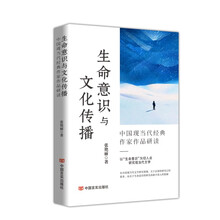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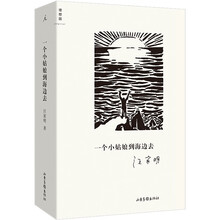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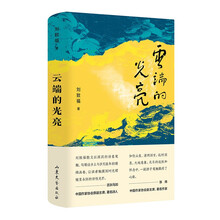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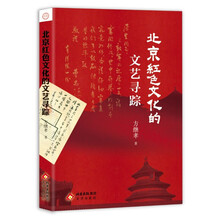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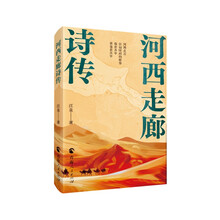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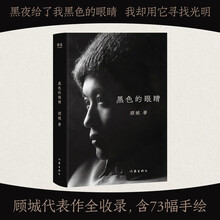
小说《时间》选取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叙述策略,作者设定了从年龄(三十七岁)到人生阅历、知识程度都与自己大体相仿的陈英谛为叙述者,讲述其在南京沦陷后的浩劫中历尽劫难,家破人亡的故事。小说通篇由主人公在屠城前后跨度约十个月间的日记构成。作者堀田善卫在公开出版的相关资料极为有限、历史研究完全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多方搜集并查阅了各类文献,构思了这部告发日本战争罪恶、传达大屠杀受难者声音的文学作品。尤为重要的是,堀田善卫参照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中检方举证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主人公蒙难经历的部分细节,就依据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的法庭证词。作者还特意让在东京审判上出庭作证的检方证人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原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迈纳·贝茨(贝德士)、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以及他们的证词中多次提到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等第三方的见证者,以各自真实的姓名和身份出现在小说中,还原出了历史现场特有的真实感。
十二月十日
日军已经完全包围了南京城。
汤山、雨花台正处于激战之中。
牛耳山也同样。
将军山一带的水泥碉堡群,也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之下,大半已被摧毁。
朱盘山一带,据说草木被鲜血染成殷红,尸体堆积成山。
日军将俘虏全部杀死。据说,是用军刀乱砍致死,因此满地僵尸都是遍体鳞伤。应该是屡次被砍所致,或者不只被一人所砍。
又云,日军杀到了麒麟门,中华门危急。
枪声炮声盖住了城内城外,任何地方都听不到人声。
我们五个人——挺着大肚子的莫愁、杨小姐、英武、佣人洪妈和我,都聚拢到一间屋子里,偶尔的交谈也都是寥寥数语。其间,即便是眼下,玻璃也在无时不刻地被震动着。我们的心,也完全一样。
下午三时许,炮声骤然停息,出现了一段真空般的时间,我走到院子,观望了十来分钟。杨小姐和英武也跟了出来。
我下意识地捡起了一片枫树的枯叶。
英武和杨小姐也学着我去捡。我心里正想,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是奇妙,英武突然对我说:
“爸爸!真漂亮啊!”
听了这话,我几乎惊愕了!心里扑通一下。这个五岁的孩子……。
我在心里,其实也正想着同样的事。杨小姐用她一双湿润的大眼睛告诉我,她也同样为此而吃惊。
我们的人生和生命,已经再无法用自己的手去控制和把握……。我们此刻度过的这段时间,异常接近于被宣告死亡之人所独有的时间……。
或者,也可以说,现在,我们是在透过“死”来凝望“生”。
我们在透过“死亡”的透明玻璃,观看着一切物事与风景。
——“爸爸!真漂亮啊!”
叶脉从整体到细部,清晰、完整。简直是完美的。
我们的“生”,仿佛也一览无余地看得见叶脉上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的确,一片平凡的枫叶,和这片承载着枫叶的纹丝不动的大地,从没有像眼前这样,显得如此这般的、难以置信的丰饶和美丽。
我又转过头去,眺望了一眼紫金山。这座危岩万仞的高山巍然屹立,焕发着人类视线所及的极限处的天地之涯的天堂抑或地狱般的极致之美。
如同一个即将踏上不归之旅的启程者,我一次又一次地抬眼眺望那座山峰。如果我是诗人,一定会题写一首“永诀之秋”的诗句。
不论是树叶,还是碎玻璃片,所有闪光之物都昭示着,时间是人所不及、枪炮与刺刀也无法触及的永恒,以光耀的形式而存在的。一枚红叶、碎玻璃片、紫金山,这些事物如今全部是同格和同质的。
枪炮声又从南、北、东三个方向震天动地地响起,我让英武和杨小姐回到房间,独自蹲在门廊下陷入了沉思。
我应该永远都不会忘记此刻看到的,永恒被凝结于一丝光耀之中的这一瞬间的风景。
爸爸!真漂亮啊!……
如果这句话并非是在眼下的危机时刻,而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也仍然被人相信吗?如果,那只被认为是映现于一双惊恐的眼膜上的一种幻觉,那么,我关于异常与日常并无差别的思考的前提和结论就将被推翻,只要它与人有关。
然而——
然而,然而。
我不吝承认这是一种美,可是,这种美,只有在人的心灵被某种东西吞没后才会出现。那种光耀所带来的,不是光亮所常有的温暖,而是冰一样刺骨的寒冷和切肤之痛。
年仅五岁的英武,先于任何人感知到了这种美,这让我想起了早亡的友人P。P在游学法国时,死于汽车事故。不知为何,他在中国文学和西欧古典文学中,独爱那些夭折的文士和诗人的作品。他最喜爱中国的李长吉和法国的兰波、洛特雷阿蒙等颓废派诗人。“在幼儿的眼中,有着整个宇宙的全部历史。”这是P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认可这句多少带有伤感的话。因为,我除了付之一笑,就只能承认他是对的。如果P此刻能站在这里,他可能会说,在一块玻璃碎片的光耀里,能看到整个宇宙的兴衰。在与死相邻的时候,通过死亡而看到的风景里,他有可能会看到堪称“真理”的东西。
这种美和真理,是在日常生活已不能维持的状况下,当人被某种东西所吞噬之后,才得以成立的。而且,这种美和真理,理应也会吞噬沉迷其中的人。
只有陷入这种状态中,才能感知到的无情之美。古人说美是苦难所生,如果这种美只有在危难之际才能被感知,我毋宁说,我憎恨这种美。美的实态,并非轻而易举地窥见得到的。那也许根本不是什么美妙之事……。P对我讲过,在普法战争中,当普鲁士军队包围了巴黎之后,巴黎的文人被强烈的唯美思想所迷惑。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德国诗人普拉滕的诗句:
谁用眼睛观察美,
他就将自己交给了死神,
他再也不能在尘间尽人事。
我们不是“不能尽人事”,而是连在“人世间”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就好像在战争的大气层中,所有物体都被剥去了表层的覆盖,袒露出了赤裸的实体。竟有如此唯美之诗,让人意外。
我虽然喜爱这首诗,但并不认同这种美学观,因为从根本上,美包含着阻断了人生的东西,因而往往有某种绝望投射其中。自然与自然之美,不是被人所意志的美。因为,自然是非意志性的,换言之,自然也是令人绝望的。如果死意味着遵从自然法则,那么,只有遵从这种绝望的法则,才能看得到美……。
但是,我写这部手记,不是将其作为追寻美的产物而写,而是作为我的自由(?)意志的诗篇而写。
我忍受着对“自由”这一词语的不快,所以在它的后面加上了问号,或者说不得不加上了问号。在这部手记的最后,我还能有自由地使用“自由”一词的权利吗?
作者堀田善卫之女致中国读者
译者序:用“鼎的话语”刻写时间
正文
代后记:《时间》
堀田善卫要以小说的方式提醒日本国民,没有从受害者角度反思战争,清算责任,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日本就不会有未来。从这一点来说,《时间》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