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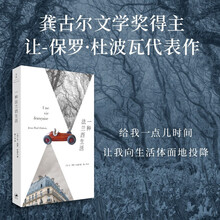

深夜,男孩离开了村庄。逃!他知道自己必须逃走,离开家,离开沉默的父亲和哭泣的母亲。男孩瑟瑟发抖地躲在一人高的地洞里,头顶上是追捕他的人群咚咚跺响的脚步声和摇曳的火把光。他饥肠辘辘,奄奄一息,直到遇到了那个老牧羊人和他的一头驴、一条狗、九只羊。一老一少在这贫瘠、严酷的荒野中相依为命,生活简化为简单的三个字:活下去!他从未对老牧羊人讲述过自己悲惨的过往,然而,当马蹄声在漫天的灰尘中响起,牧羊人还是明白了一切……
这是一趟自我追寻与救赎的人生旅程,也是一则关于善恶和信仰的当代寓言。
人们在呼唤他。从洞口传来的回音好似蟋蟀鸣叫,他试着由此确定每个人在橄榄树林里的位置。那叫嚷声犹如燃烧的岩蔷薇的哭号。他侧躺着,身体呈之字形,缩在几乎没有多余空间可以移动的土洞里面。他的两只手或环抱膝盖,或枕在头下,还在旁边的壁上掏了一个小小的如同壁龛的洞,勉强塞得下装口粮的背包。他先在洞口铺上两根通常拿来当横梁的粗树干,再覆盖整枝剪下的枝丫。他伸长脖子,支着头,希望听清楚一点。他眯着眼,竖耳聆听那逼他非逃不可的声音。什么都没听见,连狗叫声也听不见,他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只有训练有素的狗才能发现他躲在哪里。或许是枪猎犬或者优秀的拉戈托罗马阁挪露犬。又或许是猎兔犬,这种狗长耳短腿,他曾在来自首都的报纸上见过。
幸运的是,那些异国品种并不适合这片平原,这里只有格雷伊猎犬的踪迹。它们颀长的骨架只覆盖着一层精实的肉。这种神秘的狗会全速追捕野兔,鼻子无时无刻不在嗅闻。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任务就是追捕猎物,然后撕裂它们。它们身体两侧火焰般的红色条纹,恍若主人抽打后留下的伤疤。这片干旱的土地在孩童、女人以及狗的身上都烙下同样的痕迹。不管怎样,它们跑得再快也没用,因为他会一直缩在这个小土洞里。这个属于蚯蚓和往生者的世界,充斥着上百种能掩盖他踪迹的气味。这是他本来不会闻到的气味,让他远离母亲的气 味,都是他自找的。
每每看到格雷伊猎犬或想到这种动物,他就想起村里的一个男人。他身体残障,驼着背的模样像极了手风琴演奏者。他靠一辆三轮车行遍大街小巷,车子前面有个手把,可以控制方向。每当太阳西下,他便离开村庄,往北边地面平坦的道路而去,那是三轮车唯一能走的路。一群狗跟在他身边保护,狗的脖子上都绑着已脱线的绳索。看到那个男人乘坐笨重的车子前进的画面,他感到很心酸,也很好奇,不明白那个男人为何不让狗拉着车子前进。他记得曾在学校听过有关他的传言:当他不想要哪条狗时,就把它吊死在橄榄树上。在他不算长的人生里,已见过几十具狗尸吊在远处的橄榄树上,那一副副骨头脱臼的皮囊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蛹。
他感觉那些人就在附近,于是他打算保持安静。他听见自己的名字一遍遍地回荡在树林里,仿佛打在水面上的雨点。他蜷缩在土洞里,心想,这或许是他仅有的安慰吧:在破晓时分聆听呼唤他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回荡在橄榄树之间。他听出酒馆老板的声音,还有夏季时节会在村里落脚的某个脚夫的声音。他不知道还有哪些人,但他猜想邮差和编草匠也在其中。他感觉心底意外地涌出一股潮湿而温热的欢欣,孩童那种难以表达的、无声的确幸让他感到一种仿佛鸡皮疙瘩掉满地的快乐。他不禁问自己,他们也曾这样找过他的哥哥吗?他是否也引来这么多人找寻他的下落?在一片叫唤声当中,他感觉自己也许重新凝结了村庄蒙尘已久的团结。瞬间,他的怨恨退到内心的某个角落。他让村里的男人都聚在一起了,这些男人有着强壮的古铜色胳膊,以犁耕地,把种子播满崎岖的耕地。他引爆了一个事件,他心想,这次事件让旧时仇敌都不得不挽起袖子,肩并肩地团结起来。他问自己,这一刻在几年或几个礼拜过后,是不是还会留下痕迹,是不是会变成弥撒结束后或酒馆里闲聊的话题。这时,他的思绪飘向父亲,想象着他到处解释。他看见他一如既往地装可怜。他努力想说服所有的人,他的孩子外出打石鸡,一定是掉进某处看不见的井里了;说厄运老缠着他们家不放,上帝从他身上割走了一块肉。他摇了摇埋在膝间的头,想甩开满脑子的胡思乱想。父亲卑躬屈膝的模样再一次回到他的脑海中,治安官的身影也跟着浮现。这幅画面尤其勾起他内心的恐慌。他努力竖耳细听,始终没听见治安官的声音,但即便听不到,他仍感到无比恐惧。他想象着那个男人嘴里叼根烟,跟在拍打着橄榄树的人群后面。他踢着泥块或懒懒地弯腰捡拾橄榄,那是最后一批打果子时漏下的。他怀表的链子垂露在罩衫外。他头戴棕色毡帽,领口紧系,留着用糖水定型的八字胡。
离洞口几米远的地方传来某个男人的声音,将他从沉思中唤醒。是老师,他正在跟另一个离他不远的人说话。少年发现自己心跳加速,血管里的血液疯狂奔窜。苦痛,在蜷缩了数小时后,从他体内喷涌而出。他想马上爬出去,结束这种不舒服。他没杀人,没偷,没抢,更没冒犯上帝。他想拨开盖住洞口的树枝,让附近的人发现他。或许其中一人会叫同伴安静,然后转过头细听发出窸窣声的方向。他们俩会交换目光,蹑手蹑脚地靠近树枝堆,猜想着找到的是兔子还是那个失踪的孩子。他们会拿开树枝,看见他整个人缩在洞里头。他想假装昏迷不醒,满身泥巴,衣服湿透,头发肮脏,就是他手里的王牌。其他人听到他们的叫声后都赶了过来。第一时间赶到的是他的父亲,他气喘吁吁,情绪激动,但欣喜若狂。接着大家将他团团围住,如同一圈旋涡,害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时有人点燃火把,火苗熊熊燃烧,而不是木头将烧尽的点点火光。他们会在一片欢呼声中把他挖出来,一双双强而有力的手臂扬起薄薄的一层灰。接着,他被放上担架。人们高唱农歌,畅饮温热的葡萄酒,回到村里。父亲粗糙的手搁在他黝黑的小小胸膛上。一场快乐的庆祝活动拉开序幕,吸引所有的人聚在酒馆。然后,每个人回到自己的家,支撑屋顶的厚实石墙冷却了见证一切的厅堂。这些便是父亲磨损不堪的腰带挥舞起来的前奏,铜扣划破厨房腐臭的空气是如此快速,来不及看到它的闪光。他讨厌自己那副蜷起身体的凄惨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