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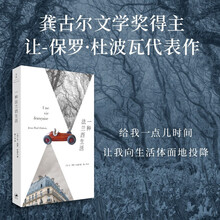

《人虎》写一桩离奇的少年杀人案,由此描述了印尼的乡镇生活、家庭纠葛、男女爱情,以及人性的复杂。受印尼口述故事的传统形式影响,小说开篇便交代了杀人案的凶手和遇害者,之后才层层剥茧,道出酿成这起悲剧的原因。这使得整个故事更加扑朔迷离、扣人心弦,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下去。
在小说中,作者埃卡•古尼阿弯完美呈现了印尼村镇的自然及人文风貌,并将魔幻现实主义和印尼民间传说融入其中,碰撞出精彩的火花。读完《人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文学批评家会将埃卡•古尼阿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提并论。
——本书责编
大胆、老辣、幽默,埃卡•古尼阿弯可能是当代东南亚zui雄心勃勃的作家。其小说《人虎》围绕一个谋杀之谜展开。尽管开篇di一句话就揭露了凶手和遇害者,凶手的杀人动机也并不神秘,然而整个故事仍让读者感到痴迷。这证明了埃卡•古尼阿弯极高的写作天赋,特别是他制造悬念和紧张故事情节的技巧。小说的主人公,少年马吉欧,其实可以看作是生活在爪哇岛上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只不过他没有亲自动手杀人,一切都是住在他体内的那只白色的雌虎干的。
埃卡•古尼阿弯称《人虎》中有他自己的影子,他说:“我和马吉欧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在印度尼西亚,我们保持愤怒,也压制愤怒。但zui后,心中的猛虎往往会挣脱牢笼,一跃而出,我们对此却束手无策。”
这种对“个体”而非“政治”的关心,以及小说中体现的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抗拒,使埃卡•古尼阿弯摆脱了印尼大作家普兰莫迪亚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束缚。在荷兰殖民统治的末期,普兰莫迪亚希望通过写作唤醒印尼人的身份认同,因此被誉为印尼的爱弥尔•左拉。而埃卡•古尼阿弯正逐渐成长为印尼的村上春树:其作品运用大量的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侧面揭露了印尼的社会百态。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编辑
这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海滨小镇里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马吉欧,无论怎么看都与常人无异的少年,却声称自己体内住着一头白色的雌虎——这源于印度尼西亚古老的传说。生活的困苦与家人的背叛折磨着这个不幸的少年,彻底被激怒的他无法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或者如他所说,身体内的白虎一跃而出——咬死了自己心爱女孩的父亲。随着故事发展,这次暴力事件背后隐藏的令人心碎的真相才被一一揭开。
初遇白虎
那头雌虎和天鹅一样白,比豺狗更凶猛。玛梅曾经看见过一次,雌虎如影子一般从马吉欧体内冒出来,稍纵即逝。此后,她就没再看见过。可以看得出雌虎仍然潜伏在马吉欧体内,但是玛梅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发现那是什么。黑暗中一双虎眼在马吉欧的瞳孔中闪烁着黄色的光芒。最初玛梅被吓得不敢直视那双眼睛,害怕雌虎真的会从里面再跳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玛梅见多了,对那双在黑暗中闪烁的眼睛已经习以为常,也就不再为此感到忧虑了。雌虎不是她的敌人,也不会伤害她,也许它是在那儿保护他们所有人。
马吉欧离家出走的几星期前偶然看到了它。那是一个清晨,当时他独自一人在礼拜室里睡觉,雌虎舞动的尾巴轻轻拂着他的一双赤脚,把他弄醒了。他以为那是马·索马在拍他,叫他起来和自己一起做礼拜。他睁开眼睛,没看到托盘上有热气腾腾的咖啡,饭盘里也没有炒米饭,却看到一头白虎卧在他身边舔着虎爪。已是拂晓时分,天色明亮,空气湿润。显然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雨,这时还没有人来做礼拜。马吉欧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所能做的只是敬畏地盯着那头正在满心欢喜地打扮着自己的壮硕的野兽。
他知道这野兽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星球上活着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在小镇郊外的丛林中游荡,但从来没看过这种野兽。他见过野猪、身上斑斑点点的小猎豹和豺狗,却从来没见过几乎像牛那么大的白虎。他流下了泪水,慢慢伸出一只手摸着雌虎的前爪。那似乎又是真的老虎,虎毛柔软得有如鸡毛掸。雌虎将爪子缩回去向他示好。就在虎爪抬起来时马吉欧再次把手伸过去,雌虎有意与他玩笑,像猫那样用虎爪轻拍了他一下。马吉欧试着去抓雌虎的爪子,但它躲开了,翻身爬起,伏身到另一边做出准备发起攻击的样子。马吉欧还没来得及躲闪,雌虎就扑过来了,和他扭成一团。他累得平躺在地上,气喘吁吁。雌虎这才往后退开,卧在他身边又开始舔舐虎爪。马吉欧轻柔地拍了拍虎肩。
“爷爷?”马吉欧说。
爷爷住的村子离马吉欧家很远。他先要搭载客的摩托车到丛林边缘,那里有一排叫“星期五集市”的小商店,是各种交通工具的终点站。再往前就是山林间蜿蜒崎岖的泥巴小道,如果有辆牛车也许可以继续往山上走,但摩托车就很难再开进去了,载客的摩托车车主根本就不愿意去。去看爷爷时,马吉欧得在合欢树林和三叶草丛中跋涉,再穿过红木树林,深入只有猎人才认得路的丛林深处。接着他要在一片山地间走一个小时,那儿只有他和那些可能在某一天会成为他的猎物的野猪才熟悉。山的后面是一个小村庄,稻田和鱼塘环绕着一所伊斯兰学校。爷爷并不住在那里,而是住在一个可以使马吉欧身心放松的地方。多次从小村庄走过之后,他在路上也认识了一些当地人,但他不能在那里逗留太久,得在夜色降临、渡筏停摆之前赶到小河边。渡筏是用一排竹子做成的,系在一条穿越小河两岸的缆绳上。摆渡工站在竹筏前拽着缆绳,慢慢拉着竹筏往对岸走,水流湍急的时候还得用一根竹竿撑筏。小河不浅,水流缓慢。河里没有鳄鱼,但有能掀起巨浪的水怪,尽管谁也没见过,孩子们却都很害怕。过河只要花十分钱,渡筏一次可以运十几个人,以及他们的牛羊、一袋袋稻谷和其他农产品。下了竹筏后马吉欧还得继续往前赶路,沿着一条滑溜溜的小道爬上另一座山。在山顶上他可以看到下面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广阔的原野中央是另一个小村庄,好似沙漠中的绿洲,草木葳蕤,房屋密布,椰子树高耸入云。
马吉欧八岁时第一次自己走这条路。其后他只要有机会就去那里看爷爷,尽管他得走半天。他总是玩得十分高兴,也总会带一大串香蕉或者一篮子兰撒和榴莲回家,让玛梅和父母高兴一下。有时如果他特别想去爷爷家但又没钱搭摩托车,他就走到“星期五集市”,然后再继续赶路,虽然会累得半死,但仍觉得快乐无比。有时他也走不同的路线,因此很快就和村民以及住在丛林里的妖精交上了朋友。从此以后,只要他在,一起捕野猪的伙伴们就再也不担心迷路了。
爷爷虽已白发苍苍,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无疾而终,去世后人们才在他的床上发现他的尸体。他每天都在一块稻田和一个种植园里劳作,但后来这一整块地被马吉欧的父亲卖掉,再也不是他们的了。马吉欧真心爱他爷爷。老人会带这孩子去一条小河,他说那里是妖精们的王国。他总是说,不要调戏女妖精,但如果某个妖精爱上你了,那就把她带走,因为那是件好事。爷爷还说女妖精都非常漂亮。马吉欧总是期望有一天他能遇到一个爱上他的女妖精,但无论他去过多少次那条小河,那种艳遇的可能性总是挂在天边遥遥无期。
更令他心迷神驰的是有关爷爷的雌虎的故事。据村里的讲故事人马·姆哈说,村里的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雌虎。有些人娶了雌虎,有些人则是继承了祖先的雌虎。爷爷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头,而这一头以前又属于他父亲的父亲,一直往上追溯到他们的远祖。没人记得谁最先娶了雌虎。
在温暖的夜里,马·姆哈会坐在她家的廊台上讲故事。孩子们蜷伏在她脚边,女孩们轮流按摩她的后背。如果她在纺纱织布,女孩们就认真翻她的头发找虱子。她总是有新故事,也不必编什么故事,她说,她讲的都是真人真事。和雌虎的故事一样,许多故事都是通过一代代讲故事人的传述才流传了下来。但有些现在发生的故事只有一些特定的人才能听得懂,马·姆哈当然就是那个能听得懂故事的老奶奶。
马吉欧记得马·姆哈既没有丈夫和孩子,也没什么事可做,她只是没完没了地讲故事。她可以走进任何人的厨房,在里面吃饭,也有人会带些吃的到她的木棚里给她。人们爱她,孩子们尤其喜欢她。她讲过一个瞎眼女人的故事,那女人只吃紫莎草茎,头发里有蛇和蝎子,但没有虱子。她还讲过关于妖精公主们的故事,专门诱拐英俊小伙子去她们的王国。但如果人们不闯进她们住的地方,她们也不会有什么恶意。后来马吉欧才知道那些地方是清泉里、河塘里、山顶上和大树上。然而,最能唤起马吉欧的好奇心的是关于保护神白色雌虎的故事。
据马·姆哈说,白虎和主人住在一起保护主人平安。她说他爷爷也是那些有白虎的人之一。但爷爷从来不对孙子讲白虎的事,他说马吉欧还太小,没法驯服这样凶猛的野兽。白虎比斑豹大得多,比人们在动物园、马戏团或者学校课本里看到的老虎大得多。如果有人无法控制住他的野兽,一旦它跑出来,就会变得非常凶狠,没法制服。
“但我只是想看看它。”马吉欧说。
“以后吧!也许你会拥有它呢。”
他经常听人说他爷爷孔武有力,也听说过村里其他老一辈人的故事:他们抵抗荷兰人,让入侵者怎么都没办法把最出色的年轻人拐骗到德里国;子弹打不死他们,后来入侵的日本人的武士刀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发怒时体内的白虎就会冲出来发起进攻;他们还赶走了在丛林里游荡的“伊斯兰之家”游击队。马·姆哈说,这都是因为那些老一辈的人从小和雌虎结下了情谊,雌虎通过结姻成为家族的成员。
马吉欧从来都弄不懂这类婚姻是什么意思。他无法想象婚礼上有个男人坐在一只头戴流苏、虎颊抹粉、虎唇擦着口红的雌虎身边,婚礼主持人祈求安拉保佑某某先生和这只雌虎。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觉得一个男人和他的老虎妻子性交是非常奇怪的事,他不知道通过这种结合而生下来的孩子会长成什么样。每次他对马·姆哈说起这种关于人类和老虎的婚姻的想法时,她就会露出掉光了牙齿的牙床咯咯大笑起来。
“只有男人才和老虎结婚,”马·姆哈说,“但也不是所有老虎都是雌的。”
爷爷当然有个妻子,一个女人。所以很清楚,那头雌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爷爷的妾。爷爷从来没有和雌虎结过婚,因为他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但对于这个家来说,雌虎仍然是爷爷的另一个配偶,受到爱戴和尊重,有时甚至甚于人妻。马吉欧的奶奶先过世了,死于支气管炎。这种病使他们整夜听着她的咳嗽声而无法入睡,也使她在死前不时发烧,身体萎缩。爷爷从此鳏居孑然,或许有头雌虎陪着,他便觉得足够了。但他也没再活多久,妻子的去世所带给他的沉重的打击,很快就夺走了他的性命。
马吉欧在爷爷生前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有一天晚上老人明确地说:“那头虎白得像天鹅。”
如果雌虎出现在马吉欧面前,爷爷希望他认出它来。爷爷又说,如果雌虎愿意的话,它可以去找马吉欧的父亲成为他的妻子。这样马吉欧就得等他父亲死后才能得到雌虎。但是如果它不喜欢他父亲,就会在某一天去找马吉欧,当他的妻子。
“如果它也不喜欢我呢?”马吉欧急切地问。
“那它会去找你的儿子或你的孙子,或者如果我们家的人把它忘记了,它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现在这雌虎来找他了,在外面的世界还是一片寒冷时,静静地卧在礼拜室里他身边温暖的地垫上。和爷爷说的一样,雌虎白得像天鹅,像天上的白云,像棉花。他兴奋莫名,因为这头雌虎比他所拥有的其他一切都宝贵。他想象着它会怎样和自己一起去捕野猪,帮助他把毁坏稻田的野猪赶进兽栏;而且如果有一两头野猪攻击他而他又无力抵抗时,它就会保护他免受伤害。马吉欧从没想到雌虎会在这么一个寒冷的清晨出现,像姑娘一样把自己奉献给他,有一阵子它看上去又像只家猫。马吉欧深情地凝视那张对他来说是如此可爱的脸,这小伙子觉得自己深深陷入情网了。
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它的脖子,抱着它,感受着贴在他身上的虎皮所带来的温暖。这种感觉就像在寒冷的清晨赤裸裸地和一个姑娘在床上相拥,享受历尽整夜缱绻之后的柔情蜜意。马吉欧闭上眼睛,感受历经长期等待后的心醉神迷,他从此不再渴望,确信小时候听到的故事都是真的。然而,他突然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他的挚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它所带来的温暖消失了。马吉欧睁开眼睛,雌虎不见了。
这使他比刚看到雌虎时还吃惊。小伙子站起来寻找,礼拜室很小,他确信雌虎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根虎毛都没留下。大雨依然哗啦哗啦下着,路上上学的孩子们的抱怨声传了进来。下这样的滂沱大雨时,人们会去割香蕉叶来当随时可以扔弃的雨伞,但马吉欧没心思想这事。他心里除了那头雌虎以外什么都不想。他茫然地站在那里张嘴呼唤,却得不到回音。他不知道要怎样称呼那头雌虎。爷爷从来没有告诉他它叫什么,马·姆哈也没说。或许他们觉得他得给它起个名字。但是,如果没地方去找这家伙,给它起名字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或许他会因曾经失去他所挚爱的姑娘们而心碎无数次,但现在他遭受的痛苦远远超过所有失恋带来的痛苦的总和。他抑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不,这不是在做梦,他告诉自己。它来找他,因为它属于他。他感受到它那皮毛的温暖,他们曾在一起嬉戏。这太真实了,绝对不是一个在清晨所做的寂静的梦。他一次次寻找,感觉到它真的离开他了之后,他的心痛转为怨恨。他颤抖着紧握十指。他从未感受过如此冷酷而渴望报复的狂怒。他没法消除这种狂怒,只能强忍痛苦。雌虎使他陷入情网,让他感受到了多年来一直渴望的幸福的高潮,它不应当这样离他而去。
他在门上敲打着,用指头刮擦着,直到绿色的油漆脱落显露出赤褐色的木板,他嘴里发出令空气都为之震颤的号叫。门上深深的刮痕令他感到震惊。马吉欧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愤怒随之慢慢消退。他瞪着门上三道平行的刮痕,如果刮在某个人的背上,那会是三道极深的伤口。然后他仔细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的指甲不长,他把指甲都剪得短短的,不然在捕野猪时手持长矛很不方便。照理说他不可能把门板弄成这样,可他短短的指甲里还是塞满了油漆和木屑。马吉欧蒙了一阵,他对自己所做的这些感到敬畏又困惑不解,但他马上想明白了。它没有离开他。雌虎仍在那里,已变成他的一部分,至死也不会和他分离。他倚靠在墙上摸着肚脐,感到雌虎现在就盘踞在他的肚脐之下。它根本不是一头容易驯服的老虎。
一个结合了谋杀和欲望的超自然故事,一本迷人的颠覆传统的犯罪小说。
——《卫报》
古尼阿弯创作的世界既熟悉又令人意想不到,其中融合了魔法、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传说。
——《出版商周刊》
故事紧凑、主题明确、内容让人毛骨悚然。像所有成功的犯罪小说一样,《人虎》非常适合一口气读完。
——《纽约时报》
不容错过,非常值得一读!
——《赫芬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