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跳出常理仔细想想,圈养人类食用并不是件合理的事。这活儿条件尤为苛刻,麻烦事一堆。即使他们被养得很胖,比起我们到来之前他们饲养作食物的动物,肉还是少很多。但止步于这一类反对意见的,怕是没有明白象征意义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只把圈养人类当作是获得食物以及身体需要的一定量的蛋白质的方法,显然,开支成本是要远远高于所得结果的。与其种地来供养人类、猪和牛,然后再吃他们,不如直接吃大型农场出产的谷物和蔬菜。我看了一些数字,发现,尽管生产流程精益求精,而且我们坚持不懈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乍一看这些数字确实能唬人,但我很快就明白,养殖业属于消耗巨大却效率一般的产业。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在建立这一套系统时,想的不是利益。他们肯定是亲口尝过了人肉,吃得飘飘欲仙,他们感到,吃人肉是坐实我们统治地位最辉煌的方式。让我们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都可以提醒自己,人类的生和死掌管在我们手里,我们完全有资格当他们的继任者。我们也都知道,人类创办的大型肉业公司的生产方式也没好到哪里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肉类工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不顾后果地扩张。然而,稍微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点研究的人都知道,要天天吃肉或者让地球上所有人都吃上肉是不可能的,否则,代价就是穷尽土地和水资源,污染空气,玩火自焚。我们做出了我们的选择,这里头八成有反击或报复的意思,我们是不敢承认的。你们会说,人类没有对我们怎么样啊!错!他们当然有对我们怎么样。他们毕竟糟蹋了这个世界,按我们一路走来的经历来看,这里本来是宇宙中最舒适的星球之一。但他们自以为是,揣着那点智慧,为自己行动的规模和进步的速度沾沾自喜,愣是一步步把这个温柔乡变成了地狱。即便我们的确享用了他们的建设成果,但将来肯定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提前开始重新流浪,那也是拜他们所赐。这一切不容小觑。面对耳边时不时响起的揭露养殖场恶劣条件的声音,要反驳是很容易的。这些人没什么资格抱怨,毕竟截除牛角的是他们,弄断鸡嘴的是他们,碾碎小公鸡的是他们,剪断小猪尾巴的是他们,拆散小牛犊和牛妈妈的还是他们。他们每天早上在槽里发现病入膏肓或已经死去的动物,嘴里说的是损失的配额。今天遭罪的人类是昨日的刽子手,他们的暴行足够列出长长的清单。他们没有手持大刀杀戮,但大屠杀正是以他们的名义才进行的。对其他极端暴力义愤填膺大声抗议的人,却能接受这样的暴力被掩盖、被处心积虑地藏匿起来。
这样看来,我们重新洗牌发牌,把他们强行摁入他们千方百计要脱离的动物统治,也算是还非人类以公道。问题是,这种以牙还牙的做法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巧妙,也不利于梳理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复仇有它的诱惑力,貌似。统治也有它的迷人之处:只需两代,人类的奴隶化和养殖就已经成为我们创造的社会架构的一部分,写入了我们的权利、道德、信仰和日常重复的每个举动之中。既然这样做并不合理,那我们无疑是在里头找到了一种表达身份诉求的迷人方式。就是在这里,我们跳出了实用论,当我们进入无理由和貌似的荒诞里,文化就产生了。不管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其他动物,吃,从来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而是确认我们是谁、我们在各色生命中排名第几的有效方式。以众生为食—我们经常以名义担保会这么做—是站在高处俯瞰天下。因此,当被问起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回答说我们不只是流浪者,不只是魔鬼,我们是吃人的那一拨,不管他们曾拥有什么,我们才是新的主人和占有者。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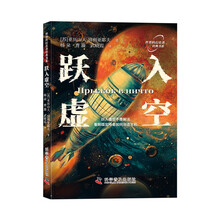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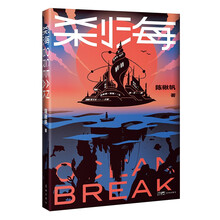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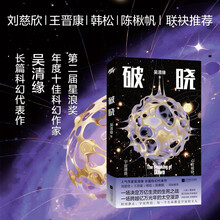

——《文学评论》
这本小说,就像洋葱,层层剥开一个我们人类已经无法治愈的新人类世界,拷问着人类盲目甚至兽性的统治的后果。
——《解放报》
樊尚.梅萨日无情地深入到敏感之处,既不怕想像未来的世界末日,也不怕给自己的小说取一个19世纪无政府主义政论小册子那样的书名。
——《转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