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基座》:
下车,在邮局门口把信塞进邮筒。过十字路口,从一位比我老、埋头读报的档主处买了一份今天的报纸。由于太熟悉,我连进哪个店铺、看哪个货架都能预先设计。比如,进华盛顿街一家廉价品专卖店,侧身在奇窄的过道挪动,从最里面的底层,找到几种园艺工具,但没有买下,懒得拿着四处走动之故。
前来饭聚的两位友人,一个打电话,一个发微信,都说要晚点到。那好,额外的时间用来寻春。春在往昔。我写过一首诗《四月,雨很明亮》,道出30年前效“细雨骑驴人剑门”的陆放翁,春日上唐人街寻诗的梦想:“虽说此处无驴(连黔之驴也无)/剑门太远太远/眉睫的雨却乖/尽滴人权充诗囊的篮子/最蠢是汽车的刮雨器/哕唆有如老奶奶的夏扇/何不停下,给车里人以氤氲,以明媚——一个假设的江南?”此刻若要踏青,9公里外的日本茶亭左侧有樱花林,青铜般的枝丫,一个个小不点儿的芽苞就是行将启封的春讯;金门公园名满天下的大温室外,迎春花云蒸霞蔚;虞美人和波斯菊在我家后院。至于烟水、熏风、桃花的红雨、屋檐下燕巢里的啁啾、远山布谷,这些春的“标配”,你要拥有,须买越洋机票。
算定友人没到,但我先走进饭店落座,为的是看自己印在报纸副刊的文字。打开报纸时想起一个比喻:照镜子。此刻就是。一个笑话说,夫妻逛画廊,太太是近视眼,指着面前一幅说:“这人像超难看!”先生趋近,小声提醒:“那是镜子,不是画。”平日我是类似的近视眼,但此刻多了冷静和客观,果然发现,用词不妥三处、叙事欠细一处、累赘多处。总而言之,不是东西。
友人终于赶到,点菜、吃菜。三个人,不约而同地不大吃饭,貌似较彻底地实践钱钟书的主张,“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其实不尽然,我们的目的是叙旧,唐人街的菜式近于千篇一律,说是大快朵颐,不如称为敷衍肚皮。聊天本来海阔天空,逐渐归结到逾来愈逼近的老境。女性友人说,她的洋老公从前要她发誓,将来他老了,不送疗养院,她那时年轻,答应了。现在才知道难办,一个体力有限且也上年纪的女子,怎么替病床上的大个子男人翻身,抱上厕所?我说,不谈为好,“最后一段路”是老天爷的辖区,说也白搭。我说罢打个哈哈,一句话没说出来,心里狠狠自嘲:你不是信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吗?且把撒手之前的种种“预”给我看?然后,和两位友人道别。街上的太阳真好,永远不老的是它,还有希尔顿酒店门口的马蹄莲,我经过时一个劲地鞠躬。
好了,该去买镰刀。回到老地方,细细挑选。镰刀和草以及树有关,也就是和“春”有关,唯一切题的工具。弯弯的,窈窕如上弦月。带细齿,教我想起儿时从草坡抓到的蚱蜢,那钢条般的腿也如镰刀一般。货架前的过道上下堆满了货物。一位比我老的老太太昂然而人,扬言买一种带5个钩的衣架。敬老的店员领着她往里闯,我为了让道而紧贴货架。接着,两位中年女性在我旁边找晾衣服的绳子。3个女士,一色纯正的乡音。油然想起家乡的春天,我的知青岁月。40多年前,屁股后面的皮带上插一把类似的镰刀,在乌青色天空悬挂一把雪亮镰刀的凌晨,走20多里崎岖山路,再下深谷割柴草。“千万留神刀口,柴草如果太硬,镰刀会打滑,刀口若向上,你的手指头就没了!”第一天,村里的打柴专业户这样教训我。此刻,我手里的镰刀,隐隐然带着雾一般的汗汽,空山鹧鸪的啼叫“行不得也哥哥——”绿色柴草好闻的微腥、山风。
拿着镰刀去付款。女收款员好奇地看我一眼,我趁机请她把镰刀包好,以免割伤人。她说好的,往地上捡起一张报纸。我无意间瞥见,包裹镰刀的竟是刊登我的“不怎么样”的散文的副刊。这可是万万想不到的“计划外”。我没作声。报纸是今天的,要么她刚才买来看;要么报社在送往报纸档销售的同时,送一些给商户做包装纸。不管怎样,都是天作之合。
该回家了,路上一切依然可做预测,比如路线,穿过联合广场时,空地上琳琅满目的画,注定无人购买,但画家自我感觉良好地晒着不老的太阳;比如缆车经过时的铃铛;比如文身男子春草般茂盛的胡子;比如地铁工地上秤杆似的起重机“称城市”的雄姿。但有一样,我怎么也解不透:巴士上,一个背着奇大的背囊的白人男子,头上的金发分成二三十绺,貌似黑人惯常打的辫子,但他的头发没“编”过,如何合成辫子的形状?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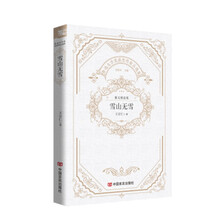




荒田行文,说他运用母语倜傥自如,并不为过。当然,这可能是对一个散文作家的至高评价了。
——邵燕祥(诗人、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