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唯一爱你的方式就是撒谎
容子走了过来,停在了门口。夕阳照进房间,轻柔的风掀起窗帘。我转身看着她,容子也望着我,眼里闪着泪光。我张开嘴,欲言又止。刚刚还在高声唱歌的她,终于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你啊……”我苦笑了一下,打破了沉重的气氛,但是接下来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也哽咽了。
我张开双臂,迎接着一头扑进我怀里的容子:“没事的没事的,有我在你身边,没事的。”
也许怀抱是我唯一能给她的安慰。但是我口口声声说着的“没事”却是那么软弱无力。什么叫“没事”呢?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还那样不停地说着破绽百出谎言。但是,那时那刻,我唯一能说出来的,也就只有这句毫无意义的谎言了。
我轻轻地拍着容子抽搐着的背脊,让她在我怀里尽情地哭着。容子的泪水湿透了我的衬衫,渗到我的皮肤上,凉凉的。身为丈夫,面对哭泣的妻子,我的心里是前所未有的无奈和无力。
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反复地问自己。我不能代替她生病,不能代替她痛苦,我能做的就只有这样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给她一点点心灵上的依靠。在病魔面前,在生死面前,再伟大的人也只能俯首称臣。我渺小的力量又如何能撼动这个摧毁性的悲哀呢?我抱着容子,同时也抱着自己不知所措的心。
“没事的……”我继续机械地说。
依旧是那最灿烂的阳光,它投射进来,用暖暖的光辉将我们这对无助的白发夫妻环绕在淡淡的金色中。从那一刻开始,容子一天天走向衰弱和死亡。她的生命就这样被突然宣判了,猝不及防……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去
挚爱的妻子即将离我而去,对我而言,这是一份难以承受的痛苦。我们一起走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不挑剔,穷日子的时候也没有怨言。容子是我的贤内助,生活中所有事情她都替我打点、为我准备,我从未担心过饮食起居。我们好不容易携手到白头,突然之间,永远的离别却摆在我们眼前。
面对生离死别,活着的人能做些什么呢?我该怎么做呢?守候在病床前,紧握着容子冰凉的手,我只能默默地祈祷,希望分别的时刻来得晚些,再晚些……
三个月过去了,容子并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离开,而是在病床上迎来了新的一年。不过容子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
容子不拒绝服用抗癌疫苗,我查到了一种疫苗的购买渠道,于是每周去一趟东京取药。独自坐在客车上,望着窗外的行人,我试着去想象每个人的生命旅程。出生、死亡,每个人都逃不出这个命运的循环。为了让容子能够多一线生的希望,我来回奔波着,这世上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一生珍爱的东西?在最珍爱的人即将要离开的时候,谁都会像我一样去极力挽留,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我每天去两次医院,从家或者工作室走过去,路上买些吃的。我每天和容子一起吃晚饭,我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着容子,亲手把饭喂到她嘴里,饭后就漫无边际地和她聊天。容子靠在窗台,我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迎着温柔的光线,我们讲起很多往事:我们去旅游时发生的种种趣事,我专程去阿拉斯加待了一周也没看到极光的糗事……
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容子的笑声还是那么爽朗。容子性格开朗,喜欢和别人交流,聊天的同时会把自己的快乐传达给周围的人。不论走到哪里,只要容子是开心的,她周围的人也一定会跟着开心起来。护士小姐有时候也会加入我们的谈话中。她问我们一起旅游时会不会经常吵架,并说她跟她丈夫新婚旅行时就开始吵了。
于是,容子解释了我们不吵架的原因:“到了观光地我们就各走各的,他喜欢逛名胜,我特别喜欢逛商店、买特产,所以我们想吵也没机会吵啊。”
说到极光的事情时,护士小姐都在笑我:“先生您居然不知道白夜现象啊!”我一脸尴尬,笑得最开心的却是躺在病床上的容子。
容子住院那段时间,女儿纪子几乎天天都在医院照顾容子,经常陪容子聊天。一天我还没走近病房就远远听到母女俩在笑。
一进门,女儿朝我坏笑着说:“爸爸,原来是这样的啊?”
“什么这样的?”我不解。
“我长这么大一直以为爸爸和妈妈是相亲认识然后结婚的呢!”
“哈哈,你猜错了吧?”容子接过话去。
“我和你爸爸可是真正地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
于是,我们又讲起在图书馆的相识,讲起那封坚决的绝交信,讲起我们奇迹般的重逢。
女儿嘲笑我:“看不出来,爸爸,你第一次见妈妈就上前搭讪啊?”
“哈哈,我那是男子汉的行为,懂得该出手时就出手!”
“哈哈哈哈……”我们都笑了起来,整个病房都被笑声点亮了。我们就这么回忆着过去的美好,谁都不愿去触碰即将到来的离别。
好景不长,进入二月,容子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到了起不了床的状态,只能安静地躺着,时不时喃喃地说几句。有时候容子会疼得睡不着觉,我就轻轻地帮她揉揉腰,希望能缓解一下她的痛苦。到后来人为的按摩已经起不到一点缓解疼痛的效果,医生开始使用吗啡镇痛。看着病床上痛苦的容子,我意识到任凭我有多么舍不得,任凭容子有多么不情愿,最后的离别还是来了。
2000年2月24日,杉浦容子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我常常觉得,和容子的分别是那样的突然。检查出身患肝癌后的第四个月,入院治疗了两个多月,容子就永远地离开了。太突然,我甚至没有准备好该如何去面对。作为比容子年长四岁的丈夫,我从未想过容子会在我之前离开。容子曾经答应过我,会照顾我直至我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因为没有她我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
“我知道啦,爸爸你走了以后我还要健健康康地活十几年呢!”容子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而如今她失约了,先走了,留下不知所措的我。
就在容子停止呼吸的那天傍晚,我和女儿纪子坐在病床边和容子还聊起全家一起去非洲旅游的经历。
“爸爸和我们都吃坏肚子了,就妈妈一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妈妈肠胃真厉害啊!”纪子说。
“是啊,某个人还说什么明明是想减肥的,但就自己没事,太不公平了。呵呵,那时还真生气了呢。”我凑近容子,笑话她。
容子躺着,听我说完跟着笑了起来:“看着你们那么难受,我是真想替你们受罪啊!”虚弱的容子声音细细碎碎的。
“等你好了,我们再一起去非洲吧!”
“好啊,但是,可能有点太远了。”容子的表情透露出一丝惆怅。
“哪有这回事,坐着飞机,一会儿就到了。”我抢着说。
容子转过脸看着我,说:“孩子爸爸,什么时候我能去了,我想和爸爸一起,就我们两个人,像以前一样,一起去多摩动物园那样。”
“动物园啊,好啊,你知道我喜欢动物。”我笑起来。
“嗯,我们准备好便当……”
“对对,准备好便当,再带上小酒,看着一路的樱花……”我不停地点头,脑海中回放起我们曾经一起出游的情景。
“爸爸,你该回家了。”一旁的女儿提醒我。
我看时间不早了,于是准备起身回去:“妈妈,我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爸爸,你今晚能在这里陪着我吗?”容子一脸焦急。
我有点吃惊,平时都是纪子在这里陪着她,今天是容子第一次要我留下来:“嗯,没问题,只要妈妈你希望我留下,我就留下陪你。”
“可是,妈妈,爸爸每天都来也很累的,今天就让他回家睡吧,有我陪着你。”女儿担心我。
“就今天一晚上,好吧?倒是纪子你,好几天都没好好休息了,你今天就回去睡吧。”容子坚持着要我留下陪她。
“可是,爸爸在这里能睡着吗?”女儿左右为难。
“没关系,没关系,今晚我在这里,你放心回家吧!”于是女儿回去了,我留下来陪着容子。
夜晚的病房显得更加安静,我关上大灯,只留下床头的读书灯。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夜空中没有月亮,路上也没有什么车,信号灯由红色变成了绿色,一盏一盏车灯开始移动。我拉上窗帘,转身回来,见容子闭着眼睛,我以为她睡着了,于是伸手去关读书灯。
“爸爸。”容子睁开眼睛轻声叫我。
“嗯,我在这儿呢。”我坐到椅子上,伏在床边,握起她的手。
“爸爸,对不起……我竟然对爸爸提出了这样无理的要求……”
容子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本来我应该照顾你的……对不起……”
我摇着头:“不,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多亏了你,我才能走到今天,要是当初没有遇见你……”我轻轻地说着,哽咽着。
再低头看容子时,她已经安静地合眼了。“容子,容子。”我轻轻地叫了她两声,容子却没有再睁开眼睛,就这样她永远地离开了我……
容子走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每次意识到她已经不在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家里每个角落都有她的身影。她在我面前打扫卫生,在我耳边说着话,一切都还那么清晰,仿佛就是上一秒的事情。可下一秒她却不在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容子走了七年了,可我依然不能适应没有她的日子。写关于她的故事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叫她:“喂,容子,你还记得我们去那个地方旅游时你为了买便当没赶上火车吗?喂,喂……”
抬头一看空荡荡的房子,客厅、厨房……到处都是空的,只有我的回音。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又不得不再提醒自己:“啊,原来你已经不在了……”
我低头继续写作,过一会儿又会不自觉地叫:“喂,容子啊……帮我加点茶好吗……”
容子最后的那段日子,每天都要与病魔抗争,每天都要忍着疼痛接受治疗。因此,那些日子就像一张张排列着的灰白卡片,但最后留下的画面却是一张耀眼的彩色明信片。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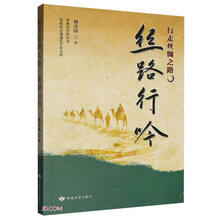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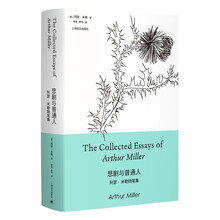




——《朝日新闻》
一个情感细腻的男人真挚地表达了爱妻之情。
——《每日新闻》
爱情是生活点滴中流露的情绪和痕迹。
——《读卖新闻》
我们从来无法得知人们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但在一起,便是此生做过美好的决定。
——田村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