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点火儿
一天下午,在休息时间里,新来的男孩弗兰克·戈尔德下了床,捻手捻脚地坐到轮椅里,滑上了走廊。周围静悄悄的,空无一人。这是10月初,天已经热了许多。弗兰克此时已熟悉了医院生活,知道护士们正在楼上吹风扇。护士长宾尼办公室的门关着,说明她也安稳地待在她的长沙发上午休。
他的首要目标照例是看一眼艾尔莎。透过半开的门上的铰链间的缝隙,他往女病房里窥探。艾尔莎的床在门后。他喜欢看她熟睡的脸。即使她的头转了过去,埋进了枕头,只有粗大的金咖啡色的辫子也无所谓,这仍旧给了他些许希望。但是,在这个下午,她的床空了。
他转动轮椅,经过悄无声息的厨房。厨房的长椅已经被擦拭干净,空荡荡的。就连苍蝇都在睡觉。整个地方都好像中了魔咒,只有他逃脱了……
他一直在等着这一刻。他口袋里有一根香烟和一小捆火柴。那是他母亲上次来探望时,他偷偷拿的。她当时不辞而别,去和护士长宾尼说话,把手提袋落在了他的床上。后来,他想象,薄暮时分,她站在车站的站台上,找着她的火柴,很想吞云吐雾,却惊讶地找不到点火的工具了。探望总是让艾达心烦意乱,所以她并非每周都来。
但是,偷窃的行为仿佛是在抗议什么,似乎他正在回到过去卑劣的自我里。他突然感到自在,仿佛又能主宰自己了。卑劣是一种隐私,但在这里生活,首先丧失的就是隐私。而自己的抗拒,抗拒的是这个地方的孩子气,它的小洗手间,它的午休和规章,它的半医院、半托儿所性质,以及他被送到这里时感到的被贬低的感觉。
“你能来我们太高兴了,”当救护车把他拉来时,护士长宾尼坚定地说道,“小一点儿的孩子正好喜欢把大一点的孩子当榜样呢。”
弗兰克端详着她容光焕发的脸,除了开心什么也看不出来,一切早就被决定了。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海盗,突然间登上了一个满是伤残动物的岛。大浪把它们席卷过来,倾倒在这里。它们和他一起搁浅了,盼着回家。
他此时滑下了廊道,经过了新治疗楼,出来后转向晾衣绳,躲在一个铁丝棚架后面。要想不被发现,只能躲在这里。洗过的衣物在午餐时就干透了,已经被收进去了。公路对面的防护网厂的隆隆声和震动声无休无止,相隔这么远依旧声音巨大。防护网厂如同被关进笼子的大型动物,而他则像是误入了对方的领地。眼前白花花的强光让他感到喜悦。自从脊髓灰质炎引起的发烧消退后,他面前的光似乎都不太亮了,反而显得比较苍老和忧愁。
独处的时候太少了,必须用双手把这样的时间牢牢攥住。他把香烟放进嘴里,划着软脆的火柴,一根接一根。汗流进了他的眼里,他的手微微发颤。他想诅咒艾达,没有理由。
一个男人的影子挡住了强光。一双红色的大手护着一缕火焰。“想点火儿?”诺姆·怀特豪斯吼道。烟点燃了,弗兰克赶紧吸了一口,摇头晃脑的,喜悦之情仿佛要溢出胸腔。他现在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喜爱诺姆了。诺姆是个园丁,正默默地缓步走开。他的步态好像在说,一个男人有权安静地吸烟。
接下来,弗兰克把香烟摁在晾衣绳的杆子上弄灭,随后把烟蒂扔过了栅栏。他觉得自己可能病了,头晕眼花。他转回黑暗的走廊,回到房间,一头扎在床上。他的身体再也不是一个正常男孩的身体了。
他也不再是个小孩子,不再像他周围的小孩子那样满身香皂味儿、睡得很死。然而,过了一会儿,随着他的心跳趋缓,他的脸上露出笑颜。他仍能听到诺姆隆隆的声音。
“点火儿?”
他也可能原本想说,“不要命了?”
但是,艾尔莎在哪儿呢?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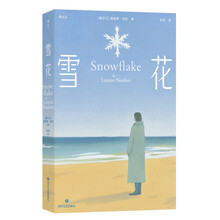
——《纽约时报》
“伦敦的文章犹如一首衔接完美的诗歌,混合着伤感和幽默。”
——《华盛顿邮报》
“《孤岛的诗歌》有着经典名著特有的宁静感,它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经典。”
——《悉尼图书评论》网站
“史诗般地展现了生活和环境的变革: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爱与认同之间、在各种各样无能为力的事情和活动之间,人们生活的真实境况。”
——澳大利亚《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