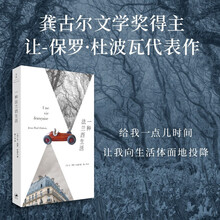冥冥之中的确有一条法则,要求一切的爱,尤其是对女性的爱,要懂得怜香惜玉。我不乐意看到她在人前那种有说有笑的活泼劲,不乐意她尽力去讨人喜欢,然而一旦她显得朴素、文静、楚楚可怜,甚至泪水盈眶时——她哭泣的时候,她的嘴唇会像小孩那样撅起来——我对她的爱立时达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的确,在社交场合我多半是不合群的,是个挑剔的旁观者。我甚至暗自高兴,这种不合群的挑剔的心态使我能洞幽烛微地观察到人们的种种缺陷。然而我又多么向往成日成夜同她亲热,由于无此可能,我深感痛苦!
我常常念诗给她听。
“你听,多么扣人心弦!”我大声说。“把我的心灵带往歌声清越的远方吧,在那儿忧伤就像小树丛上的月光!
但她的心弦未为所动。
她舒适地躺在沙发床上,双手托腮,斜睨着我,无动于衷地轻声说:“是呀,挺好的,不过为什么要像‘小树丛上的月光’呢?是费特的诗吧?他太喜欢写景。”
什么,写景!我恼火了。我开始论证与人无关的景是不存在的,即使一丝微风也是我们自身生命运动的结果。她笑了:
“亲爱的,只有蜘蛛才这样生活!”
我朗诵道:
多么忧伤呀!清晨纷飞的雪尘
又使林荫小径的尽头失去踪影,
但见一条条银色的长蛇,
钻过一个个雪堆逶迤行进……
她问:
“什么蛇?”
于是又得解释那是风搅雪。
我重又吟咏,激动得脸色都发白了:
寒夜睁开蒙胧的眼睛
朝我的车篷下探寻……
山林后边云雾瑷逮,
昏暗的月光好似幽灵……
“亲爱的,”她说,“我可从来没见到过这种景致!”
我接着念下去,可心里已在暗暗地责备她。
灼热的阳光穿过乌云直射而下,
你坐在长椅前画着耀眼的黄沙……
她听了颇为赞许,大概因为她想象这是她坐在花园里拿一把漂亮的伞在沙土上涂鸦。
“的确很美,”她说,“不过够了,别再念了,还是来跟我亲热亲热吧……你呀,对我总是看不入眼!”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