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 期 五
冷却塔,污水处理厂。芬斯托克,查尔伯利,从属怀奇伍德的阿斯科特。列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穿越田野。两条烟斗灰色铁轨排列在曲折的河流两岸。闪烁的阳光照耀着已铸成的金属。即使现在,它的周围还升腾着蒸汽。霍格华兹和艾德索普。夜班邮车穿越边境。夏延族① 人冲下山脊。货车车厢传出三角洲蓝调。在某处,那些秘密的接点有可能转向,辗转送你到由穿制服的搬运工、姑婆以及湖滨基石组成的世界。
安吉拉靠着冰冷的窗户,着迷地看着一闪而过的电线。它们一会儿下垂,一会儿被下一根电线杆托起,周而复始。塑料大棚犹如银色的床垫,砖墙上布满无法辨认的涂鸦。六个星期前,她埋葬了自己的母亲。一位大胡子男人身穿肘部发亮的套装,用诺森伯兰管吹奏着《丹尼少年》② 。一切都失去了常态:那个教区牧师手上的绷带;那位在墓碑间追赶被风刮走帽子的女士;那只不属于任何人的狗。她认为,妈妈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每周一次的来访主要是为了安吉拉自己的切身利益。煮熟的羊肉、古典调频电台,还有肉色塑料洗脸台。母亲的死应该是一次解脱。第一锹土落在棺材上,她的内心沸腾起来,她意识到妈妈已经成为……什么?一块基石?一块挡浪板?
* * *
葬礼之后那个星期,多米尼克站在水槽前刷洗那个绿色花瓶。最后一场反常的雪依然堆在小屋旁,旋转式晾衣绳在风中翻转。安吉拉握着电话走进来,仿佛那是她在门厅桌子上找到的一个神秘物品。“是理查德。”
多米尼克把花瓶倒放在架子上,“他想干什么?”
“他提议带我们去度假。”
他用茶巾擦干手。“你说的是你弟弟,还是哪个完全不同的理查德?”
“我们的确在谈我弟弟。”
他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过去十五年里,安吉拉和理查德在一起待的时间不超过一个下午。他们在葬礼上相见,似乎最多也就是敷衍。“那个异乎寻常的地方在哪里?”
“他在威尔士边界租了一栋房子。在瓦伊河畔的海伊附近。”
“赫里福德郡的细沙滩。”他折起茶巾,挂在暖气片上。
“我同意了。”
“好吧,感谢你跟我商量。”
安吉拉顿住,盯着他的眼睛。“理查德知道我们没钱自己度假。其实,我并不比你更想去度假,可是,我没有多少选择。”
他举起双手。“说重点。”他们这样争论的次数太多了。“那就赫里福德吧。”
《英国地形测量局161号,黑山/群山之灵》。多米尼克翻开粉色的封面,打开这本纸风琴似的厚重地图册。他从小就喜欢地图,而这一本是个庞然大物。X标示地点。燃烧的火柴把纸边熏成了棕色,形成圆齿,像破碎镜子似的三角形用来展示各种信息。
他斜视安吉拉,很难联想到坐在联盟酒吧远侧的那个身穿蓝色夏季裙装的女孩。现在,她让他厌烦了。瞧瞧她的身材和松垂的肌肉,还有腿肚子上暴起的青筋,差不多是个老奶奶了。他幻想过她突然意外死亡,让他重新找回二十年前失去的自由。五分钟之后,他又产生了同样的幻想,他回想起自己多么不充分地利用了第一轮自由。他听到电车轮子的吱吱声,看见一袋袋的液体。所有那些另类生活。你永远难以真正地主导它们。
他注视着窗外,看到毗连运河上的一艘小船,把舵的某个大胡子笨蛋、烟斗、茶缸。“啊嘿,伙计。”愚蠢的度假方式,每次起身都会碰到头。要和理查德在一艘小船上度过一周。
想想那情景。他们处在无名之地的中央,谢天谢地。如果一切太过分,他可以走进群山,朝天呐喊。说实话,他担心的是安吉拉,担心他们兄妹之间所有那些固有的摩擦。一旦爆发,就无法挽回。
理查德的头发,是的。现在,他想到了他的头发,那是魔鬼的栖息之处。那繁茂的黑头顶恰似雄海象的獠牙,在向虎视眈眈的贝塔雄海象发出警告。亦像一个完全独立的生物,某个外星生命形式,把吸盘插入他的头颅,把他当成一个媒介。
孩子们坐在对面。亚力克斯,十七岁,在看安迪·麦克纳勃的作品《主力军》。黛西,十六岁,在看一本名为《每日祷告的艺术》的书。班吉,八岁,他掉过头来,把脚放在头靠上,脑袋搭在座位边上,闭着眼睛。安吉拉用脚尖碰碰他的肩,“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骑在马背上,砍纳粹僵尸的头。”
他们看上去好像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亚力克斯身强体壮,肩膀和二头肌突出。他每隔一周都要走进浩渺的蓝色大自然,玩独木舟,骑山地自行车;班吉是那种男孩液体,能流入任何碰巧遇到的空间;黛西……安吉拉很想知道,过去一年,她的女儿是否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情,某种有可能说明她那种傲慢的谦逊,那种使她自己朴素的如此张扬的事情。
他们冲进隧道,窗户发出砰砰、哗啦的响声。她看见一位超重的中年妇女在黑暗中漂浮了几秒钟,然后消失在一片阳光和白杨树中。她回过神来,裙子紧箍腰部,后背冒出汗珠。那种列车的气味,强烈的灰尘,发热的刹车,厕所散发的微弱臭气。
“卡特用脚踩着那个男人的肩,把他翻了过来。这不可能是意外发生的事。他杀了邦妮·奥尼尔。十年前,他们一起在凯恩戈姆斯受训。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的上尉在阿富汗中部干什么?手持带黑标的俄国步枪,试图暗杀国际建筑公司的亿万富翁首脑吗?”
车厢深处。检票员蹲在那里,身边是一位头发灰白,眼镜上挂着红线的虚弱妇女。“这么说,你没买票就上车了,没钱买票?”他是个光头,结实的前臂上有云状的蓝色文身。
安吉拉想替她买票,想把她从这个恃强凌弱的男人手里救下来。
那位妇女试图用布满斑点的小手从空中抓取某种无形的东西。“我不能……”
“有人在赫里福德接你吗?”他的声音里透出一丝体贴,刚开始她没有听出来。他轻轻碰碰那位妇女的胳膊,想引起她的注意。“是儿子,还是女儿?”
女人挥挥手,“我不能很……”
安吉拉感到眼角一阵刺痛,转过脸去。
六个月前,理查德再婚,同时获得一名继女。安吉拉没有去参加婚礼。爱丁堡路途遥远,孩子们还在上学,而且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兄妹的感觉。他们只不过是两个人,每隔几个星期打个电话,简单聊几句,或者讨论一下母亲治病计划的两个人。葬礼上,她第一次见到路易莎和梅丽莎。她们的皮肤没有瑕疵,再配上黑皮靴,好像是以昂贵的价格从某个独特产品店买来的。女孩盯着安吉拉,在和她目光相对的时候,也没有回避。她一头剪短的栗色头发,身穿对葬礼而言还不算太短的黑色牛仔裙。十六岁,那么光彩夺目,又如此蔑视一切。“梅丽莎在学校导演了一部剧,《仲夏夜之梦》。”
路易莎有点像足球运动员的妻子。安吉拉无法想象她走进剧院或读一本严肃书籍的样子,也无法想象她和理查德单独相处时,会谈些什么。但是,他对其他人的判断总是有点摇摆不定。他和那位“姜巫婆”结婚十年。上次来看他们时,他给孩子们买了礼物。他花了很大的功夫,方向却搞错了。送给班吉的是足球年刊,送给黛西的是手镯。她想知道,他是否正在犯同样的错误,是否她只不过不是詹尼弗,而他却是社会阶梯上的另一梯级。
“我要上厕所,”班吉站起来,“我的膀胱彻底装满了”。
“别迷路。”她碰碰他的袖子。
“你不可能在火车上迷路。”
“恶心的变态人有可能会掐死你,”亚历克斯说,“再把你的尸体扔到窗外。”
“我会用拳头打他的胯部。”
“裤裆。”亚历克斯说。
“Critch,crotch,cratch……”班吉一边唱,一边沿着车厢走去。
“我们终于发现,我们不再需要沉默。我们不再需要孤独。我们甚至不再需要语言。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一切行动变得圣洁。我们可以为家人做一顿饭,而它成为祝福。我们可以在公园里散步,而它成为祝愿。”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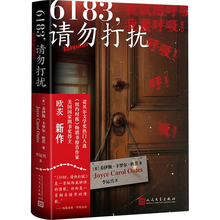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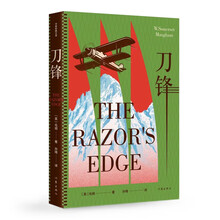



——《华盛顿邮报》
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一面可怕的镜子,四分五裂地从不同方向映照出其他人的样子。
——《哥伦比亚快报》
高质量的写作方式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正在度假的庞大家庭,甚至比其中的成员更了解他们每一个人。
——英国《独立报》
家庭应当是一个充满凝聚力的整体,而非由相互冲撞的个体为了各自的需求、失望或者好胜心而勉强组织起来的团体。
——《西雅图时报》
哈登深入挖掘了每个人都无法抛诸脑后的挫败、忧虑以及虚弱。
——《娱乐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