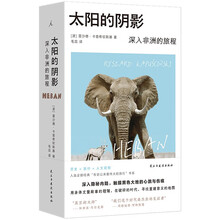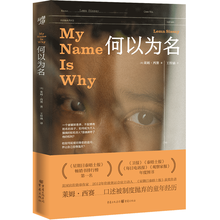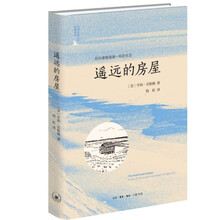海轮就要靠岸了!
我真羡慕船上那些正准备接受亲人、朋友热烈欢迎的旅客们。在我的眼中,此时此刻,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数百人站在岸边登陆的跳板前引颈招手,有长期惦记自己男人的可爱的太太们,有身穿整洁童装、数月未曾见到自己爸爸的孩子们,有一身夏季打扮、苦恋着自己男朋友的小情人们……彩色的小手绢挥舞着,高兴的泪花滚落着……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迎接他人,而不是迎接我。在整个航程中,我与这个旅行团队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可现在竟显得如此孤单,几近被人遗忘。没有人再向我招手,更没有人为我落下激动的泪花。
在这里,我没有朋友、没有情人,更没有亲人。真的,我非常羡慕所有有亲人迎接的同船旅伴!
海轮终于停止了轰鸣,停靠在了香港码头。
执勤的船员还没有开放挂在船舷边的之字形人行舷梯,乘客还不能下船。水正忙碌着用钢缆将轮船紧紧地系在岸边,要将客轮与登陆的跳板绑在一起。我注意到,很多乘客都已经相当激动了。可不是吗,香港是整个海洋旅行航程的终点。
香港,对很多人而言,已经是第二故乡,是他们长年居住的地方。
在海轮的甲板上,行李箱、旅行袋、帽盒、木箱、纸箱以及打了捆的大型包裹堆得像金字塔一般。除了这些个人的行李之外,甲板上还站着行李的主人。母亲的手是从来不会闲着的——在我看来,不少动作都是多余的——不仅不能挪下或者说丢失带来的任何一件、哪怕是小小的一件行李,手还得紧紧地拽住、哄着穿着过节般漂亮衣服的孩子。真不容易!可对孩子们来说,混乱就像一个不期而遇的节假日。孩提时的我就有这种体会,每逢搬家,家具不再放在原来习惯的位置上,我就会显得特别兴奋——久远的儿时记忆。
我向下看,眼光越过船舷上的栏杆。此时的香港码头人声鼎沸:人们相互拥挤着、推搡着、无数只手在空中胡乱地挥舞着……完全无序的宏大场面,给人的印象深刻而又独特。依我看,没有哪一位电影导演能组织起如此恢宏壮观的群众场景,即便组织起来,也不会这般生动、自然。可以说,这就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波浪般起伏的苦力群、暴风骤雨般的喊叫声……
我看见,众多苦力们大都只穿着一条邋遢的、裤脚高高卷起的长裤,赤裸着因烈日暴晒后呈现出的古铜色的上半身。汨汨的汗水在蒸腾,肌肉发达的脊背、脖颈和胳膊显得油光发亮。
我看见一位苦力,正在用一块灰暗的、脏得难以描述的毛巾拭去额头上的汗水,他身旁的另一位苦力则从头上取下那已经皱成一团的宽边帽,夹在腋窝下后扮出一副鬼脸,给人一种严肃中不乏滑稽的幽默印象——辛劳的苦力也自有一份自己的乐趣和享受!再往后的第三位瘦小的苦力则像一位马车夫,绕着自己干瘦的胸脯使劲地甩着两只膀子,那是因为心情激动、兴奋不安,在这种高温气候中他是不会感到寒冷的。
每一次海轮停靠码头,对苦力们来说,都意味着是一次要特别留意的挣钱机会。要搬运行李了!赚钱的机会来了!有时候,他们会特别幸运,能诱使几个初来乍到、不熟谙中国码头行情的旅客上当,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毫不费力地“挣”上比平时两个星期还要多得多的钱。别看这小小的铜钱,多几个少几个对码头苦力们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岸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呈震耳欲聋之势。登岸的之字形舷梯已经开始放行,码头上众多苦力组成的人墙也挤得越来越近了,那架势,似乎要把大客轮挤到海里去似的。我已经看见几个穿戴着时髦整齐制服的印度籍警察正在尽英国人职责,用粗粗的竹警棍抡打着苦力,也已经听见苦力群中这里或那里不时传来的、哇呢哇啦听不明白的、痛苦的叫喊声。那边,几个苦力已经幸运地揽到了活儿,一个苦力正利索地将一个超大而沉重的箱子举到了赤裸的脊背上,看他那轻松敏捷的动作,好像举着的不是一件沉重的行李箱,而是一团轻飘飘的羽毛。不过,你再看他那张紧绷着的脸、看那颤抖的肌腱和几乎要绷断的青筋,你就会知道,他实际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扛着行李的码头苦力们开始迈着稳健的步伐,一步一拍地、有节奏地哼唱着劳动号子,走在人行跳板的厚木板上前往码头货栈。一时间,整个码头上响起了苦力们唱出来的,不!是吼出来的、仅有一个节奏的劳动号子:
“嗨—唷、嗨—唷、嗨—唷、嗨—唷……”
这陌生的、不间断的、有节奏的发自甚至是儿童、妇女以及男人们喉咙的、感情充沛的劳动号子,交替地在码头上空回响着,浑厚有力,此起彼伏,敲打着人心!辛勤劳作中的香港码头苦力!突然间,一阵刺耳的、痛苦的叫唤声撞击着我的耳膜!发生什么事了?我赶紧转过了头,原来,一位身材单薄的年轻苦力被肩上扛着的沉重货箱压倒了。四个角均包着铁皮的行李箱轰地一下砸在了跳板厚厚的木板上,也砸在了年轻苦力的左腿上。很快,旁边的另外两位苦力跑了过来,搬开压在年轻苦力腿上的行李箱,扛在了自己的肩上,高兴地、幸灾乐祸地哼着劳动号子又离开了。他俩没有理由不高兴,又得到了一件行李,又能多赚上一笔钱了。至于躺在跳板上、腿上流着血的年轻苦力,他们连看都没顾得上看一眼。
受伤的年轻苦力带着痛苦的表情艰难地支撑着身子站了起来,哀诉着、呻吟着,一跛一跛地向前走着,还要不时惊慌地向后张望,唯恐警察又跟了上来。可不,脊背已经重重地吃了警察一竹棍。在这里,没有人会同情你,由于这位受伤流血的年轻苦力挡住了人行道,所以遭到了警察的殴打!
在此期间,客轮的周围已经聚集了数不清的小舢板和篷船,这是在中国南方的江河湖泊里常能见到的一种十分典型的、可供居住的小型船只。黑乎乎、臭烘烘、脏兮兮的舢板和篷船拥挤地贴着到港的大型客轮,上下起伏的舢板、喧闹叫嚷的船民,像一群嗡嗡叫唤的苍蝇正围绕着一具腐臭化脓的僵尸。
舢板上的女人和孩子们抬头望着海轮船舷边站着的旅客,有的在悲叹地乞讨,有的在兜售手中高高举起的小商品:雕刻工艺、彩绣织物、人造花卉、水果、玩具娃娃、小帽子以及很多其他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
小舢板船边,那些连路都还不怎么会走的小娃娃们在扑通扑通地跳水,他们能游能潜,纷纷在水里抢捞着船上的旅客扔下的分币。孩子们还能在舢板船的边缘完成双手倒立等惊险的杂技动作,供船上的旅客们消遣,以博取旅客们开心的笑声。有的孩子甚至能在舢板船面积不大的甲板上非常灵巧地完成连续腾翻三周的绝技。
舢板船的甲板上到处堆放着蔬菜和被煤烟熏得黑乎乎的炉灶,炉灶的周围放着许多坛坛罐罐,一只只肥大的绿头苍蝇正飞舞其间。在这种篷船上,是没有丝毫卫生可言的,孩子们也一个个满身污秽,身上布满了脏兮兮的痂皮。船上那些做母亲的女人穿着长长的、宽大通风的裤子站在甲板的后面,一来一回不停地摇着船尾的舵桨。女人们的声音清亮且刺耳:一位母亲在兜售她“美貌如画”的女儿,客轮上的旅客可以“借”她的女儿享用,一天只收三个银圆。另一位母亲介绍说,她的小篷船可以载着客人在港口周围的水域兜风散心。还有年轻的姑娘和小姐们在做自我推销,她们背台词似的、哼唱般地叙说着自己的风流故事: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怎样成为一个小寡妇的,她现在还那么年轻、那么迷人……她们敞露着、渲染着自己女性的魅力,讲述自己曾接待过多少国家与民族的男人,与多少水手、绅士、记者……共度过良宵,所有的男人们都从她们身上得到了幸福和快乐。有的女人还手持着推荐自己的各种纸片,在空中不停地摇晃。这些纸片都是她们曾经接待过的、深感满意的客人写下后交给她们的,相当于一份鉴定和证明……
这就是香港的码头,海水肮脏得可怕,到处漂浮着污秽、龌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