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混沌出世,既与众相同又与众不同。在娘肚子里,我就与众相同但又与众不同,因为是我嘛。尽管学有所获,尽管时光如桥下之水,我内心深处许多情感依旧源于那个
时代。我早在进襁褓以前就跟自己过不去,后来穿燕尾服,穿茜红色裤子,穿律师长袍,依然跟自己过不去。我既像天使又像魔鬼,竭尽所能充当傻蛋,不畏疾风,不怕酷暑
严寒,尤能抗寒。从娘肚子起,我便体验希望与失望,体验徒劳的抗争,体验一般的失败和独一的失败。所谓独一,因为是我嘛。
我早就竖耳贴门偷听,这是我主要的恶习,也是我原始的优点。由于娘胎中不见形象,我便在温暖中谛听、剽窃思想和声音。多亏昏暗,我其他的官能大大地发展了。
我的母亲,不愧为我的母亲。她活像贞德和圣母玛利亚,我活脱脱就像查理七世和圣约瑟,就像双子星和金牛星座下凡,长两个脑袋,即一个脑袋不算数再长一个,就像中国的猴王,翻云覆雨,翻山越岭,翻江倒海,而不顾砸碎坛坛罐罐。这是一部很古老的历史,维系着我的肚脐。这部历史对许多人而言,将是百年战争,将是追溯时间的机器,将是古董陈列架,总之,将是跳蚤市场。
我斟字酌句,却言之无物,有如串串空心珍珠,到头来我写下的句子,各人怎么理解听其自便。反正总有人自以为若有所悟的,其实毫无悟道之言,就像看戏,有人傻笑,其实没啥可乐的。不管怎样,人各有所悟呗。只需扔出几根骨头。由他人龇牙啃噬,由他人识别是猪肉还是羊肉,是公有理还是婆有理。我嘛,很久以来,长篇大论,信手走笔,搜索枯肠,蹒跚而行。我口袋揣着沙丁鱼罐头,若无其事,蹚着泥水高歌独唱。
本世纪过了三十年,比耶稣基督的寿数稍短些。小不点儿出生了,家人不置可否,因为原先期待一个女孩儿,并准备照此孕育。孕前,我就不是个东西,孕中受浪漫曲摇晃而阴差阳错,呱呱落地已有面临死亡的悲剧感。幼儿期我很虚弱,很不知趣,受到女佣过分虚情的、一板三眼的照料;战前尽管学会“狐步舞”,仍少不了眼夹泪珠去意大利旅游,横渡大西洋,穿着饰有银色绒球的舞裙。
每到黄昏,家人便把我弃置于黑暗直至天明,把我裹进被单活像裹入尸布,我陷入极度的孤独,睡在摇篮里后来睡在小床上,像死人躺在棺材里。就这样我在战前已经死过几千次了,但也锻炼了我的性格,也许不总像家人期望的那样吧。至于温馨的厩栏,明亮的清水,干洁的饲料,那是无可挑剔的。
其实我从未离开过母亲的肚腹,如今依旧,她去世那么多年了,我仍囿于暗室,规避目光,但在我头顶上,美丽的新生云彩随风匆匆而过,这些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云彩明天、长久、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在自己的树上衰老。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的生命之树屹立在村庄上空,由于天天向上,我发现了岸界。水岸真美哟,在所有的山后都有水岸,我所认识的小水岸藏在小丘后面,但最遥远的水岸最叫我心荡神驰。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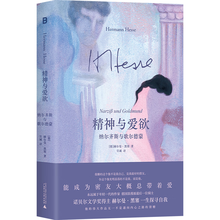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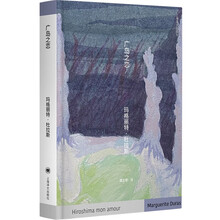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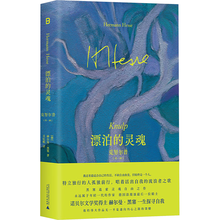





语言格调与语言色彩是塞利纳式的,辛辣的、粗野的、反讽的、夸张的语言随处可见。
真正使读者耳目一新、引人思索的还是作品中的这个“我”,他骇世惊俗,使人震撼。这是一个“既像天使又像魔鬼”一样的人,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有蔑视芸芸众生的狂傲,并以世人特别是手下败将的失败为乐。他在现代生活中是一个善攻能守的角色,全身都是“盔甲”,能做到滴水不漏。
——著名法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柳鸣九
本小说1997年在圆桌出版社出版后,法国各大报刊反应良好,大力推荐。俄罗斯立即翻译出版,文学评论界一片赞扬声。也许咱们中国读者还不太习惯这类小说,但作为了解当代法国小说动态不妨一读。
——著名旅法翻译家沈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