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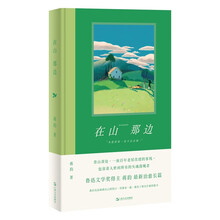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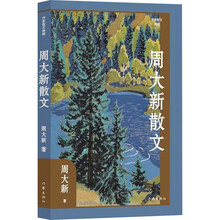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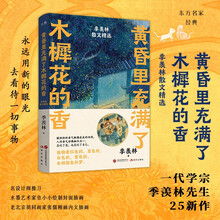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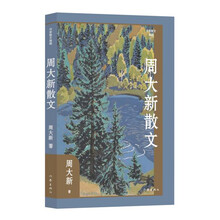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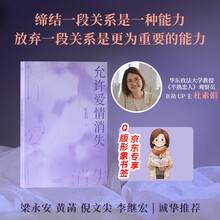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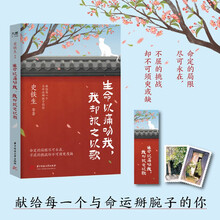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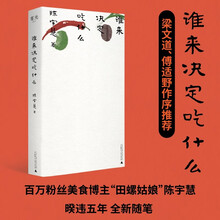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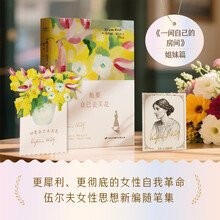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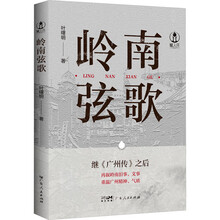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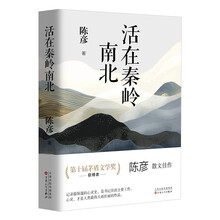
· 20世纪伟大、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汉娜·阿伦特与同时代杰出的作家之一玛丽·麦卡锡的书信集,既是两位知识分子友谊和人生、创作历程的记载,也是艺术和政治批评的典范,更是20世纪文化和思想史的见证。
· 阿伦特与麦卡锡的书信文字严谨、敏锐,字里行间却又不乏友人间的真诚和亲密,以一种私人的方式向读者呈现了两位伟大女性的政治、道德、文学观和思想脉络,更为我们生动展现了她们心灵的一隅。
· 信件中谈及的事件和人物多广为中国读者所知,包括越南战争、希特勒的审判、尼克松、水门事件等,也涉及乔治·奥威尔、奥登、海德格尔、埃德蒙·威尔森(《到芬兰车站》作者)、罗伯特·奥本海默等中国读者熟悉的人物,这些为我们了解两位作者所处的时代提供了ji佳视角。
· 本书序言作者卡罗尔·布莱曼曾为麦卡锡做传,该书获得美国国家评论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因此其序言紧扣二人的不同身份和境遇,又道出二人共同的思想渊源,是帮助读者进入这本书信集的zui佳导读。
· 本书中文版首次引进。译者章艳曾译有《娱乐至死》等广受好评的作品,译笔优美、准确,译文可读性极强。
书信中的浪漫传奇
“除非通过讲故事,否则我们无法说清生活是什么样子,无法描述造化如何弄人。”
——汉娜·阿伦特,1971年5月31日
1944年,她们在纽约曼哈顿的莫雷山酒吧(Murray Hill Bar)第一次见面。当时,玛丽·麦卡锡还处于和埃德蒙·威尔森(Edmund Wilson)的婚姻之中,陪同她的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其弟马丁·格林伯格(Martin Greenberg)是汉娜·阿伦特在修肯出版社的同事。阿伦特的评论和散文最初只发表在《犹太杂志》(Menorah Journal)和《当代犹太人档案》(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上,后来也开始出现在《评论》(Commentary)、《党派评论》(Partisa Review)和《国家》(The Nation)上,这使她的名声不再局限于她所属的德国犹太移民圈,而是被更多纽约知识分子所了解。那时,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但也已经来美国三年。她传递着一种权威——“代表某种更加古老更加深刻的东西,那就是她所理解的欧洲文化”,她的同时代人威廉·巴莱特(William Barrett)后来这样回忆——这着实让她的美国新朋友着迷。
1944年的玛丽·麦卡锡被阿伦特怀疑主义者的机智所震撼。后者和她出生在柏林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的身上都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气质,让人感觉很轻松。比如她曾讲过一个关于逃亡者的笑话,说一只逃难的猎獾狗哀叹自己作为圣伯纳犬的前世。1985年我对麦卡锡进行采访时,她回忆说:“她充满了活力,一种让人激动的不同寻常的活力……她给我带来快乐和惊奇。”在莫雷山酒吧,阿伦特笑着说,美国还没有“定型”,这还是一个小店主和农民的国家,与其说这是个新世界,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旧世界”,这里的社会视野非常狭隘,和这个国家的开国者拥有的政治视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观察与麦卡锡1947年9月的一篇文章呼应,但视角有所不同。为了解释美国生活中的游牧性质,解释她所看到的“美国装饰、美国娱乐和美国文学中存在的丑陋性”,她在《美丽的美国》一文中写道,这种“庸俗”是不是“以看得见的形式表达了欧洲大众的贫穷,表现了漂洋过海来自欧洲的落后和贫困”?关于美国电影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她指出,“欧洲是未完成的底片,而美国已是样片”。
麦卡锡认为,欧洲拥有“稳定的上层阶级”,而在美国,这种阶级的缺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庸俗化”。这和汉娜·阿伦特眼中的欧洲不同。阿伦特经常把美国这个她的移居国称作“共和国”(Republic),她眼中的美国和麦卡锡描述的战后美国也不尽相同。阿伦特看到了其他东西。在1946年给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Carl Jaspers)的信中,她用赞许的语气提到,美国不存在“民族国家”和“真正的民族传统”。
幻想(fantasy)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对于她们俩来说,这是一种具有巨大创造潜力的幻想,不仅让她们的友谊在经历了早期的一次误解之后迅速加深,而且也促进了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很多作品都从对方的文化传统中获取了灵感。我们很容易注意到,阿伦特在《论革命》(On Revolution)和《共和国的危机》(Crises of Republic)里对宪法与人权法案中所蕴含的政治原则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而麦卡锡写的是《我眼中的威尼斯》(Venia Observed)、《佛罗伦萨的石头》(The Stones of Florence)和《美国鸟》(Birds of American),《美国鸟》中处处体现着康德的道德哲学。即使是《群体》(The Group)这样一本书中全部角色都出自瓦萨学院1933届美国女孩的书,也还是在小说的结尾处把视线投向了那个远行去了欧洲的女孩“雷姬”(Lackey),她在战争爆发前夜回来了,带着一个像男人一样的埃斯蒂安纳男爵夫人,后者是个德国人。
晚年的玛丽·麦卡锡把她与汉娜·阿伦特以及意大利评论家尼克拉·乔洛蒙提(Nicola Chiaromonte)的友谊看作是一种皈依的体验,后者也是她在1944年认识的。“也许那就是欧洲!你知道,直到刚才这一分钟我才意识到这一点。”1980年秋天,她向我追忆了那个让她难忘的夏天,乔洛蒙提深深地影响了她。那是1945年的夏天,在马萨诸塞州特鲁罗的海滩上,当时她和埃德蒙·威尔森已经分手。她和乔洛蒙提谈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从埃德蒙和他的世界……还有《党派评论》那些家伙的世界走出来的感觉,”她感叹道,“实在太美妙了!”
麦卡锡之前曾为《党派评论》写过戏剧评论,还写过一本叫《她所结识的人》(The Company She Keeps)的半自传体小说。1945年,她为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的《政治》杂志(politics)翻译了西蒙娜·韦伊的散文《〈伊利亚特〉,或力量的诗歌》(“L’Iliade ou le poème de la force”),她还在巴德学院研究俄国小说,这是她的第一份学术性工作。当时很多东西都处在变化之中,特别是广岛原子弹的爆炸结束了惯常的政治,也终止了她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短暂兴趣。“我们非常活跃,”她回忆着特鲁罗的那群人,包括詹姆斯·艾吉、尼科洛·图奇(Niccolo Tucci)和乔洛蒙提的妻子玛丽亚姆。但是她所说的“绝对的觉醒”其实也就是“思考这些作家[韦伊和俄国作家]说了什么!”
就在六年前,埃德蒙·威尔森写了《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这是研究欧洲革命传统的重要作品,麦卡锡认为,“相比之下,那只能代表空洞的文学观”,他只会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两个作家”,认为“托尔斯泰当然是个更好的文体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语写得很糟糕,诸如此类……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应该把作家的生活和他们的作品联系起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信仰什么”。对于麦卡锡来说,这种联系至关重要。她童年生活中失去的东西让她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害怕文学赋予那些“急急爬过沉默的海底”的纯属个人的“蟹钳”以某种目的和意义,这是艾略特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描写。
乔洛蒙提和阿伦特是不同的,他们俩和麦卡锡认识的那些纽约知识分子也不一样,但他们俩都是欧洲人——“也是柏拉图主义者”,麦卡锡在1980年这么评价道,“更应该说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他们都非常关注个人和政治的道德性,这让麦卡锡感到非常激动,而这种激动是那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政治无法带给她的。例如,阿伦特的信条——用对世界的爱来代替对个人的过分关注,赋予了政治生活某种救赎的力量,而童年时代的麦卡锡是从宗教中获得这种力量的。
不难想象麦卡锡在汉娜·阿伦特身上发现的那些特质,正如一位崇拜阿伦特的耶稣教信徒所写的,她“具有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但是,她们的友谊也经历了考验,1945年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麦卡锡说了错话。在谈话中,大家谈起法国公民对占领巴黎的德国人的敌意,她说她为希特勒感到难过,因为他竟然会荒唐到希望得到他的受害者的爱戴。这完全是玛丽·麦卡锡的风格,她说这话是要故意冒犯那些道貌岸然的反法西斯分子,绝不是针对汉娜·阿伦特的。但阿伦特非常愤怒,她当时就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一个希特勒的受害者,一个去过集中营的人!”麦卡锡根本没有机会道歉。据麦卡锡说,三年后,她们在一个会议上讨论《政治》杂志的前途,她们同属少数派。在地铁的月台上,阿伦特转身对她说:“我们结束这荒唐的争吵吧,我们的想法如此相近。”麦卡锡为关于希特勒的话向她表示歉意,阿伦特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只在法国的一个拘留营里待过。她们的友谊之花从此常开不谢,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无人可以媲美。
玛丽·麦卡锡1912年出生在西雅图,六岁时就失去了父母,是被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监护人抚养长大的。她任性固执,除了学校里的那些知识女性,其他人她谁也不服。这种情况第一次是出现在西雅图圣心修道院的嬷嬷中,后来是在塔科马的安妮赖特神学院,再后来就是瓦萨学院。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汉诺威,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长大,她的父母亲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她是家中的独女。在某种意义上,阿伦特是麦卡锡所有老师中最出色的一位,但她的权威,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知识上,都没有阻止麦卡锡对她的思想提出质疑,尤其是当她的思想晦涩难懂,同时又和麦卡锡本人的现实感产生冲突的时候。
所以,在赞扬《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人类思想方面至少领先了10年”之后,麦卡锡在她写给阿伦特的第一封信中还是忍不住指出,“书中确实有些不规范的表达,比如用‘ignore’(忽视)来表达‘be ignorant of’(不知道、不懂)……再版时也许应该更正”。她还对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自己“更重要的异议”——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些丧失家园的人用来剥夺他人现实感的一种体制”——她触及了她们之间一个有趣的差异,这种差异让她们持续了25年的通信充满了活力,并且为她们之间的几次争论添加了一种“哲学小说”(conte philosophique)的色彩。
麦卡锡认为,阿伦特削弱了极权主义中的“偶然因素”,她这么说指的是某种可能,即“某些特征被融入了这些极权主义运动中,仅仅因为这些特征很管用”。阿伦特似乎认为“纳粹和斯大林有特殊的方法能够掌握政治行为的法则”,这是麦卡锡在1951年4月的信中写的。麦卡锡承认人们常常有这种印象,但阿伦特没能把自己的观点说明清楚,因为她自己有时候似乎也持相反的观点:“人不是理性世界的阐释者或艺术表现者,而是一个无例可循的创造者。”
麦卡锡深信,机会和选择共同塑造人生,而且机会的重要性大于选择。在她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各种精彩的创造,任何东西都可以推陈出新,比如家里的旧布、习俗和历史。这种创造不仅出现在她常常用来检验自己创造力、表现个性的回忆录和信件中,而且还出现在对历史的思考中。在《我眼中的威尼斯》中,威尼斯这座具有多元文化传统的城市正好让麦卡锡自嘲了自己多宗教背景的童年,她这样写道:“作为一座城市,威尼斯是个弃儿,像被放在篮子里的摩西一样漂浮在水面上,因此它必须学会创新,必须学会偷窃,必须急中生智。”
她和阿伦特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变化的态度——不是政治上的变化,这一点她们是一致的,在危机时期她们都能勇敢面对,虽然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解使她的态度更为悲观。她们的差别在于个人的变化,特别是在与异性交往中的变化。麦卡锡相信,在恋爱中,某种个人的改变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恋爱的唯一理由。(也许,这正是她不断恋爱的原因。在麦卡锡的中年,爱情在她自我提升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伦特更喜欢尼采所说的“保持自我”,不愿受任何思想规范和社会习俗的约束,她坚持一种更为悲观的、更具欧洲人特点的观点,但她也是浪漫的,只是方式不同。
1956年,麦卡锡和伦敦的一位评论家开始了一段注定失败的恋情。阿伦特这样写道:“你知道,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我认为你的感觉不会错。”但是她很高兴玛丽决定不再见那个男人。她为那个男人的谎言向玛丽表示了同情,她称这种撒谎的行径为“幻想型谎言癖”,是那种自吹自擂的谎言,所以不能相信(这是典型的阿伦特式的悖论,源自拉丁时代的传统,在现代演讲术中已经衰微)。她认为,“对自己的出身撒谎,假装自己是英国的贵族”是一种冒名顶替,是对英国的讽刺。这种谎言只和事实有关,所以最终会真相大白,但是“如果一个人撒的谎是关于他的‘感情’,他是绝对安全的,谁会发现呢”?阿伦特认为,“他们的谎言里有一种公然的蔑视,这种蔑视正是他们吸引人的地方”。
这里阿伦特提到了布莱希特的警告,“这里有一个你不能依靠的人”,她还提到了海德格尔,他是阿伦特1925年时的老师,他们之间有过一段恋情(1985年麦卡锡告诉我,“这是她一生中真正的一场恋爱”)。阿伦特认为,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说,才华掩盖了他们的不可靠,或者说弥补了他们的不可靠。而对于那些没有天赋的叛逆者来说,他们的价值在社会中得不到认可,所以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自我毁灭将成为一项持久而光荣的任务,这比拯救自己更加光荣,也许也更加有趣。唯一不能允许的是,他可以自娱自乐,但不能把别人拖下水”。所以,他要把玛丽吓跑,“当然,这么做很残酷,”阿伦特对她说,“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爱你的人对你不残酷,尤其是他也是用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
这些关于爱情的观点揭示了阿伦特让人意想不到的一面,这无疑是因为麦卡锡那些感情纠葛促使她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1960年,麦卡锡和华沙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詹姆斯·韦斯特(James West)开始了一段疯狂的跨洲恋情,为了这个男人,麦卡锡愿意放弃一切,阿伦特对此深表忧虑。后来,韦斯特成为了麦卡锡的第四任丈夫。
阿伦特“害怕”麦卡锡“可能受到伤害”,麦卡锡在1960年5月的一封信里让她不要担心——她和韦斯特在苏黎世共度周末后,向阿伦特描述了他们的情人之旅,并且说:“我是真的受了伤害。”麦卡锡愚蠢地告诉了韦斯特她以前的一段恋情,他表示难以置信,而且非常愤怒,结果她伤心地痛哭。他后悔了,承认自己性格里有“恶劣的东西”,麦卡锡也感觉很愧疚,她安慰自己说“恶劣”的性格可以“改正”。
“你关于[以前那次恋情]的故事听上去很滑稽”,阿伦特在回信中戏谑地说,“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得自食其果啊。”但她指的不是“受伤害的事——这只是表达感情的另一种方式”。同时,她希望麦卡锡不要自欺欺人:“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改变任何东西……这只是女孩子们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你要么愿意接受‘原来的’他,要么趁早离开。”
这种泼冷水的做法和漠不关心是不同的,这在另一个故事中也可略见一斑。《党派评论》的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1947年见过一面,他后来向阿伦特抱怨波伏娃谈论美国时“没完没了地胡说八道”。“威廉,你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她并不非常聪明,”她建议说,“你不要和她争论,你应该和她调情。”
虽然阿伦特警告说“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改变任何东西”,麦卡锡还是认为他们“都应该有所改变”,她回信说:“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毫无改变,那相爱还有什么意义?”很快,她再次结婚(这一段婚姻持续了28年)。但是阿伦特一直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急着离婚再婚,“你们为什么不能就住在一起呢?”1985年,麦卡锡回忆起阿伦特的这个问题时告诉我,“她希望我认真考虑这个建议,无论她现在哪里,她也许都在不满地摇头,因为我们没有听她的话。”
阿伦特知道麦卡锡和她的第三任丈夫鲍登·布罗德沃特(Bowden Broadwater)之间的问题,她甚至出面劝说鲍登同意离婚,在此过程中,有一次她曾表达过不满。布罗德沃特威胁说,只有等韦斯特离了婚,他才会同意离婚,麦卡锡1960年10月7日写信给阿伦特说:“我的心里充满了愤怒、失望和怀疑,难以平静。”她猜疑鲍登说服了阿伦特,让她认为他的做法是对的。“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吉姆了,他也一样。我们这样被动地受制于别人实在太荒唐了”,几个星期后她这样写道。在1960年11月11日的回信中,阿伦特只是重申了一些事实,她说布罗德沃特在这件事中“完全可怜无助”,她“作为朋友”和他谈话,非常诚恳,“没有威胁”,因为麦卡锡他们才会结识(“不是我个人的朋友……而是家庭的朋友”),也因为她似乎对他还有些影响。至于麦卡锡说她和韦斯特“受制于别人太荒唐”,阿伦特回答说:“显然,你们俩的痛苦是你们自己造成的,过去的事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这也许给你们带来了麻烦,但并不荒唐,除非你说你们的整个过去不仅是个错误,而且是个荒唐的错误。”
这些对“心里像螺旋形开瓶器一样曲里拐弯的欲望”(这是奥登的话,也是阿伦特最喜欢的一个表达)的评论贯穿着她们的通信,和其他作家发表的书信不同的是,她们的通信中不仅有高尚的思考,还有女人间轻松的闲聊—不是八卦,虽然也有八卦,而且不完全是玛丽·麦卡锡的。阿伦特在1960年的信中,描述了“小个子波德霍雷茨(Podhoretz)看上去像个犹太服务生一样疲惫”,还有艾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jin)[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告诉她的]“走路的姿势和动作就像一头傲慢的骆驼”,这些文字都令人难忘。让麦卡锡和阿伦特的信与众不同,并且赋予它们一种罕见的戏剧力量的,是她们在信中如在耳边的声音,这种直接性有时会产生一种戏剧效果。即使是关于个人私事的评论读起来也像对话—是可以传递思想的对话。
这些信中的思想(“思考这种事”,阿伦特这样称自己最喜欢的消遣)和想法或观点不同,后两者可能产生于思想但不尽然。阿伦特和麦卡锡对于20世纪思想界“习见”(idées re·ues)的很多思考都是批评性的思考,但这和我们在信中发现的思维活动也是不同的。这种思维活动可以被称为“纯粹的”思想(pure thought),如果这个定语不违背阿伦特的“思考的自我”(thinking ego)这一精神的话。在这种思维活动中——无论是关于感情问题、街头犯罪、学生叛乱或是“黑色力量运动”——阿伦特,尤其是阿伦特,会来回穿梭在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对此的思考之间,从而填补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这种思维活动的本质在于它具有能够直接关注世界的能力,不仅仅是关注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而是关注世界本身,并且剥去了思维中可能存在的迷信、情感因素以及理论的装饰。
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在她的政治文章中还是她的书信中,阿伦特确实都很像苏格拉底,他们都努力让哲学贴近现实,审视那些我们用来判断世事的看不见的标准。我曾经问过20世纪70年代担任阿伦特助教的杰罗姆·科恩(Jerome Kohn),《精神生活》(The Life of Mind)未完成的第三部的主题——“判断”是否会成为阿伦特写作中的一个拦路虎,他说,“根本不会,”他向我指出了一个这本通信集的读者也很容易发现的事实,“汉娜一生都在进行判断,判断各种事件,理解它们给其他人带来的后果,这些对她来说就是运用常识。”
这种多思(thougtfulness)——不要和“为善”(being good)混淆起来——和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是一种远离琐屑表象世界的途径。阅读阿伦特关于“知识分子无判断力的多思”的论述时,那些笨拙的德语式英语句子也许会让读者蹙眉(英语是阿伦特的第三语言,排在德语和法语之后),但是如果认真阅读,读者对如何思考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全新的理解。我们可以用阿伦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喜欢乘坐的小火车来比喻她的这种思考。她把这种火车称为“叮叮当当”,从她避暑的位于山区的台格纳坐到洛迦诺去看马戏或电影。“虽然身边都是朋友,但她却像一个孤独的乘客,一个人乘着她的思想列车”,麦卡锡在《和汉娜告别》中写到了1970年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去世后阿伦特的凄凉,这个沉静的形象让我们在阅读阿伦特的文字时感受到了一场神秘的精神旅行。
据高登·A.克雷格说,他最近乘坐从法兰克福开往汉堡的火车,听到播音员在广播里说:“欢迎乘坐汉娜·阿伦特城际快车——不管她是谁——祝您旅途愉快。”过了一会儿,那个声音又回来了:“汉娜·阿伦特是一个作家”,最后又说:“对了,我刚刚知道——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哲学家。”这只是一件有趣的轶事,但至少说明她得到了公正的认可。[在美国,我们不以诗人或哲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火车,但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在给金星绘制地图时,用一些著名女性的名字来命名那颗遥远行星上的火山口:赛珍珠、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克莱尔·布斯·卢斯(Clare Booth Luce)、丽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和苏格兰女王,阿伦特和麦卡锡和这个殊荣无缘。]
麦卡锡喜欢看她的朋友“思考”。“听汉娜演讲就像看到她的思想通过动作和手势变成可以看得见的东西。”1975年在阿伦特的葬礼上她这样告诉来悼念的人。她生动地描绘了阿伦特和思想之间富有活力的关系:“汉娜是个保守主义者,她不会把任何思考过的东西随便扔掉,她一定会让它派上用场,”她接着说,“思想对她来说是一种资源管理,把体验的荒野变成适合人居的地方——建造房屋、开辟道路、拦堤筑坝、造林防风。这些任务都落到了她的肩上,因为她具有不同寻常的智慧,是前后几代人的杰出代表,她有责任系统地思考她在这个时代中每一个特有的经历——社会混乱(anomie)、恐怖行为、高级战争、集中营、奥斯维辛、货币膨胀、革命、取消学校种族隔离、五角大楼文件泄密、太空探险、水门事件、教皇约翰、暴力和公民抗命——完成了这些工作后,再让思想回到内心世界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形成过程中。”
……
序言:书信中的浪漫传奇
编者的话
第一部分 1949年3月—1959年12月
第二部分 1960年4月—1963年4月
第三部分 1963年9月—1966年12月
第四部分 1967年2月—1970年12月
第五部分 1970年12月—1973年4月
第六部分 1973年5月—1975年12月
后记
汉娜·阿伦特著作目录
玛丽·麦卡锡著作目录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很难找到另一位比阿伦特更适合引导人们面对21世纪人类困境的20世纪思想家。
——《纽约客》(New Yorker)
玛丽·麦卡锡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女作家。
——《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
这两个有着截然不同的过去和气质的女人之间的友谊是什么样的?她们成为朋友并非因为她们“想着类似的事”,而是因为她们都以与对方、为对方“思考”为己任。
——《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
对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段友谊的耐人寻味的记录。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这些信件智慧、雄辩、有爱,勾勒出这段跨越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友情。……也是艺术批评的典范和友谊的见证。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她们漫长的通信异常精彩,反映了二人截然不同的人格和对政治、哲学、文学人物、当代事件的观点。
——《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