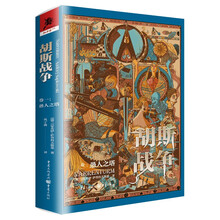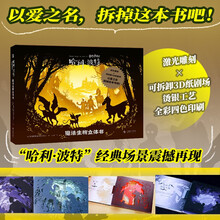《掉到精灵国度底下的女孩 影子的狂欢会》:
从前,有个女孩叫九月,她有一个秘密。话说秘密这种东西微妙得很。秘密会让你满心甜蜜,让你感觉像猫儿抓到肥滋滋的麻雀,而且吃它的时候没被抓被咬。但秘密也会卡在你身体里,慢条斯理地熬煮你的骨头,熬出苦涩的汤。于是你便受制于秘密,而不是秘密受制于你。幸好秘密还在九月掌握之中,她像带着一双昂贵的手套一样守着她的秘密,冷的时候拿出来戴上,回忆曾有的温暖。
九月的秘密是她去过精灵国度。
这种事并非史无前例,其他小孩也遇到过。有很多书都写过小孩去精灵国度的事,自古以来,小男孩、小女孩就读着这些故事,做木剑、用纸折半人马,等着轮到自己。而九月在上个春天就等到了。她对抗了邪恶的女爵,让精灵国度免于女爵的残酷统治。她交了些朋友,那些朋友不仅勇敢、聪明又有趣,而且是双足翼龙、水精和会说话的灯笼。
唯一的问题是,那些书里写的净是些神气活现的家伙,却很少写到他们回家以后该怎么循规蹈矩。九月原本是那种一心希望精灵神怪等都真有其事的女孩,现在摇身一变,成为知道这些都确实是真有其事的女孩。那样的改变不大像换了个发型,倒像整颗头都换了。
而这样的改变对她的校园生活没什么帮助。
从前九月不过是个安静的怪孩子,会在数学课时望着窗外,在公民课时把色彩缤纷的大书藏在桌子底下看。现在,其他孩子觉得她有种狂野且陌生的感觉。同年级的女孩说不出她们为何那么讨厌九月。如果叫她们坐下来,问她们为什么,她们顶多只说得出“她就是和我们不一样”这种话。
所以她们不邀请她参加生日聚会,不问她暑假的安排。她们倒是会偷她的书,向老师捏造她的坏话。
她们会理直气壮地说:“考代数的时候九月作弊。”“九月在体育课上偷看恶心的旧书。”“九月和男孩子一起去化学大楼后面。”她们在九月背后窃笑,笑声在她们挤成一团的蕾丝裙和系着缎带的鬈发周围,立起了刺人的藩篱。窃窃私语的声音表明了她们站在藩篱之内,而九月永远都被挡在外面。
九月不顾挫折,依然守着她的秘密。每当她觉得害怕、寂寞、心寒的时候,她会唤起她的秘密,像吹着余烬一样朝它呼气,直到秘密又亮起来填满她的心——她的图书馆翼龙A到L朝星期六的蓝色脸颊喷气,直到他笑出声;绿风在麦子之间跺着他的宝石绿雪鞋。他们都在等她回去,她当然会回去——很快、马上、随时就会回去了。她感觉自己很像玛格丽特阿姨。
旅行回来之后,玛格丽特阿姨似乎变得不太一样。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巴黎、丝质长裤、红色手风琴和牛头犬的事,大家都不太懂她在说什么。但他们会礼貌地倾听,最后她的声音渐弱,她望向窗外,仿佛看到的不是一亩亩麦子和玉米,而是流淌而过的塞纳河。九月觉得她现在了解她的阿姨了,并且决定下次阿姨来的时候,要对阿姨体贴一点。
每天晚上,九月都坚持等待着。她照样洗着那些粉红带黄的茶杯,照顾她一直照顾着的那只焦虑的小狗(小狗愈来愈焦虑了),听着高高的胡桃木收音机播放关于战争、关于爸爸的新闻。收音机在他们的客厅里显得高大吓人,在她眼里好像一扇恐怖的门,随时会打开,把坏消息放进屋里。每当太阳在长长的黄色平原上西落时,她都随时注意地平线上有没有闪过一点绿色,有没有斑点毛皮在草丛中闪现,有没有那种笑声、那种呼噜声。但秋天像一叠金黄的纸牌一样一天天过去了j谁也没有来。
妈妈星期天不用去飞机制造厂,所以九月爱上了星期天。她们会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火炉边看书,看小狗叼她们的鞋带。有时妈妈会滑到阿伯特先生惨兮兮的旧福特A型车下面,乒乓敲打,直到九月能扭动钥匙,听车子再次隆隆发动起来。不久之前,妈妈还大声念着精灵、士兵或拓荒者的故事给她听,但现在她们开始一起读书,各看各的小说或报纸,九月记得战争开始前妈妈和爸爸差不多就像这样。星期天是最棒的日子,星期天的阳光似乎永远不会消失,而妈妈灿烂率真的笑容让九月容光焕发。一到星期天,九月就不难过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