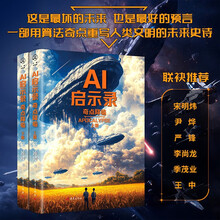第四章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天了,但除了那场谈判,好像没有别的谈论话题。”奥格瑞姆骑在猛咬的背上,拉长的面孔尽是郁闷。
“看样子,这也包括你在内。”杜隆坦说。奥格瑞姆紧皱眉头,陷入了沉默,显得有一点困窘。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寻找木柴,为此他们已经从村中跑出了好几里远。这不算是最糟糕的任务,但必须有人去做,毕竟这远不如狩猎那样令人兴奋。木柴是氏族在冬季生存所必需的,刚刚取得的木柴还要先熟化和晒干。
但奥格瑞姆是对的,加拉德肯定一直在思考那次会面。因为第二天清晨,酋长没有离开他的屋子,只有盖亚安现身了。母亲从杜隆坦身边走过的时候看到了他询问的眼神,便说道:“你的父亲因为古尔丹的话感到困扰,他要我去找德雷克塔尔。我们三个也许应该讨论一下那个绿色的陌生人描述的现象,研究它们会如何对众灵产生影响,以及我们该如何最有效地发挥我们的传统。”
其实杜隆坦只是扬了扬眉毛,但母亲却做出了如此详细的解释。杜隆坦心中立刻产生了警觉。“我也要参与讨论。”他说。盖亚安摇摇头,她镶缀着骨头和羽毛的辫子也随之左右摇摆。
“不,你还有其他事要做。”
“我以为父亲对古尔丹已经没有兴趣了,”杜隆坦说,“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们要为此进行讨论。作为儿子和继承人,我应该出席。”
盖亚安再一次挥手示意儿子离开。“只是一次谈话,仅此而已。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找你的,儿子。而且我说过,你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收集柴火。当然,无论是什么工作,哪怕是氏族中最弱小的成员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比酋长的工作低微,霜狼兽人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发言权。但这一点无法掩盖现实——氏族正面对着严重的问题,杜隆坦却被排除在外。他不喜欢这样。
杜隆坦回想起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被命令去收集柴火以维持篝火。他大声抱怨,因为他想和奥格瑞姆练剑,因而受到德雷克塔尔的责备:“砍倒大树却只是为了生活所需,这有失慎重且危险,大地之灵不喜欢这样。它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树枝来建起篝火堆,还有干燥和易于被点燃的松针。只有懒惰的小兽人才不愿为了尊崇众灵而多走几步,却只是像狼崽子一样号啕大哭。”
当然,杜隆坦是酋长的儿子,不愿意被称作懒惰的小兽人,更不愿意被说成像狼崽子那样哭泣,所以他立刻听话地去执行任务了。长大以后,他曾经问过德雷克塔尔那时对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萨满“嘿嘿”笑了两声,“肆无忌惮地砍树的确很愚蠢,”他说道,“而且砍倒过于靠近村子的树木会让外来者更容易发现我们。不过......是的,我确实觉得这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你不觉得吗?”
杜隆坦不得不同意萨满的话。不过他紧接着又问:“众灵的规则会一直符合酋长的意愿吗?”
德雷克塔尔咧开大嘴露出微笑:“它们有时候是相符的。”
现在,当杜隆坦和奥格瑞姆并骑前进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砍树......
“古尔丹说,当南方的兽人砍开树干的时候,树木的气味......不正常。”
“现在是谁开始说古尔丹了!”奥格瑞姆说。
“不,说实话......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还有那颗血苹果......他让我们看到的那个里面没有一颗种子。”
奥格瑞姆耸了耸宽大的肩膀,朝前方的杂木林一指。杜隆坦看到落在地上的许多枯枝,仿佛无数黑色的骨殖,还有堆积在它们下面的褐色干松针。“谁知道?也许那些南方的树不想再被砍伐了。至于说那颗苹果,我以前也吃到过没有种子的果子。”
“但他怎么会知道?”杜隆坦坚持问,“如果他在我们面前切开那颗苹果,却看见里面是有种子的,那他就只会在我们的嘲笑中被赶出村子。他早就知道那里面不会有一颗种子。”“也许那个苹果早就被切开过了。”奥格瑞姆跳下猛咬,打开了空口袋,准备用枯枝将它填满。猛咬开始在原地转圈子,想要舔奥格瑞姆的脸。他的主人不得不和他一起转圈子,一边笑着说:
“猛咬,停下!你还要扛柴火呢。”杜隆坦也笑了,“你们两个别只是跳舞......”这句话说了半截就梗在了他的喉咙里,“奥格瑞姆。”朋友语气的变化立刻让奥格瑞姆心生警觉。他顺着杜隆坦的目光望过去,几步以外,灰绿色的松树林中,树皮上的一个白点表明有人从那里砍掉了一段树枝。
他们俩从能走路时就一起狩猎,练习在暗中靠近用皮革制作的野兽玩具。他们之间的默契更胜过语言的交流。奥格瑞姆此时绷紧了肌肉,在沉默中等待着酋长儿子的命令。
观察,杜隆坦的父亲这样教导他。那根树枝被整齐地砍断,不是被折断或者拧断的,这意味着这人有武器。断口上还在渗出琥珀色的汁液,也就是说它刚刚被砍断不久。这棵树周围的雪也被踩乱了。
片刻间,杜隆坦也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倾听周围的声音。他能听到冷风轻微的叹息和松针的沙沙作响。当他深深吸气的时候,树林中洁净的香气便会飘进他的鼻翼。但他的确嗅到了一些东西的味道:皮毛,还有一种麝香气味,陌生,但并不会让人感到不快。杜隆坦知道这不是德莱尼的那种怪异的花朵香气,而是来自于其他兽人的气味。
在这两种熟悉的气味中,还夹杂着第三种明确无疑的刺鼻味道:鲜血的刺鼻腥气。
杜隆坦向利齿转过身,将一只手放在这头狼的鼻子上。利齿顺从地倒卧在雪地上,像他的主人一样安静。除非受到攻击或者杜隆坦召唤,否则他绝不会动一下,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猛咬和利齿是同一窝出生的,也和利齿一样训练有素地执行了奥格瑞姆的命令。两头狼用聪慧的金色眼睛看着他们的主人谨慎地前行,避开可能埋着树枝的雪堆,以免树枝的断裂声会暴露他们的形迹。
他们随身的武器只有斧头、座狼的牙齿和他们自己的身躯——这些武器足以对付普通的危险,但杜隆坦还是很希望有一把战斧或一杆长矛。
他们向那棵被砍断枝杈的树靠近。杜隆坦摸了摸断口上滴落的树脂,又向被踩了许多脚印的雪地指了一下,仿佛是在说这些闯入者是多么明目张胆。这些兽人根本不在乎是否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杜隆坦弯腰去检查脚印。数尺以外,奥格瑞姆也在做着同样的事。经过一番迅速却又详细的调查,杜隆坦竖起四根手指。
奥格瑞姆摇摇头,用两只手表示出一个不同的数字。
七个。
杜隆坦面色变得严峻起来。他和奥格瑞姆都正年轻,身体灵活,动作迅捷,肌肉强健。他相信他们能顺利地干掉两个敌人,甚至是三个或四个,哪怕他们手中只有短柄斧。但七个......
奥格瑞姆看着他,向树林深处一指。他从出生时起就热衷于战斗,现在他同样渴望着去和那些闯入者较量一番。但杜隆坦缓慢地摇摇头——不。奥格瑞姆的眉毛拧在了一起,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他的表情却无异于向杜隆坦发出了一声惊呼。
这会成就一次伟大的洛克瓦诺德——杜隆坦将在英勇奋战之后死去,并因此得到赞颂,在歌声中被铭记。但他和奥格瑞姆现在离村子实在是太近了,杜隆坦抱起手臂,仿佛怀中有一个孩子,告诉奥格瑞姆——回村报信才是最重要的。奥格瑞姆不情愿地点点头。
他们回身向座狼伙伴们走去。两头狼仍然匍匐在雪中。杜隆坦不得不压抑住立刻跳上狼背的冲动。他将一只手探进利齿咽咙处柔软的长毛中,白狼站起身尾巴慢慢摇动,和杜隆坦一起向远处走出一段路,直到那片树林和隐藏在其中的危险已经远离他们。在确信树林中的人不会听到或者跟踪他们之后,杜隆坦才跳上利齿的脊背,催促白狼,用他有力的四条腿施展出的最大速度向村庄奔去。
***
杜隆坦径直冲向酋长的屋子,没有知会一声便推开了屋门:“父亲,有陌生人......”
他的声音停在嘴唇间。
根据氏族律法,酋长的居所是村中最大的一栋房子。一面旗帜悬挂在这里的墙壁上,酋长的盔甲和武器被放置在角落里,烹饪器具和其他日常用品整齐地摆放在另一个角落中。屋子里的第三个角落通常都会用来储存作为被褥的毛皮。它们被卷起来,竖在墙边,不会影响家人在房间里的活动。
但今天的情形和往日截然不同。加拉德躺在覆盖硬土地面的一块裂蹄牛皮上。另一张皮子盖在他的身上。盖亚安一只手伸到他的脖子下面,将他的头撑起来,让霜狼酋长能够从她另一只手握住的瓢中吮吸液体。杜隆坦闯进来的时候,盖亚安和站在她身边的德雷克塔尔都猛然向他抬起头。
“把门关上!”盖亚安喝道。惊骇到无法说话的杜隆坦立刻服从了命令。他迈开长腿,两步就走到父亲身旁,跪倒下去。
“父亲,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酋长喃喃地说着,有些气恼地推开了还在冒着热气的瓢。“我累了。你也许会以为在我身边晃悠的不是德雷克塔尔,而是死亡本人,有时候我真的很怀疑他们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杜隆坦看看德雷克塔尔,又看看盖亚安,他们都面色严峻。盖亚安看上去似乎在过去三天中都没有怎么睡过觉。杜隆坦这时才发觉,他的母亲为了进行谈判仪式而戴在头发上的珠子直到现在都没有取下来。以前每一次仪式结束以后,盖亚安都会立刻脱掉仪式服装。
不过杜隆坦还是首先向盲眼萨满开了口:“德雷克塔尔?”
那位老兽人叹息一声:“这不是我所熟悉的疾病,也不是创伤。但加拉德的感觉......”
“很虚弱。”盖亚安说。她的声音在颤抖。
看样子,这才是她催促杜隆坦在这三天里离开村庄去收集木柴的原因。他不希望杜隆坦在村里,总是提问题。
“严重吗?”“不。”加拉德嘟囔着。“我们不知道,”德雷克塔尔并没有理会加拉德的话,“这才是让我担心的。”“你认为这和古尔丹所说的那些事有关系吗?”杜隆坦问,“关于这个世界正在生病的事?”疾病是否已经蔓延到了霜火岭?德雷克塔尔又叹了口气:“有可能,或者这可能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是一种我无法探知到的感染,也可能是......”“如果是感染,你就一定会知道。”杜隆坦刻板地说,“众灵说了什么?”“它们非常不安,”萨满回答道,“它们不喜欢古尔丹。”“谁又能怪它们呢?”加拉德说道。他向杜隆坦眨眨眼,想安慰儿子,但只起到了反效果。整个氏族都在因为绿色兽人恐怖的预言而惴惴不安,再让加拉德以这样的状态出现在族人面前显然是不明智的。盖亚安和德雷克塔尔是对的,应该等到他恢复到......
杜隆坦暗自骂了一声。一开始看到父亲变成这副样子,他完全被吓呆了,甚至忘记了自己为什么闯进父亲的房间。
“我们在树林中发现了入侵者的足迹,就在大约十一二里远的东南方,”杜隆坦说道,“那些足迹还带着血腥气,可以判断那些人绝不是简单地杀死了一头野兽。他们的血腥味已经在那里很久了。”
加拉德满是血丝的小眼睛里充盈着泪水。听到儿子的报告,他眯起眼,把毯子掀到一旁,一边挣扎着坐起身一边问道:“有多少人?”
但他的腿还没办法支撑住身体,盖亚安扶住了他。杜隆坦的母亲非常强壮,拥有多年积累的智慧,但在杜隆坦的记忆中,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母显露出老态。
“我会召集一支战队。”杜隆坦做出决定。
“不!”喝止的命令在身后响起,杜隆坦停下了脚步。服从父亲的命令已经成为他根深蒂固的习惯,几乎就像是一种直觉。
但盖亚安却不同意酋长的命令:“杜隆坦会处理好那些闯入者的,就让他率领战队吧。”
加拉德一把推开妻子。酋长的动作专横而满怀怒意,但杜隆坦知道,是恐惧让他父亲变成这样。通常如果父亲对待母亲如此不敬,盖亚安肯定会还以颜色。加拉德是酋长,但她是酋长的妻子,她绝不会容忍被这样对待。
而这一次,母亲没有任何回应。
“听我说,”加拉德对屋子里的所有人说道,“如果我不亲自去处理这个威胁,整个氏族都会知道——会相信——我怕了,甚至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好。因为古尔丹的谬论,他们已经在感到不安了。如果他们再看到我无法领导......”他摇摇头,“不,我会亲自指挥这支战队,带着胜利回来。我们那时就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我会让霜狼看到,我能够保护他们。”他的话无可辩驳,即便杜隆坦拼命想说些什么。他看看自己的母亲,从母亲的眼中看到了无声的请求。今天,盖亚安不能与加拉德并肩战斗。在他们的人生中,盖亚安第一次怀疑丈夫将无法回来。氏族不能在一场可怕的战斗中同时失去酋长、薪火传承者和酋长的儿子。痛苦绞勒着杜隆坦的心。
“我会一直看着他,母亲。他不会受到伤害......”
“我们流放那些软弱的人,杜隆坦,”加拉德打断了他,“这就是我们的处世之道。你不能只在我的身边打转,更不能干涉我。如果这是我的命运,我会接受它,但我不会接受别人的扶助,无论是在寒冰的背上,还是用双脚站在大地之上。”他说话的时候,身子还在微微晃动,盖亚安伸手扶住了他。这一次当他将自己的爱侣推开时,动作中没有半点粗蛮。他伸手抓起那只瓢,看了它一会儿。
“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什么?”他对杜隆坦说道。在听取儿子的报告时,他一口口喝下了瓢中的药汁。
第五章
盖亚安和杜隆坦帮助加拉德穿上战甲。它与狩猎甲胄不同,是专门被设计来抵挡斧刃、战锤和狼牙棒的,而狩猎护甲防御的主要是蹄子和长角。野兽往往攻击身体从胸口到大腿的中心区域,兽人也会攻击这些部位,但肩膀和喉咙这样的脆弱部位更是近战中兽人武器所青睐的目标。喉咙要用厚硬的皮颈甲护住,肩头要戴上镶有金属钉的大块甲片。但对于一个荣誉就是全部的种族,护甲远比不上武器重要,兽人带上战场的武器都非常巨大。
奥格瑞姆手持的武器是毁灭之锤,他的家族正是以这件武器作为姓氏。它由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作为锤头,被镶嵌金钉的双股皮带固定在粗橡木柄上。仅仅是这根沉重坚硬的橡木柄就已经是一件致命的武器了。
雷击是加拉德在狩猎时使用的家族武器,他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是一把名为“裂斩”的巨斧。这把斧子有双侧钢刃,都被精心打磨到只有一片树叶那样薄,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强大武器。加拉德很少会将它绑在背上,但今天,他自豪地拿起了它。
杜隆坦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为自己是加拉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当霜狼酋长大步走出屋门时,腰背挺得笔直,就像杜隆坦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样,一双深褐色的眼睛里闪耀着正义的怒火。奥格瑞姆已经将命令传达给了氏族中的战士们,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也都披挂好了战甲。
“霜狼兽人!”加拉德的声音在人群头顶回荡,“根据我的儿子带回的消息,有人闯入了我们的森林。那不是公开拜访我们的狩猎队伍,而是一些鬼鬼祟祟的家伙。他们从我们的树上砍下枝条,他们的身上带着陈血的气味。”
不久之前的回忆让杜隆坦不由自主地想要打哆嗦,他立刻压抑下这种冲动。兽人认为新鲜的血腥气有一种独特的气味——只要那些血是因为狩猎或荣誉而泼洒,但陈血的味道,那种腐败变质的臭气......没有兽人愿意让身上有这种气味。战士们浴血奋战,以此为荣,但随后就会将血污清理干净,穿上洁净的衣服庆祝胜利。
会是古尔丹所说的那些红步氏族吗?他们是不是因此才自称“红步”?因为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会留有他们的杀戮所泼溅的血液?当古尔丹提到他们的时候,杜隆坦本来对他们还有一些好感,觉得如果他们来到霜狼的地界,他会欢迎他们。任何拒绝那个术士的兽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兽人。在嗅到那些兽人的气味之前,他一直都抱有这样的想法。
应该允许被杀死的灵魂离开——无论是兽人的灵魂,还是像裂蹄牛这样野兽的灵魂,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雪兔。他们被杀死,被吃掉或火化,从此返回到大地、流水、空气和火焰中。他们留下的皮革都会得到清洁和鞣制,上面绝不会有一点烂肉和血渍。
想到会有兽人执著于生命的腐败,杜隆坦不由得在心中感到惊骇——每一名认真倾听酋长说话的霜狼兽人一定也有着和他同样的心情。
“我们会冲向这些入侵者,”加拉德继续高呼,“把他们从我们的森林中赶走,如果他们反抗,就杀死他们!”
他举起裂斩,高声吼道:“Lok’tarogar!”胜利,或死亡。
霜狼兽人们一同呼吼起来,并在这吼声中与他们的酋长一同驾驭已经迫不及待的座狼奔向战场。杜隆坦跳上利齿,回过头,越过没有披甲的肩膀迅速向父亲瞥了一眼。只是一瞬之间,刚刚还重压在加拉德身上的疲惫感又掠过了酋长的面庞。随后,加拉德将一切倦意都赶走了。杜隆坦明白父亲有着怎样纯粹而坚强的决心。
杜隆坦突然感到喉咙一紧,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
***
加拉德强迫自己将迟钝的意识集中在胯下坐骑的纵跃上。霜狼兽人正全速扑向那片遭受入侵的树林,没有采取任何隐蔽的措施。
他的儿子和奥格瑞姆报告说看到了七个兽人的脚印,毫无疑问,那里还会有更多兽人。敌人的数量甚至有可能超过霜狼战队——人数从来都不是他的氏族的优势。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杜隆坦和奥格瑞姆都没有发现任何入侵者带有座狼的痕迹。那些入侵者(如果他们真的是红步兽人)将要面对二十余名兽人战士,但真正与他们作战的力量将更加强大一倍,他们的霜狼也都接受过和兽人战士一同作战的训练。在霜狼氏族中,兽人和座狼的关系更像是朋友,而不是主仆。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敌人。至少加拉德是如此希望的。他也只能希望自己可以坚持得足够久,履行职责,返回家园,继续和这种拖累他的,该死的虚弱作战。
现在他的症状很像是被一种低贱却危险的虫子咬了,兽人叫它“掘地者”。被咬伤的人会连续数日衰弱无力,这对兽人而言是非常可怕的事。疼痛、剧烈地抽搐、断肢,这些症状兽人都知道该如何应对,但那种虫子带来的萎靡和昏睡会让兽人不知所措。但盖亚安和德雷克塔尔都没有找到他被掘地者咬过的痕迹,德雷克塔尔也没有从众灵那里听到任何声音,能够揭示这种神秘的疾病本质是什么,实际上,盲眼萨满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当杜隆坦带回有敌人出现的消息时,加拉德就知道这是一个预兆。他将起身奋战,他将重整旗鼓,战胜这种疾病,就像战胜其他所有敌人一样。实实在在的胜利也会鼓舞起氏族的士气。古尔丹可怕的预言,他的出现所引起的不安,他那个奇怪的奴隶,他的绿皮,还有所有那一切都让霜狼氏族笼罩了一层不祥的影子。让敌人流血会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加拉德渴望着再一次挥起正义的战斧,让热血随之喷涌。也许这正是众灵的一次试炼——只要赢得胜利,他的力量就能恢复。疾病一直在暗中觊觎他的氏族,即使是作为酋长的他也无法幸免。现在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他将彻底把恶疾打退。
那些傲慢的闯入者在受伤的树下留下了一片宽阔的足迹,他们的脚印污浊了新雪。霜狼们紧随其后,宽大的狼爪沿着他们的足迹一路前行,在一座山脚下拐了个弯。老祖父山的顶峰此时消失在了低矮的云层里。
这些闯入的兽人正在山丘的另一侧等待他们。加拉德对此感到高兴。
他们站成一排,腰杆挺直,一言不发。一共只有十七个兽人。霜狼兽人的护甲和武器都显示出北方民族的风格,而这些入侵者的护甲却显得五花八门,格外怪异——熟皮,生皮,金属甲片杂驳纷乱。他们的武器也同样形制不一。
但这不是让霜狼兽人感到惊诧的原因。加拉德知道,让他们感到惊诧的原因是他们的盔甲上,皮肤上,尤其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覆盖着铁锈色的,脏污的,干结的陈旧血印。
那些兽人之中最为高大,肌肉也最发达的一个站在队伍中央,比他的同伴靠前一些。加拉德相信他就是他们的首领。他剃光了头壳,也没有戴头盔。
加拉德轻蔑地看着他。这些也许就是红步兽人吧,他们在北方活不了多久。
在寒冷地带,兽人战士会保留自己的头发,头发和头盔在保护肩膀上的脑袋的同时也有助于保暖——在这方面,奥格瑞姆是氏族中唯一的叛逆者。加拉德决定要砍掉那颗秃头,看着他落在雪中,看着从那里面流出的热血将白雪融化。
早些时候,盖亚安曾经请求他不要参与这场战斗,几乎是乞求。盖亚安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妻子的恐惧比折磨他的疾病更让他感到警惕。盖亚安是他认识的最勇敢的兽人,但现在,加拉德发现自己成为妻子的弱点。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结伴而行已经有这么长时间,加拉德完全无法想象没有盖亚安陪伴在身边,他该如何战斗。但这就是他现在要面对的状况,他很清楚盖亚安为什么会选择留在村中。
这种耗竭性的疾病是不适合兽人的,加拉德不会容忍它继续存在下去。
他不会责怪盖亚安没有陪伴他。
他从喉头发出一阵低吼,凝聚起全部力量,用它们做了两件事——举起裂斩,张开嘴发出洪亮的战吼。
他的声音立刻得到了其他霜狼兽人的回应。他的身边有儿子和奥格瑞姆。就像他们和盖亚安以前经常做过的那样,两名年轻的战士协同一致向前猛冲,气势悍勇,令人胆寒。他们的座狼紧紧靠在一起让两名骑士并肩冲锋,然后便分向两边,朝各自的目标冲锋而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