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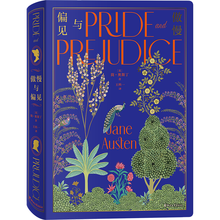


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笔下的野性世界
野性向文明的复归,生命对人性的拷问
在本书中,杰克·伦敦一反《荒野的呼唤》的故事,讲述了一只幼狼如何从荒野中进入人类的文明世界。作者从白牙出生前北国荒原的渲染,引出白牙的母亲吉喜与独狼的故事,写到白牙早年奇特的独自冒险和*早进入印第安人的营地,在狗群的歧视和欺压下成长为拉雪橇的头狗。后来白牙落入美人•史密斯之手,这是一个邪恶的人,他让白牙成为斗狼,专门跟各种各样的狗,甚至狼和猞猁斗,从中获利。结果白牙跟一头斗牛犬斗,命悬一线,要不是一个开矿的专家前来相救,白牙必死无疑。从此以后,白牙的命运有了根本的转变,白牙从只知道仇恨和杀戮到渐渐懂得了爱,成了一头忠诚救主的狗。
《白牙》:
第一章 肉迹 冻住的河流两岸是黑压压的云杉树林。风刚刚吹走树上的白霜。树木似乎东倒西歪地挤在一起,在逐渐暗淡的光里,连成黑魃魃的一片,透着不祥。无边的寂静笼罩着这片土地,荒芜死寂,了无生意。它那么孤单寒冷,不光是透出悲凉的意味。树林里暗含着一种笑意,可这笑意比悲凉还要可怕——犹如斯芬克司的微笑一样阴郁,冷若冰霜,无疑交汇着残酷与无情。这是一种独断专横、不可言传的智慧,永恒的智慧正在嘲笑生命和一切挣扎的徒劳无益。这里是蛮荒无际、冻结心肺、寒冷刺骨的北国。
但是在这片荒野上,确实有生命公然与北国作对。一队狼狗沿着冻住的河流艰难前进。它们硬硬的皮毛上结了冰霜。它们喷出来的热气马上凝结,一团团落在短毛上,形成了冰霰。狗身上都套着皮具,身后拉着由挽绳连着的雪橇。雪橇上没有人。雪橇由厚实的桦树皮制成,一整张贴着地面。雪橇的头部向上卷起,就像纸卷一样,这是为了把前面挤压出来的软软的雪浪压下去。
雪橇上牢牢地绑着一个狭长的方形箱子。虽然雪橇上还有几块毯子、一把斧头、一个咖啡壶、一个平底锅,可最显眼、最占地方的,还是那个狭长的方形箱子。
狗队前面,一个穿了宽宽的雪鞋的男人正在艰难跋涉。雪橇后面,也有一个男人在跋涉。雪橇上的箱子里,躺着第三个男人,他的跋涉已经结束了。荒野征服他、打倒他,打得他动弹不得,无力挣扎。荒野向来不喜欢运动。对它而言,生命是一种冒犯,因为生命就是运动。荒野总想摧毁运动。它冻住河水,使它不能流向大海;它把树汁从树干中榨出,使大树里里外外全被冻住;不过最可怕的是,它总想压服最最有活力的人类,因为人类一直违背它的格言:一切运动终将停止。
可一前一后,两个还没有死的男人依然无所畏惧、不屈不挠地前进着。他们身披鞣皮。他们呼出的水汽在脸颊上、唇上、睫毛上凝结成霜,使他们的脸难以辨认。他们仿佛戴着幽灵的面具,像鬼界幽灵葬礼上的殡葬师。可在这些下面,他们还是人,深入这片荒芜死寂、嘲笑着生命的土地;他们是置身于一场巨大冒险的渺小探险者,与这个像宇宙一样深远的浩瀚世界对抗。这个世界遥远陌生又毫无生气。
他们继续前进,沉默不语,放缓呼吸,节省体力。四面八方的死寂似乎触手可及,压迫着他们,影响他们的思考,就像深水的大气压力影响潜水员的身体;死寂以无边的空旷和不可变更的法则打压他们;死寂把他们打人思想的最深处,像从葡萄里压榨出葡萄汁一样,把人类灵魂里虚假的热情、兴奋以及过度的自尊全部压榨出来,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只是渺小有限的尘埃和微粒,凭着一点不高明的狡诈和小小的聪明,活动在强大的自然元素和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中。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太阳的白天十分短暂。暗淡的光线渐渐消失,一声微弱的长啸远远传来,在寂静中响起。这啸声突然飞冲云霄,达到最高音后,持续不断,令人心惊胆战。之后,它才慢慢消失。要不是这长啸中带有某种饥肠辘辘和凄惨凶猛的意味,它也许会被误认为是迷失灵魂的哭泣。走在前面的男人转过头,与后面的男人对视了一下。然后,隔着狭长的箱子,他们互相点了点头。
第二声长啸响起,像针一般尖锐,划破了寂静。
两个男人寻找着声音的来源。声音来自后方,来自他们刚刚走过的空旷雪地的某处。接着,第三声长啸在第二声长啸的左边响起,这是回应。
“它们在追我们,比尔。”走在前面的男人说。
显然,他说起话来很吃力,声音沙哑,听上去不那么实在。
“猎物快没了,”他的同伴接了话,“我都好多天没看到兔子影儿了。” 之后,他们不再说话,可他们能清楚地听到身后断断续续传来猎食者的长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