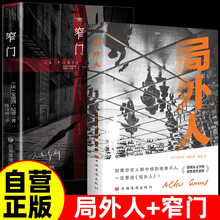当看到这个男人把手伸向色拉时,美登里有些疑惑:他为何能那般悠然地品尝生菜色拉,即便那是一份拌着鹅肝的高档品?
当切下最后一片黏黏的泛着脂色光泽的肉片时,长原把叉子和刀摆成一个十字,慢悠悠地把酒杯端到嘴边。侧眼看去,他这个动作似乎想用红葡萄酒把鹅肝的余味掺和起来细细品味。美登里觉得他的举动实在显得做作。
“厨师长刚才老往这边瞅呢。”美登里冷冷地提醒道,“他等着把下一道鱼送出来,都快不耐烦了,还不快吃!我可不喜欢吃冰冷的菜。”
“他们不至于这么不懂规矩吧。”长原终于右手拿起刀来,用叉子叉起肉,放进嘴里。这个动作两秒都不到。把仅三厘米大小的小小的肉片特意切开放入口中,在这个场合显得颇为滑稽。
美登里迫不及待地在餐桌上看起表上的时间来:“拖到这么晚,我不得不放弃甜食了”。
“有什么关系呢?我会送你去机场。现在这种季节不会堵车,用不了一小时准能到。”
“领机牌至少得在二十分钟以前。还得横穿候机厅,上电梯。所以,七点以前必须离开这儿。我最不喜欢在飞机就要起飞时才匆匆赶到。”
“要是这样的话,”长原避开美登里的视线,把最后一小块鹅肝放进嘴里,说道,“再住上一晚不挺好吗?”
美登里思忖,在这种场合,女人应该作何表示呢?眼前是七年前分手的男人,当时颇费了一番周折。现在这个男人又直率地在挽留自己。
美登里心中不无胜利感,但更多的是厌恶。这种感觉几乎令她作呕。
来到札,她忽然想见见长原。她常常对自己为人懦弱暧昧的性格感到懊恼,况且这个男人对现在的自己更加缺乏了解。干吗要上这儿来?出于什么目的上这儿来呢?实在应该重新考虑。
“明天下午我还要讲课呢。”美登里语气平淡地说道,不强调讲课这个词更能体现出日常的气氛,“学生们都知道,北海道分校的讲课今天全部结束。明天他们会兴冲冲地来找我,到时候我不出现,他们会吃惊的。”
“所以我说,明天有早班飞机,你乘那班飞机不就没问题了吗?”长原急不可耐地挽留。他的语气很坦率,好像美登里理所当然地还是自己的女人。
这个男人居然还不自悟,美登里差点儿出声来。于是,她直截了当地说:
“我可得负责啊。以为我还能像以往那样自由自在任性过日子。”
用鸟羽毛和黏土制作人造花,把这种技术第一次介绍到日本来的虽然不是美登里,但是把这人造花取名为“素丽花”,并在花的着色技术上加以创新,确实是她们的功劳。最先注意到的是一家对流行极为敏感的杂志,以“富有新意,艺术感强,人造花以其质朴的美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的醒目标题作了报道。正巧某电视台的制片人看到这篇报道,于是,在一个艺术表演节目的背景布置上,采用了这种人造花。而且,每周的节目摄影中都采用美登里制作的人造花。从那时起,“素丽花”这个词逐渐在媒体上传开了。当时,美登里几乎天天在想,自己大概是“时来运转”了。各个杂志社纷至沓来,要求登门采访。大百货公司也发出邀请,请她担任手工艺教室的讲师。她自己暗暗吃惊,居然还当上了早晨以主妇为对象的专题节目主持人。电视台对美登里的期待并不只是作为一个手工艺家,还希望她“通过花卉来探索生活和人生”。美登里不知不觉地俨然成了一名评论家了。周围的人都在议论,美登里的成功一定与她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从普通的职员到艺术创造者—辉煌的转折”,新闻界为她绘制了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当对工作和自我都不满足时,有一天,我决定出门旅行。在墨西哥的荒野,我看到了一朵美丽的玫瑰,可是,那不是真正的玫瑰,它是用羽毛和泥土做成的。当我一看到它时,心中顿时有了灵感。对!我要把它带回去,让它在日本的大地上开放……”
最近,在不乏即兴者参加的演讲会上,美登里总是这样叙说。可事实并非如此。凑足存款,去参加廉价的墨西哥团体旅行确有其事,但是,有关人造花制作方法,那是在回日本以后才知晓的。同一旅行团里有个老妇人,是外交官的遗孀,她曾经随丈夫在南美各地生活。美登里和这个老妇人一见如故,旅游回来重访她时,讨教了制作人造花的方法。
“当地的妇女常常制作人造花,我是跟着她们学的。刚开始完全照着她们的方法做,都失败了。因为日本湿度高,不一会儿就散架。整整花了五年工夫,我才掌握好合适的黏度。”超世越俗的这位老人对美登里的成功由衷地感到高兴。
“真没想到,我这样的老太婆教的方法,竟让你做出那样色泽鲜艳的花来。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你,我都好高兴。”
美登里想,自己没什么对不起人的。若是像老妇人那样,用花里胡哨的原色来制作的话,“素丽花”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流行。美登里大胆采用了黑白两种单色,这种配色无疑说明,她独具慧眼,洞察到了现代艺术的走向。加之美登里略有文才,去年出版的散文集《没有花怎能生存》,虽然经过了编辑的苦心修改,但毕竟算是出自她的手笔。
女职员一跃成为花卉艺术家—一个女性开拓的辉煌人生。
散文集里充斥着陈旧的宣传词藻,使用了大量的照片,且价格定得很高。但出人意料,销路居然不错。
前天和昨晚,在住宿的札的饭店里,她收到了饭店经理的致敬信和款待的水果。房间安排的是四方形双人房,从最上层的窗外向下望去,宽阔的广场上仿佛铺洒了一层薄薄的光珠。就是在这个时候,美登里下决心去见见长原。当然,一乘上飞机,不,在这以前,从有人请她到札任手工艺教室讲师时起,长原就一直在她的意识中出现。只不过这犹如在记忆的沼泽中噗噗冒出的气泡,心思一集中,气泡就大起来,但不去想它时,它便转瞬间消失在沼泽底下了。对长原的情结,仅此而已。气泡在不知不觉中变大,并浮出水面来,这当然源于美登里作为女人所特有的炫耀心理。说得好听些是来告别,实际上是想对自己没有强烈占有欲的男人显示一下已经身价倍增的自己。
和当时比,美登里的体重增加了四公斤,脸倒反而变小了。因为脸颊显得消瘦,在化妆上颇费苦心。不仅如此,身上的穿着更是今非昔比。昨天在宾馆房间里穿的是意大利的丝绸连衣裙,粉红和嫩绿,配色大胆的服装是为了和主办人会餐而特意准备的。但昨晚和那些人的会餐使她大为扫兴。他们百般炫耀在地方城市里的权势,这种低劣的素质正是美登里深恶痛绝的。
今天晚上,百货公司的宣传部长又邀请她去品尝寿司,她以身体疲劳为由谢绝了。去不去芒野的日式烹调店用餐呢?那是在东京时打听到的。一位编辑朋友告诉过她,那里的女老板很豪爽,一个人去吃也很有意思。美登里边看着札的夜景,边慢吞吞地考虑。已经快八点了,她终于打定注意,拨起电话来。手里拿着一张名片,是赞助这次研讨会的地方报文化部的人给她的。
“请问,您知不知道有个叫北荣的广告代理店的电话号码呢?北方的北,繁荣的荣。”
“噢,我很熟啊。那家店和我们有业务往来。”
听到报社的人立即说出那家店的电话号码,美登里舒了一口气。看来长原活得并不那么潦倒。这种安心感促使她再次拨起了电话。她想要是不在也就算了,自己只不过想在单独旅行的夜晚排遣一下而已。
电话铃响了十多次,正当她准备搁下话筒时,有个女人说话了,声音显得有点不自然:
“这儿是北荣广告社。”
“长原先生在吗?长原武文先生。”
“我这就去叫他。对不起,您是哪一位?”
“我叫永田美登里。”话刚说出口,美登里心里有点儿后悔。干吗急着把这张王牌亮出来呢?应该稍等一下,如此对方会先开口向自己打招呼。以前都是如此,没等男人说出真心话来,美登里就急不可待地先开口。所以,每次都是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
在长原来接电话之前,美登里轻轻地卷了几下舌头,似乎这样说话可以流利些,听起来可以格外明快些。这种做法果然奏了效。
“是我,我到札来了。”
电话机里传来的并不是美登里所期待的沉默。对方一点也不逊色,口气爽朗地回答:
“哟,好久不见啦!我看了报纸和宣传招贴,知道你要来。你彻底成了名人啦。我在犹豫,像我这样的人该不该给你打电话。”
“没这事。不过,时常挂念倒是不假。”
“深感荣幸。”长原诙谐地说道。但美登里听起来充满揶揄。
“一起吃顿饭怎么样?”
“这个,今天我得回去。”
“什么时候的飞机?”
“八点二十分,末班飞机。”
“时间还早。好,我去找一家味道最好的店。”
正如长原所说,找的这家餐厅确实不错。鹅肝色拉之后是一道白葡萄酒煮比目鱼。美登里用面包蘸着酱汁,吃得精光。不足之处是上菜太慢。除了长原和美登里以外,只有两批客人。一道吃完到第二道菜上桌,等的时间实在漫长。
时针指到了六点四十分。
“没时间了,不好意思,你等着慢慢品尝甜品吧。我先告辞了。”
“你再等一下,我送你去。服务员,快把两杯咖啡送上来。”
看得出长原对这家餐厅很熟。穿着黑制服的男服务员立即主动地把咖啡端了上来。动作之快,与刚才慢吞吞的上菜速度天壤之别。
小杯的热咖啡,两口就喝完了。似乎就是为了领情,美登里抛下手中的餐巾纸,站起身来,说:
“谢谢款待,再见。”
“我已经让车等在外面了。”
长原刚递了一个眼色,有个男人便把美登里的皮大衣拿到桌边来了。
“快走吧。”说话间,长原已经把车门打开了。
美登里坐进车里,开口道:
“账怎么结?很抱歉,让你破费。”她一直惦记着结账的事。
“这么点小事……”长原似乎微微笑了一下,“我毕竟也在工作,请名人吃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是吗,那谢谢你啦。”
进口的一瓶红葡萄酒和一瓶白葡萄酒都喝空了,费用肯定不小。该不会用公司的钱请客吧?实际上,在用餐时,美登里始终在思量,自己该在什么情况下付款。是飞快地将信用卡交给餐厅的服务员,还是等长原离开座位时,顺势到账台去付呢?
近来从没有为和男人聚餐时如何付款而伤脑筋。七年前,在和长原交往中也没在意这种事,因为长原从来是一毛不拔的。任何场合掏钱的必定是美登里。当然,那时吃的可不是法国大菜,而是盒饭店的炖鱼套餐,通心面加牛肉馅饼,或是八宝菜当浇头的汤面。在经常光顾的酒吧里喝的也是最廉价的酒。
美登里只问过长原一次:“我说,你老让女人付账不脸红吗?”
“从来不。”长原故意眨了眨眼,“我认为谁有钱就该谁付账,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但是,美登里心里很明白,长原绝不属于那种超脱不羁的人。他是个自我意识强得近乎神经质的男人。当时,他在一家业界杂志社的编辑部供职,该社出版的杂志根本无人问津。他的朋友们几乎都是些诗人和教师,他们在交往中从来不像新闻圈人士大言不惭宣扬的那样“能喝的喝个足,有钱的带头付”,他们也不可能那样去做。分手两年以后,美登里才明白,实际上长原是不愿意在自己身上花钱。和长原分手后交往的另一个男友则不同。他非常乐意为美登里购物,比如,小小的项链和西服,还炫耀似的把她带到自己熟悉的酒吧和餐厅去。那个男友还教她怎么品葡萄酒,选择菜单,怎样按季节饮食。有这样的男人作比较,美登里至今对一毛不拔的长原愤愤不满。
“比以前大方多了!”美登里嘟囔道。这是这天她对长原作出的第一次小小的报复。
长原眼睛微微一亮,但是,他并不恼火。和七年前不同,他已经不年轻了。
“没办法呀。”长原略微迟疑了一下说,“当时,我实在是没钱。住的是什么房子,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应该是最清楚了。”说着说着,他渐渐地与美登里保持距离了。这正是长原不高兴时的特征。
他一点儿也没变,美登里心里暗自思忖。下颚挺直端正,从前美登里很喜欢他下颚的棱角。那细小平庸的单眼皮的眼睛,在这种线条的衬托下,总给人狡猾谲的印象。他的声音低沉,黑黑的胡剃痕几乎布及喉结处,使得衬衫的领口和领带显得又窄又紧。这个男人一点儿也没变。眼下这种场合,用“当时……”这个词会让人觉得牵强。
“我不也一样……”美登里忽然觉得一阵心酸,好像好不容易躲过对方的反击似的,“我那时也没什么钱呀,在效益一般的公司里当一名普通的女职员。你知道我当时的工资才十万五千日元,其中要付掉两万八千的房租,再存到银行里两万,剩下的全用在你身上了。”
美登里觉得自己有点儿醉了。为什么还要对过去的情人发泄怨恨呢?不对,还是太软弱。不,甚至有点献媚了。这不,长原的左手现在完全放在自己右手背上了吗?美登里没有拨开长原伸过来的手,她对自己这样做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归途的车中和久别重逢的往日恋人手握手地在一起,谁能非议呢?她觉得自己确实有种贪婪的心理,其中也不乏作为女人的自负。但是,她还是作了小小的抵抗。
长原的指头伸进了美登里的手指间,左右蠕动。这时,美登里说道:
“听说你一回北海道就结婚了?”
“哟,你全知道!”
“总有人会传过来的。”
确实不是风闻。女人有自己获取信息的特别渠道。
“也许是我对一切都看穿了,抑或是很想做个真正的孝子,让当爹娘的中意就行,所以娶了一个在地方银行工作的老实巴交的媳妇。”
“噢……那孩子呢?”
“一个孩子,是女孩。”
“肯定很可爱吧。”
“嗯,挺逗人喜爱的。因为工作关系,我也摆弄点儿摄影,一到休息天,老是一个劲儿地为孩子拍照。对了,你还没有成家吧?”
“对啊,没人娶我呀。”
“哪有的事啊,你多大年纪了?”
“三十一岁,比你小四岁。你已经忘了吗?”
俩人这么交谈时,长原的手指不停地搓动,四个指头都渗出汗来了。
“请问,是几点的飞机?”出租车司机慢吞吞地问。
“八点二十分。不能再开快点吗?”
“尽量开快。今天路上还算车少,问题不大吧。”
“拜托了。”美登里正朝前倾着身子对司机说话时,猛地被往后一拉,长原用劲握住了她的手,皱起眉头说:
“时间来不及了。”
“咦,刚才你不是说绝对来得及的吗?司机也说没问题。”
“绝对来不及!”长原这么说时,有点儿孩子气。他的这种表情是想让美登里觉得他还在爱着自己。
“再住一晚吧。”他细声劝道,“明天乘早上九点的飞机,中午肯定能赶到。去机场先订好那班飞机票,今晚赶不上也没关系。”
美登里缄默了。虽然明摆着对他已没有爱情,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能使得男人如此竭力挽留自己,这令她感到分外惬意。
“行吗……”长原转过身来,一边用左手更紧地握住她,右手轻轻地伸向美登里的脖颈,迟疑不决地用手指横画了几个半圆后,蓦地将手指插入她的领口。但是,长原在车里的姿势使他的手指伸不到更下方。他把右手重又从美登里的领口伸出来,一瞬间隔着衣服又将手掌实实地按在美登里的乳房上。隔着皮大衣和里层的丝绸衣服,长原用食指熟练地触摸着微微向外翘的乳首,缓缓地画起圆弧来。在乳首中心小得难以比喻的表面,长原画了好几十回,画了好几个“の(日文假名no)”字。
夜色朦胧,美登里和长原的目光相遇,她意识到自己痴呆似的张开了嘴,大腿屈伸了两三次,而为了避免发出呻吟声,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快感好似一股激流一下子贯穿了全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