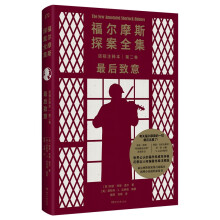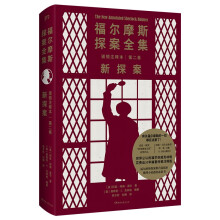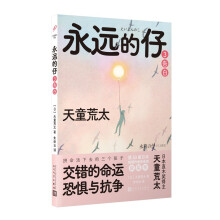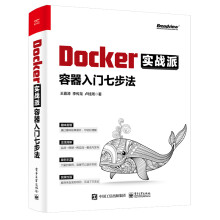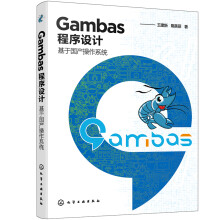等 待
每个人都梦想着自己身上会发生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情将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比如说我最好的朋友莉雅,她迫切地渴望着能离开现在所住的小区,去某个沐浴着阳光的热带海岛,享受椰果和烤鱼,从此快乐地生活下去。我的异父弟弟丹尼则一心想要为曼联队踢冠军杯决赛,进制胜球。我认识的人里面至少有三个五音不全的想要参加大型电视选秀节目,奢望能够一夜成名、暴富。
我和他们也没什么不同。我已经等了两年,等待着能够改变我的人生的大事发生。但和多半人的期待不同,我并不太愿意告诉别人我所等待的事情,害怕听者会错了意。
说实话,我在等待某个人死去。不是指哪个老人,你明白吧;也不是我们的数学老师麦克纳马拉先生,不是香农·沃特尔或马舍尔·克伦比,也不是任何其他我认识的人。我等待的这个人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从来没有见过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存在。尽管我现在多半的时间都在思虑、想象他的模样和他的喜好,但永远也无法了解到任何与他相关的事情——他甚至可能是来自平行宇宙里的一个人。
此刻我躺在这里,精疲力竭,动弹不得,内心充满了恐惧,但还是等待着。而他则过着自己的生活,做着每天例行的事情,而后在夜里睡去,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我等待着他死去,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1
“贝基……贝基……快点儿,亲爱的,醒醒。”
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妈妈穿着睡袍站在沙发后。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已经有一些日子了,因为我的气力不够,不能爬楼去卧室睡觉。现在去卧室,就好像要我穿着拖鞋爬喜马拉雅山一样。
她伸手打开了门厅柜上的小桌灯,柜子上摆满了我在越野赛上获得的奖杯。她睡眼惺忪,头发凌乱。我瞥了一眼壁炉架上的钟,两点二十。
“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继父乔在外厅低声讲着电话。
“是格兰吗?”我问,“她还好吗?”
“她很好。是医院的电话。他们想要你立刻过去。”
“现在?”
妈妈点了点头,关切地看着我。
“可现在还是半夜啊!”
“他们认为已经为你找到了一颗新的心脏。”
我那快要衰竭的旧心脏停了一下跳动。“可是……”
“我们现在就得出发了。格兰会来照看丹尼。”
妈妈拿着那个蓝色的双肩包。那是我刚上心脏移植等待名单时买的。我恍惚地盯着双肩包,时间飞逝,我早已不记得当年精心放在包里的都是些什么了。
“妈妈……”
“什么事,亲爱的?”
“我……我不能去。”
……
“你什么意思?”
“我不能去。”我语气更加坚定地说。妈妈焦急地看着我。“我真的还没准备好。”我对她说。
“没有准备好?”她惊讶地看着我,“贝基,我们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啊!”
“现在是夜里……”我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还没洗头发呢。”我的眼中一下子涌满了泪水。妈妈抱住我,好似我只有四岁而不是十四岁。过去的几个月里,每天晚上我都做着同一个噩梦,而且那个梦每晚都很可怕。一群红眼恶狼追赶着我,我累得精疲力竭,跌跌撞撞地走到一条小河里。但河水里像有什么东西,知道马上就有吃的了,兴奋地翻卷起浪花来。河岸对面,所有人都在呼喊着要我穿过小河,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但我从来没有梦到自己到底有没有来到河对岸,因为每晚这时我都会被自己的心跳声震醒。每次醒来我都是浑身湿透,大口地喘着气。
“会没事的,贝基。”妈妈说。
“你确定?”我犹疑地盯着她看。她却没有回答我。
“我害怕。”我说。
“要是不害怕那才傻呢。”她把我抱得更紧了些,一边抚摸着我那还没洗的头发,一边低声说,声音有些颤抖。我想了想每晚的噩梦,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出选择。我可以待在家里,洗了头发,等着未来几个月慢慢死去;或者我可以去医院,让医生切掉我的心脏,把某个死者的心脏缝到我身上,或许这样我就能安全地抵达对岸。
对岸到底是何方也都无所谓。
2
乔在雨中开车载着我们向医院驶去。最开始他和妈妈兴致勃勃地聊着天,但过了一会儿就再也没什么可聊的,安静了下来,于是他打开了收音机。电台播放着一首庸俗
的流行歌曲,唱着某个人把自己的心给了另外一个人。妈妈瞪了乔一眼,他领会了妈妈的意思,赶紧换了台,调到一个“为世间所有心碎的灵魂”开放的深夜畅谈节目。
“噢,我的老天啊!”她叹气道。
我坐在车后排座上,身上盖着一条羊毛毯,看着大大的雨点从车窗上慢慢流下去。
“没事儿的,妈妈。”我气喘吁吁地低声说,“没关系的。”但她还是关上了收音机。余下的路程,我们便一直在一片安静中走过。路上的车不多,路边的商店多半都关上了防盗铁门。我们碰上几个人,他们在外面玩了一夜正准备回家,此时在街道上欢笑玩闹着,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的事情。
几个人里有一个女孩,比我大很多,但有一头黑色的长发,和我以前的一样,只不过现在我的长发为了方便打理都剪掉了。她的胳膊搭在朋友肩上,一起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踏着舞步,在雨中唱着歌。我们的车开过的时候,我的目光与她相接,她对我粲然一笑,还挥了挥手。我慢慢地挥手回应,但心下立刻觉得自己的思想可鄙。她根本不会知道,此刻我是多么渴望与她互换位置。
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三点。尽管已经是后半夜,但医院里还是挤满了人。乔去给我找了一轮椅,我们在前台挂了号,而后他推着我来到心脏科。
我很高兴他们允许妈妈留在身边陪我,因为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护士把透明的氧气面罩扣在我的脸上时,我突然惊慌异常。我本该能闻到麻醉气体或别的什么味道的,但什么都没闻到。一个可怕的想法一闪而过。如果手术的时候麻醉剂失效了,我还醒着该怎么办?
3
“都过去了,贝基……醒醒,睡美人。”
我完全不知道是谁在跟我说话,也不知道是什么都过去了,只觉得喉头酸酸的,嘴里像沙场一样干。
“给你找点儿冰块含着吧?”一个稍微活泼一些的声音问道。
这个声音我也不熟悉,但我还是点了点头,而后竭尽全力睁开了眼。刚睁开眼睛,我就后悔了。屋子里非常明亮,太亮了。电视开着,叽里呱啦地响着,节目很垃圾——一堆波浪线和数字。而且还有人偷走了我的沙发。我彻底糊涂了,低头看到手腕上和胳膊上挂着细细的塑料管子,天知道我身上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有人正在摆弄着电视。
“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
我肯定知道这个声音是谁。我有些恶心,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慢慢地转过头。妈妈和乔就坐在我的床边。他们身后通往门廊的门口站着一个黑发、黑眼睛的高个子男孩,他正在盯着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