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事可不止这一件,”维兰德说,“我们别忘了那本古怪的相册。而且死者的遗孀说,西蒙·兰伯格是个有着很多秘密的人。现在我们要集中精力搞清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显然,表面和本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这个看上去彬彬有礼、寡言少语、做事有条有理的摄影师,骨子里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人对他的了解会更深一些,”马丁森说,“因为他看起来似乎一个朋友都没有,所以要找到一个了解他的人很难。”
“他不是参加了隆德的天文爱好者协会吗?”维兰德说,“我们得和这个协会联系一下。还有以前为他工作过的助手。在于斯塔德这样的小地方生活了一辈子,不可能没有人熟悉他。我们和伊丽莎白·兰伯格的谈话也只是浅尝辄止。换句话说,需要深挖的地方有很多。但各条线索需要齐头并进。”
“我和巴克曼谈过了,”斯维德伯格说,“你说得没错,他的确早早就起床了。我到他家时,他妻子也已经起来。对他们来说,凌晨4点基本上和中午差不多了。可惜他也没看清那个打过你的人长什么样子,只知道他穿了一件有可能是深蓝色的短大衣。”
“他连那人的大概身高也说不出吗?是高是矮?头发什么颜色?”
“事发突然,无法确定的事情巴克曼也不敢乱说。”
“关于那个袭击我的人,至少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维兰德说,“他奔跑的速度要比我快得多。我的印象是,此人中等个头儿,身体相当强健,身材绝对比我好。虽然有点模糊,但我感觉此人年龄和我相近。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
他们还需等待隆德法医的初步检测报告。尼尔伯格也正在和林雪平市[1]的技术实验室联系。他们还要搜索众多的资料库,对现场发现的大量指纹进行检验和比对。
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十分巨大,因此维兰德想尽早结束会议。最后大家起身离开会议室时,已经是11点钟。维兰德刚刚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电话便响了,是接待处的艾芭打来的。
“有人找你,”她说,“一个自称叫贡纳尔·拉尔森的人想和你谈谈兰伯格的事。”
维兰德刚刚决定再去找一次伊丽莎白·兰伯格,所以很不情愿打乱自己的行程安排。
“就不能让别人先接待一下吗?”他说。
“他指名要和你谈。”
“是什么人?”
“他以前为兰伯格工作。”
维兰德立刻改变了主意。看来与伊丽莎白·兰伯格的谈话只能推迟了。
“好吧,我这就去接他。”维兰德说着站了起来。
贡纳尔·拉尔森30多岁,他随着维兰德走进了办公室。维兰德问他要不要来杯咖啡,他谢绝了。
“我很高兴您能主动来警局反映情况,”维兰德说道,“虽然我们迟早会去找您,但您这样做为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
维兰德翻开一个笔记本,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我为兰伯格先生工作了6年,”贡纳尔·拉尔森说,“他是4年前辞掉我的,据我所知,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雇过其他人。”
“他为什么要辞掉您呢?”
“他说他雇不起人了。我觉得他说的是实情,而且我当时也早就料到了。兰伯格先生的生意并不大,一个人完全可以打理。他的照相馆里既不卖相机,也不卖配件,所以收入并不高。加上这些年经济不景气,去照相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您为他工作了6年,想必对他应该非常了解吧?”
“可以说了解,也可以说不了解。”
“那我们先从了解开始说起吧。”
“他从来都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对我,对每一个顾客,对所有人都是如此。他对孩子尤其有耐心。还有,他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
维兰德若有所思,不禁问道:“您是说西蒙·兰伯格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摄影师咯?”
“他这个人的头脑缺少新意,拍的照片都很传统,当然,那也正是人们想要的。所有的照片拍出来都是千篇一律,这一点他很擅长。他从来不会标新立异,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我想他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追求。至少我看不出一点苗头。”
维兰德点点头。
“这么说来,他只是一个和蔼可亲,但却没什么个性的人,是吗?”
“是。”
“说说您自认为对他不了解的地方吧。”
“他恐怕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内向的人了。”
“您指哪方面?”
“他从来不谈论自己,或他的感受。我从来没见他说过自己的任何事。不过最初的时候我也试过和他聊聊天。”
“聊些什么?”
“随便聊。但很快我就放弃了。”
“他从来不对时事发表看法吗?”
“我觉得他是个极端保守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贡纳尔·拉尔森耸了耸肩。
“就是感觉。不过换句话说,我怀疑他从来不看报纸。”
“这你可就大错特错了。”维兰德心里说。据他看来,兰伯格不仅常看报纸,而且他对国际新闻了如指掌。他的观点全都展示在那本相册里了,只不过世人无缘一睹其真容。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觉得很蹊跷,”贡纳尔·拉尔森继续说道,“在我为他工作的6年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妻子。当然,他也从来没有邀请我去过他的家。为了弄清他们住在哪儿,有个星期天我还特意从他们家门前经过。”
“这么说您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女儿咯?”
贡纳尔·拉尔森露出极为困惑的表情。他盯着维兰德,问道:“他们有孩子?”
“您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们有个女儿,名叫玛蒂尔达。”
维兰德并没有透露玛蒂尔达先天残疾的事。不过显而易见,贡纳尔·拉尔森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
维兰德放下钢笔。
“听到发生凶案的消息后,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您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谁会想要害他呢?”
“这也是我们正在全力调查的。”
维兰德注意到贡纳尔·拉尔森有些不自在。他似乎有话要说,但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您想到了什么,”维兰德猜测说,“对不对?”
“我听到过一些传言,”贡纳尔·拉尔森迟疑地说,“说西蒙·兰伯格曾经赌博。”
“哪种赌博?”
“赌钱那种,有人在耶格斯罗赛马场见过他。”
“偶尔去耶格斯罗赌一赌马也没什么奇怪的呀,怎么就会有传言了?”
“人们还说他经常出入马尔默和哥本哈根的一些非法赌场。”
维兰德皱起了眉头。
“您是从哪儿听到这些的?”
“像于斯塔德这样的小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
这倒是实情,维兰德深有体会。
“还有人说他负债累累。”贡纳尔·拉尔森接着说道。
“是真的吗?”
“至少在我为他工作期间并非如此。我能从他的账本上看出来。”
“但是,他可能向私人贷款,甚至借高利贷。”
“那我就不清楚了。”
维兰德想了想。继而问道:“传言总该有个源头的,您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些传言的?”
“很久以前了,”贡纳尔·拉尔森答道,“具体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记不清楚了。”
“您知道他锁在书桌里的那本相册吗?”
“他书桌里的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维兰德相信面前这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当年为兰伯格工作时,您有照相馆的钥匙吗?”
“有。”
“不在那里干之后,钥匙怎么处理了?”
“还给他了。”
维兰德点点头。看来从贡纳尔·拉尔森身上只能问出这些情况了。询问的人越多,西蒙·兰伯格就愈发显得神秘莫测。他记下了贡纳尔·拉尔森的地址和电话,再次感谢之后,又亲自把他送到接待区。然后他去倒了一杯咖啡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不希望被人打扰,索性摘下了电话听筒放到一旁。他已经想不起来曾几何时自己如此茫然若失过。他们接下来的调查该何去何从呢?每一条线索都不完整,各条线索之间又似乎毫无关联。尽管极力回避,但相册中他自己那张被扭曲的狰狞面孔,却总是反复不断地在眼前闪现。
想破脑袋,却仍然毫无头绪。
他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窗外狂风肆虐,呜呜作响。他把听筒放回机座。结果电话立刻便响了起来。是尼尔伯格,他说技术鉴定已经全部完成,但并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发现。现在,维兰德可以进入照相馆的其他房间查看了。
维兰德坐在椅子里,默想着发生的一切,并试着写个总结出来。他在头脑中与里德伯讨论起了案情。同事病得真不是时候,现在他该怎么办呢?调查该如何向前推进?他们掌握的情况少得可怜,调查陷入困境,举步维艰,就好像只是在原地转圈圈。
他看了一遍自己写的东西,想从中发掘出点秘密,但却一无所获。一怒之下,他把笔记本扔到了一边。
还差一刻钟便到1点,该去吃点东西了。下午他还要抽空去找伊丽莎白·兰伯格谈一谈。
他意识到自己太过急躁了,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但距离西蒙·兰伯格被杀害毕竟才刚刚过去一天。
里德伯必定会是同样的看法。维兰德自己也十分清楚,他缺乏足够的耐心。
他穿上外套,正准备出去。
这时门开了,是马丁森。从他的表情中,维兰德一看便知肯定有重要的情况报告。
马丁森站在门口,维兰德急切地望着他。
“昨天夜里袭击你的那个人我们始终没有抓到,”马丁森说,“但有人看见他了。”
说完他指着维兰德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幅于斯塔德地图。
“他是在奥林街与吉奥德胡同的拐角处把你打昏的。随后他极有可能是沿着海尔里斯塔茨街逃窜,然后又转向北。打昏你之后不久,有人在提默曼斯街上的一个花园附近看到了他。”
“是谁看到的?”
马丁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袖珍笔记本,翻开看了看。
“是一对姓西莫维奇的年轻夫妇。女的因为要照看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所以半夜的时候还醒着。她无意间向花园扫了一眼,正好看到一个人躲在阴暗处。于是她立即叫醒了丈夫,可当她丈夫也来到窗前时,外面早就已经没了人影。她丈夫说是她看花了眼,她想想也真有那个可能,所以便没有在意,哄睡了孩子之后,自己也睡了。只是到了今天,她来到花园里时忽然想起了这件事,便走到她看见人影的地方查看。哦,对了,我应该先说一声,她已经听说了兰伯格被谋杀的事。于斯塔德地方不大,就连西莫维奇夫妇也曾在兰伯格的照相馆里照过相。”
“不过她不可能知道我们夜里追捕疑犯的事啊,”维兰德疑惑地说,“那件事我们还没有公开。”
“对,”马丁森说,“所以我们才要感谢这位女士,她觉得蹊跷,便主动报告给了警方。”
“她看清那人的样貌了吗?”
“没有,她只看到一个人影而已。”
维兰德一时摸不着头脑,呆呆地望着马丁森。
“那看见又有什么用?”
“别急,”马丁森说,“虽然没看清人,但她捡到了一件东西,刚刚送到警局。现在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呢。”
维兰德立刻跟着马丁森去了他的办公室。
“是这个吗?这就是她捡到的东西?”
“一本赞美诗集,瑞典教会出的。”
维兰德思考着其中的关联。
“西莫维奇太太怎么会想到把这本书送到警局呢?”他问。
“大概因为她知道最近发生了谋杀案,而半夜三更看到有人在她家的花园里鬼鬼祟祟,难免会起疑心。起初她听信了丈夫的话,认为是自己看花了眼。可后来她便捡到了这本书。”马丁森说。
维兰德缓缓摇了摇头。
“这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他说。
“不过有大量线索可以证明这就是同一个人。在于斯塔德这样的地方,三更半夜什么人会在别人家的花园里鬼鬼祟祟呢?况且昨天夜里巡逻车一直在街上转,我同参加巡逻和搜捕疑犯的一个同事谈过,他们昨晚去过提默曼斯街好几次,因此那个花园应该是个非常理想的藏身之地。”
维兰德知道马丁森的话很有道理。
“赞美诗集,”他仿佛自言自语一般,“谁大半夜揣一本赞美诗集干什么?”
“刚刚袭击过一名探长,而后又把书掉在了别人家的花园里。”马丁森补充说。
“把书交给尼尔伯格处理,”维兰德说,“别忘了向西莫维奇家表示感谢。”
从马丁森办公室出来时,他忽然想到了别的事。
“谁负责收集和处理报案线索?”他问。
“汉森。不过目前看来仍毫无进展。”
“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什么进展。”维兰德不无忧虑地说。
维兰德走到汽车站旁边的甜品屋,买了几个三明治。那本赞美诗集和迄今为止发现的其他线索一样神秘,使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维兰德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他和同事们就像一群无头的苍蝇,在黑暗中胡乱地摸索着。
吃过午饭,维兰德开车去了拉温德尔路。为他开门的仍是卡琳·法尔曼。不过这次伊丽莎白·兰伯格并没有在休息。维兰德走进屋时,她正在客厅里坐着。她那苍白的脸色再次让维兰德感到吃惊。他感觉这种苍白是她内在气质的衍射,源于难以释怀的过往,而非仅仅是因为丈夫被谋杀。
维兰德在伊丽莎白对面坐下。她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案子至今仍然没有什么进展。”维兰德首先开口说道。
“我知道你们已经尽了力。”她说。
维兰德一时倒拿捏不准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了。是真心这么认为吗?还是在委婉地指责?
“这是我第二次来找您了,”他说,“不过我想这应该不会是最后一次。新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我会尽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这次我来不只是要问些问题,”维兰德继续说道,“我还需要查看一下您丈夫的遗物。”
伊丽莎白点点头,但并没有说什么。
维兰德决定不再绕弯子。
“您丈夫在外面有债务吗?”
“据我所知没有。房子的钱已经付清,他很少往照相馆里投钱,除非他确定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把贷款还清。”
“那他会不会背着您贷款呢?”
“当然有这种可能。我已经向您解释过,虽然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却是各过各的。况且他这个人总是神秘兮兮的。”
维兰德紧紧抓住她的最后一句话,问道:“您说的神秘兮兮是指哪些方面?能说得明白点吗?”
她直盯着维兰德的眼睛。
“所谓神秘兮兮,其实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极其封闭的人。我永远猜不透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否一致。有时候虽然他近在眼前,但感觉上却仿佛远在天涯。即使他微笑的时候,我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快乐。总之他就是让我摸不透。”
“和他相处一定让您大伤脑筋吧?”维兰德说,“但他应该不会一直都是这样吧?”
“不,他真正性情大变是从玛蒂尔达出生以后。”
“24年前?”
“并不是一下子就变了,应该说是20年前吧。起先我以为他只是因为忧伤,是为玛蒂尔达的命运感到悲痛。可是后来我就愈发不明白了,他的状态变得更糟了。”
“更糟?”
“大约7年前。”
“那时发生了什么事?”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维兰德顿了顿,说道:“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7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情?”
“对。”
“而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您一概不知?”
“也不完全是。每年春天,他都会让助手代他打理照相馆两周左右的时间。他自己则搭汽车到内陆去旅游。”
“您不和他一起去?”
“他想一个人去。况且我也没什么兴趣。如果我去旅行,会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而且去完全不同的地方。”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那一次他的目的地是奥地利。回来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看上去既欢欣鼓舞,又黯然神伤。我试过问他出了什么事,结果他就大发雷霆。我从来没有见他那样过。”
维兰德开始在本子上做些记录。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1981年,2月或3月。旅游巴士是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的,但西蒙是在马尔默上的车。”
“您还记得那家旅行社的名字吗?”
“好像是叫马克里梭旅行社。他每次都选这家旅行社。”
维兰德记下了这个名字,随后又把笔记本放回口袋。
“现在我需要查看一些东西,”他说,“尤其是他的房间。”
“他有两个房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
两个房间都位于地下室。维兰德只在他的卧室里粗略扫了一眼,便打开了衣柜。伊丽莎白静静地站在他身后,默默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看完卧室,他们又去了兰伯格宽敞的书房。书房里靠墙的地方全都摆放着书架。维兰德看到兰伯格收藏了不少唱片。除了书架,房间里还有一张已经用旧了的扶手椅和一张硕大的书桌。
维兰德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您丈夫信教吗?”他问。
“不,”她惊讶地回答,“从来没听说过他信教。”
维兰德的目光在书脊上游走着。架子上摆了许多各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主题各异的专业类书籍。仅天文学方面的书就排了好几列。维兰德在书桌前坐下。尼尔伯格已经把兰伯格的钥匙交给了他,此刻他掏出来,打开了第一个抽屉。这时伊丽莎白在扶手椅中坐了下来。
“如果您不想被打扰,我可以先回避的。”她说。
“不必了。”维兰德客气地说。
他用了两个小时才把书房查看了一遍。整个过程伊丽莎白都一声不吭地坐在扶手椅里,只是她的目光一刻不离地追随着维兰德。然而他并没有发现任何会给调查带来突破的线索。
7年前的奥地利之旅彻底改变了兰伯格,可问题是,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时间将近5点半,维兰德只好放弃。西蒙·兰伯格几乎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世界里,不管他如何努力,却始终连一丝缝隙都寻觅不到。他们又回到了一楼。卡琳·法尔曼旁若无人地干着自己的事。屋子里和初来到这里时一样,静悄悄的。
“找到您想要的东西了吗?”伊丽莎白·兰伯格问。
“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我只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点线索,让我们对凶手的作案动机,或者凶手本人有所认识,可惜我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东西。”
维兰德告了别,便驾车返回警局。凛冽的寒风并没有减弱一分,他冷得直哆嗦,心里也许已经是第一百次发出这样的疑问:该死的春天到底什么时候才来?
[1] 林雪平市位于瑞典南部,是瑞典第五大城市,也是瑞典的高科技和高等教育中心,有“大学城”之称。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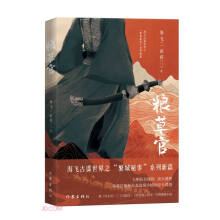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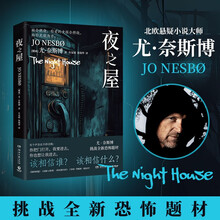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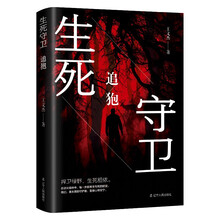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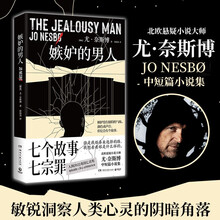
——《每日电讯报》
(曼凯尔)无疑是黑夜的主人。
——《犯罪时间》
一部精美的探案小说集。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