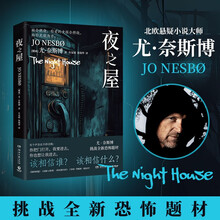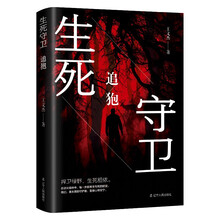福尔摩斯领着我走上台阶,并朝弓形窗的方向点了点头。“这将是我们的入口,”他低声说道,一边把提灯塞到我手里,“现在,我要用凿子去工作,你保持光束稳定。”
我的同伴像一个老练的盗贼那样,顺利地把凿子滑到了推拉窗的下缘。只见他弯下腰,迅速而沉着地动作着,随着一声闷响,窗户猛地打开了。
我们一刻也没耽搁地爬进了屋子,似雕像般在黑暗中站着,我们的感官对最微小的声音或动作保持着警觉,但我的耳边除了寂静的房子发出的嘶嘶声之外,什么也听不到。
过了一会儿,福尔摩斯凑近我,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棺材一定在一楼的某个房间里,有可能是在晨间起居室,跟我来。”他抓着我的衣袖,轻轻地拉着我穿过黑暗,走向门口。他有一种精心培养的非凡能力,那就是在黑暗中看东西。在提灯发出的微光的帮助下,他可以像猫一样轻松自如地找到方向。几秒钟之内,我们就站在了门厅的走廊上。前门上方那苍白的光线滤过气窗,在墙壁上投下了斑驳移动的阴影。立在大厅尽头的落地式大摆钟发出柔和的滴答声,打破了寂静。福尔摩斯晃动着黑色提灯发出的一束微光,试图探索周围的环境。一个装饰华美的镜子下面是大厅的桌子,桌上放着一大盆雪白的兰花,在黑暗中发出幽灵般的冷光,这无疑是在向死者致敬。
走廊通向好几个门,我们尝试打开了其中两个门,并站在门槛透过苍白的光线看房间内部。一间是音乐室,一间是起居室。在第三次尝试时,我们来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房间,称其为晨间起居室真是极不恰当。即使提灯的光束非常微弱,我也能看出这个房间平时是阴沉的。窗帘是镶着金边的黑色天鹅绒面料,壁纸也是诡异和沉闷的,它以一组奇怪的图案为主体,几乎全是雕版印画,描绘出一系列龇牙咧嘴、令人厌恶的面孔,很像魔鬼和石像鬼。熏香发出一种病态的甜味,令人想起东方。那发腻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浓烈得几乎令人窒息。华丽的地毯和家具都是深浅不一的灰色、黑色或暗棕色。壁炉上方悬挂的是房子主人的肖像。这幅油画是高贵的哥特式风格,只见塞巴斯蒂安·梅莫斯站在月光下,背景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城堡雉堞。他苍白的脸带着鬼怪般的敌意怒视着我们,就像这幅画变活了,他知道我们要侵入他的私人宅邸似的。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当光束掠过他的脸,竟看到他的眼里燃着恨意。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幽灵。
然而,所有这些观察只用了几秒钟,这个宅子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搁在房间中央的深色橡木棺材。
福尔摩斯把提灯的光束晃到棺材盖上,照亮了一个小小的银盘,上面刻着:塞巴斯蒂安·梅莫斯1866-1839。
我的朋友厌恶地哼了一声:“来吧华生,帮我打开盖子。”
“但你肯定要这样做吗?福尔摩斯……”
“这是我们来访的理由。一个封闭的棺材并无证据,它很可能是空的。”
棺材里不是空的。尽管我在阿富汗的那些年目睹了所有关于流血和恐怖的伤害,但是当棺材盖被打开时,眼前的那一幕还是使我忍不住作呕。后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是那种不协调感震惊了我的感官。虽然被告知梅莫斯是在猎杀事故中被打死的,我还是没准备好面对如此可怕的伤口。残缺不全的尸体躺在棺材中,伤口一目了然。他胸膛的上半部分已经没了,他的脸几乎不能称之为脸—只是一些血淋淋的暗红色组织,在光线下闪闪发光。甚至连他头上金色的发髻也被剃光了,这使他的外观更加恐怖。
福尔摩斯根本没有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具幽灵般的尸体感到吃惊。事实上,他满意地念叨道:“打猎意外事故,不是吗?至少需要两颗子弹才能创造这个效果。真是做得非常漂亮,华生,尸体的确处理得很好。”说完这句话,他俯身仔细地检查死者的双手,然后又用提灯照了照曾经是脸的部位,仔细检查从肉里突出的那颗牙齿。
“我很确信这个家伙是谁,他肯定不是塞巴斯蒂安·梅莫斯。”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这里的证据证明了我的怀疑。看看这双手……”他把尸体的一只手举起来,用提灯在上面照了照,“观察一下上面的茧子,指甲里有根深蒂固的污垢,这绝不是唯美主义者和花花公子的手,而是劳动者的手。”放下手臂,他又俯身面向尸体,在尸体嘴周围取了一些撕成碎片的肉,“同样,他的牙齿并没有受益于富人才支付得起的昂贵护理,那些棕色和黑色的残牙表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对牙齿的忽视。我的朋友,这个穷光蛋只是一个替身、一个假象,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塞巴斯蒂安·梅莫斯还非常活跃地活着。”
“但是这种欺骗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也许是我自以为是,但我相信这主要是做给我看的,是为了让我失去这条线索。如果主要嫌疑人已经死了,那么侦探不得不去别处寻找另一个嫌疑人……”
“同时,他可以不受惩罚地执行那邪恶的计划。”
“没错。”
“但棺材里的这个可怜虫是谁?”
我注定得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正当福尔摩斯要开口回答时,从房子的上部传来了噪音。我的心一沉,有人听到了我们的说话声。
福尔摩斯立即熄灭了提灯,“快点,”他严厉地低声说道,“帮我关上棺材盖。”
我们俩像瞎子一样全力对付棺材盖,在与世隔绝的黑暗中把它放回原位。一完成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我就听到了楼下传来的脚步声。我几乎愣住了,但福尔摩斯拖着我来到窗旁,并把我拉到沉重的黑色窗帘背后。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房间里已经亮起了电灯的光源。
有人进来了。从那沉重的脚步声和冗长的步幅来看,我觉得这是个男人。我听到他走到棺材旁,还扣动了手枪的扳机。他均匀的步伐越来越近,我能感觉到他在朝我们的藏身之处走近。福尔摩斯把他的手指放到了嘴唇上。
此时,窗帘动了一下,仿佛有一只手放在了它上面—一只随时可能揭露我们的手。我的嘴里突然变得很干燥,心也怦怦直跳。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