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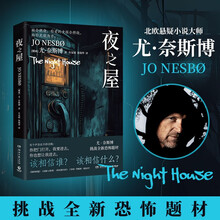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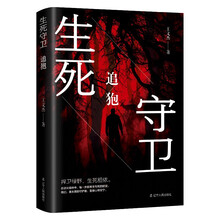




在一个寒冷的一月清晨,侦探沃兰德接到报案,来到于斯塔德的一个偏远农场。推开小屋大门,三位警察面面相觑——虽然经历过许多大场面,但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惨不忍睹的现场:
一对老夫妇的卧房浸在一片血泊之中,鲜血甚至溅到天花板的瓷质吊灯上。老头的脸被划毁得无从辨认,看起来好像是有人想要割下他的鼻子。他妻子在他身边,饱受殴打,濒临死亡。
这对与世无争的老夫妇究竟为何遭到虐杀,沃兰德开始了困难重重的追查……
他忘记了什么事。醒来之后,他确信是自己忘记了。那是缠扰深夜的梦魇,是本属于他的记忆。他竭力想唤回它们,怎奈睡梦像一个黑洞、一口深井,空空如也,无迹可寻。
他想,至少我不曾梦到过公牛。不然,我会像发了一夜烧那样,浑身燥热,虚汗连连。这一回公牛没有来招惹我。
他仍旧躺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周围的动静。身旁妻子的呼吸声细若游丝,几乎听不见。他想,会有那么一个早晨,她死在我身边,而我却毫不知情。抑或死去的是我,无声无息。黎明时才能知晓,我们俩之中有一人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他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闹钟,泛着幽光的指针显示,现在是早上四点四十五分。
我为什么会醒来呢?他问自己。我通常要睡到五点半才醒,四十多年来一直如此。我为什么现在醒来呢?他在黑暗中倾听着,突然彻底清醒了。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情况变得有些反常。他伸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摸索,最后摸到了妻子的脸。他可以用指尖感觉出她的温热。这么说来,她还没死。他们俩都还没有落单。他转而倾听黑暗中的声响。
他想,是那匹母马,它没有嘶叫,怪不得我会醒来。那匹母马通常会在夜里大声嘶叫。我不用醒来就能听到,潜意识会告诉我可以继续睡。他蹑手蹑脚地离开吱吱作响的床。四十年来,他们一直睡在那张床上。那是他们结婚时买的唯一一件家具,也是他们俩睡过的唯一一张床。当他踩着木地板走向窗户的时候,左膝疼了起来。
我老了,他想,已经年老体衰了。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会感到诧异——我七十岁了。他透过窗户在冬夜里张望着。今天是一九九○年一月七日,入冬以来的斯科纳①[1]还没有下过雪。厨房门外的灯发出一道穿过院子的光,钻进那棵光秃秃的栗子树的枝丫,投向远处的田野。他眯着眼睛望向邻居拉夫格伦夫妇的农场。那儿有一间长方形的屋子,屋脊低矮,雪白的墙安静地沉浸在黑暗中。农舍一角的马厩里,漆黑的大门上氤氲着淡黄色的光。那儿就是那匹母马的隔栏,就是它被惹得躁郁嘶叫的地方。他在黑暗中倾听。身后传来床板的咯吱声。
“你在干什么?”妻子咕哝着。
“接着睡吧,”他答道,“我只是伸伸腿而已。”
“膝盖又疼了?”
“没有。”
“那就回来睡吧。别站在那儿挨冻,容易感冒。”
他听见她翻了个身,转向另一侧。他想,我们曾经相爱过。但是他不愿接受这种想法。爱——这个词太过崇高了,并不属于我们这种人。一个当了四十多年农民、终日在斯科纳的厚黏土上躬身耕作的人,在谈到妻子时,是不用“爱”这个字眼的。在我们的生活中,“爱”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眯起眼睛窥视着邻居的房子,试图看穿冬夜的黑暗。嘶叫呀,他在心里念道。在你的隔栏里嘶叫,好让我知道一切如常。这样我就可以躺回被窝再睡一会儿。对一个早已退休、腿脚不便的农民来说,日子总是这样漫长而沉闷。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盯着邻居家厨房的窗户看。这些年来,他时不时地会看一眼邻居家的窗。现在情况似乎不太对劲,还是天太黑把他给弄糊涂了?他眨了眨眼,数到二十后就让眼睛歇一歇,然后再次看向那扇窗。现在他确定窗户是开着的。一扇在夜里总是闭着的窗户现在却是开着的,而且那匹母马压根就没有嘶叫。
母马没有嘶叫,大概是因为夜里拉夫格伦先生没有像平时那样走到马厩去。往常他总是因为前列腺病发而钻出暖和的被窝。
我不过是在异想天开罢了,他自言自语。我的眼睛都花了。周围的一切还和往常一样。毕竟,这儿能出什么事呢?伦纳普村就坐落在凯德湖的北面,是去往风景优美的克拉格霍尔姆湖的必经之路,更位于斯科纳的心脏位置,能出什么事呢?多年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时间在这个村庄里静止了,生活像一条无精打采的小溪,漫无目的地流淌着。只有几个靠出售或租赁土地为生的老农民居住在这里。我们住在这儿,等待生命那不可避免的终结。
他再次看向厨房的那扇窗,心想无论是玛丽亚还是约翰尼斯·;拉夫格伦都不会忘了关上它的。人一旦上了年纪,恐惧感便随之而来;家里的锁越安越多,任谁也不会忘了要在天黑之前关好窗户。人一变老便意味着活在恐惧之中。小时候恐惧的事物在年老时会再度来袭。
他想,是时候穿上衣服,出去看看了。我可以跛着脚穿过院子,任凛冽的寒风从脸颊旁呼啸而过,慢慢走到分隔两家的篱笆边上。现在我可以近距离地看看,到底是不是我在异想天开。
然而他没有动。约翰尼斯很快就会起床泡咖啡了。首先他会打开浴室的灯,然后是厨房的灯。一切都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
他站在窗边,觉得自己快要冻僵了。他想到了玛丽亚和约翰尼斯。作为邻居和农友,他想,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也像婚姻一样。多年来,我们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世事艰辛、荒年不济。当然我们也一同享受过那些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庆祝仲夏,共享圣诞晚餐。我们的孩子在两家农场间跑来跑去,仿佛两边都是他们的家。如今,我们将共同度过漫长的晚年。
不知为什么,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生怕弄醒了汉娜。他紧紧抓住窗闩,不让强风从他手里把窗户吹开。但是夜出奇的静寂,他回忆着电台的天气预报,并没有说有风暴将席卷斯科纳平原。
缀满繁星的夜空明净如洗,时刻涌动着冬的寒意。他正准备关上窗户,忽然听见一个声响。他转过脸去,用左耳对着打开的窗户聆听。他的左耳是正常的,右耳因为长期禁锢在既不通气又嘈杂的拖拉机里而听力受损。
他想,是鸟的叫声,是一只夜鸟在啼叫。他突然感到害怕。一种没有来由的恐惧令他惊恐万状。那声音好像是有人在喊叫,在绝望地喊叫,竭尽全力让别人听见。喊叫的人知道,只有让这喊叫声穿透厚实的石墙才能引起邻居的注意。
一定是我在胡思乱想,他想。没有人在喊叫。谁会这么做呢?他用力地关上窗户,震得花盆都弹了起来,汉娜也被吵醒了。
“你在干什么?”她问。他听得出来,她生气了。
就在他要回答的时候,他突然确信刚刚发生过的恐怖事情是真的。
“那匹母马没有嘶叫,”他坐在床沿说,“拉夫格伦家厨房的窗户敞开着,我听见有人在喊。”
汉娜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说什么?”
他不想回答,但是此刻他确定刚才听见的不是鸟叫声。
“是约翰尼斯或者玛丽亚,”他说,“他们俩中的一个人正在呼喊救命。”
汉娜下了床,走向窗户。她穿着白色的睡袍,站在又大又宽的窗前向黑漆漆的窗外探出头。
“那扇厨房的窗户不是敞开的,”她低声说,“它是被打破的。”
他走到她身边,此刻他冻得直打哆嗦。
“有人在喊救命。”她说,声音中带着些颤抖。
“我们该怎么办?”
“先去那边看看,”她说,“快点儿!”
“但要是有危险呢?”
“难道我们不该去救我们最好的朋友吗?”
他急忙穿上衣服,从厨房的壁橱里拿出放在软木塞和咖啡罐边上的手电筒。屋外,脚下的土地冻成了结实的一片。转身之际,他瞥见汉娜正站在窗户后面。走到篱笆边上之后,他停住了。万籁俱寂,现在他可以看清,厨房的窗户确实是被打破的。他小心翼翼地翻过低矮的篱笆,走向白色的房子。然而喊叫声却无处可寻。
一定是我在胡思乱想,他想。我上了年纪,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昨晚我确实梦见过那只公牛。从小时候起,梦里的公牛就一直追着我不放,让我意识到有朝一日我会死去。
不一会儿,他听见了哭喊声。声音很微弱,更像是在呻吟。是玛丽亚。他走到卧室的窗户旁,透过窗帘和窗框之间的缝隙小心谨慎地往里窥探。
突然间,他知道约翰尼斯死了。他拿着手电筒照进去,用力地眨了眨眼,才硬着头皮朝里看。玛丽亚在地上蜷曲着,整个人还被绑在椅子上。她满脸是血,碎裂的假牙散落在血污飞溅的睡衣上。他只能看见约翰尼斯的一只脚,身体的其他部分被窗帘挡住了。
他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又一次翻过篱笆。当他踩着冻黏土一路踉跄赶回时,膝盖隐隐作痛。他先报了警,然后从充斥着樟脑丸气味的壁橱里拿出一根铁制撬棍。
“在这儿等着,”他嘱咐汉娜,“你不用去看。”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眼里噙着惶恐的泪水。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醒过来是因为那匹母马夜里没有嘶叫。这一点我非常确定。”
今天是一九九○年一月七日。天还没有亮。
……
我们生活在一个绳套的时代,人们的恐惧将不断加深。
——亨宁·曼凯尔
一部精致的小说,具有催眠术般的魔力,笔触细腻,极具诗意,悬念与深度兼备。
——《洛杉矶时报》
从侦探沃兰德身上,我们看到了马丁·贝克的影子,亨宁·曼凯尔不愧是马伊·舍瓦尔和佩尔·瓦勒夫妇的接班人,而他所呈现的是一个更加现代的瑞典。
——亚马逊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