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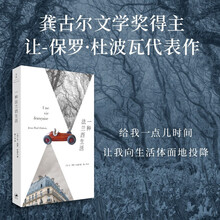




火辣辣的阳光笼罩着整座小城,几乎无情吞噬了所有建筑和树木投下的阴影。中午时分,我们驾驶一辆美国产棕色――也有人称之为巧克力色――雪佛兰越野车,终于驶入小城。我们伸长脖子向外张望,想确认一切是否还保持原样,就像去年夏天和过去许多年一样。 越野车缓缓前行。高大挺拔的白杨树矗立在街道两旁。这条林荫大道便是小城的入口。我从未告诉任何人,这些参天大树令我头晕目眩,并联想起马泰奥。(我曾在马泰奥身旁体验到这样的眩晕,当时我们俩在村外最美丽的一片林中空地上拥抱着原地转圈。我们的额头亲密地挨在一块儿,随后我感到从马泰奥的舌尖传递来的奇特的清凉感,他的体毛柔软黑亮,倒伏在皮肤表面,仿佛彻底臣服于身体的美丽。) 甜蜜的回忆一时令我走了神。我们的越野车仿佛一艘巧克力色的小船,无声地在白杨树间从一株划向另一株。透过树木间隙,我能看见酷热阳光照射下笼罩着平原的静若止水的空气。爸爸朝空调出气口侧过脸说:“什么都没变。”接着又稍稍压低嗓音说:“一切都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我暗想,或许爸爸打算向野蛮展示文明的力量,召集一伙园丁,把横七竖八的枝权修剪整齐,或者干脆用电锯把小城入口处的白杨树通通砍倒,一劳永逸!(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坐在某棵被砍倒的树干上,远眺中午骄阳下火热的平原,而爸爸也会登上一棵树干,原地打个转,然后不无苦涩地说:“这些该死的、覆满灰尘的树终于被解决掉了。”他的话有道理,只是大家要很久以后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空气在树木间飘荡,让人感觉充满希望。没人知晓这些白杨树在我心中的意义,我多么想停下脚步,身体倚靠在某棵树干上,仰起头,用目光追随树叶微小而轻快的摇曳。像过去一样,这次我同样没有请求爸爸停车,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的询问,因为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费好多口舌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偏偏在快到家门口的时候要求停车,而且一定无法回避我和马泰奥的事。 我们的车开得非常稳,仿佛被一股神秘力量牵引着前行,几乎感觉不到道路的起伏颠簸。最终抵达目的地之前,我们再度经历一番文明与野蛮的对峙,再次目睹时光静止不前,再次听到爸爸嘴里发出“什么都没变”的声音。我们两个孩子将脸紧贴在出奇冰凉的左侧车窗上,难以置信地望着那些生活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中间的人们。爸爸说:“什么都没有变。”瓦楞铁皮搭的小屋、废旧轮胎、头发乱蓬蓬的孩子们在轿车残骸和生活垃圾之间玩耍,仿佛这就是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不禁在心里想,当夜幕降临大地,黑暗笼罩一切时,当面前所有这些横七竖八堆在地上的垃圾变成有生命的精灵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瞬间,我忘掉白杨树林荫道、马泰奥、雪佛兰越野车和马达的轰鸣声,平原上的黑夜仿佛在施展可怕的魔力将我紧紧裹住。我的耳朵听不见吉卜赛人美妙的歌声,眼中只剩下几个被昏暗路灯驱逐到路边的幽暗身影。 爸爸侧眼向车窗外瞥了一下,摇摇头,嗓子里冒出一声干咳。他把车速减到最低,几乎让人误以为几秒钟后车子就会停下来。“你们瞧瞧这里的样子。”他边说边用食指敲打侧窗。映人我眼帘的是一张张肮脏而僵硬的面孔、尖利的目光、破衣烂衫以及投映在一堆堆垃圾山上飘曳的灯光。我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景象,仿佛竭力想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眼前这群人,没有席梦思床垫,更不用说床,也许夜里他们会在地上挖个坑睡进去。大地呈现深黑色,夏天上面遮盖有大片向日葵,而冬天则裸露出来,任凭阴郁的天空肆意挤压,让人不禁产生一丝恻隐之心。倘若天空还给大地片刻安宁,那它就会像大海一般平静,波澜不惊。 我从未告诉别人,自己打心眼里热爱这片土地,尽管它荒芜贫瘠,不能予人丰厚馈赠。独自一人伸开手脚躺在大地上,我会感到踏实,那是大地给予我的保护。 ……
总序 静水深流(译序) 铁托之夏 科奇斯一家 边检警察和杨柳树 如此单词 美妙之极 不同的世界 入籍瑞士 七月 达利伯尔 我们 出事了 奶奶和爷爷 爱情、大海、河流 举着的双手! 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