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来自宇宙的消息到达地球已经快十年了。每隔30小时又51分钟,人类就会收到一页新的数据--估计在发送者的家乡,这就是一天的长度。到今天为止,一共是2841条消息。
对这些消息,地球还没有回复过。1989年,国际天文学会通过了《关于发现地外智能后的活动原则宣言》。宣言称:“对于收到的地外信号及其它能证明地外智能存在之证据,任何人不得发送任何回复,直到召开相应的国际会议为止。”联合国的一百五十七个成员国认可了该宣言。至今,人类仍在沉默地倾听着。
信号的来源没有疑问:赤经14度39分36秒、赤纬负60度50分。计算视差可知:对方和地球相隔1.34个秒差距。发出信号的外星生物所在的行星,围绕着人马座阿尔法星A转动――那是离太阳最近的亮星。
最先收到的十一页数据被轻易破解:那是数学和物理定律的简单图示,还有两种物质的方程式,貌似无毒。
收到的信息对所有人公开,然而接下来破译出的图像,全世界无人能解。
1
希瑟·戴维斯喝了一小口咖啡,看了看壁炉上方的黄铜挂钟。她十九岁的女儿瑞贝卡说晚上8点到,现在已经8点20了。
贝姬[ 瑞贝卡的昵称――译注]肯定知道这有多尴尬。她说自己想和父母见个面――父母两个、同时出席。希瑟·戴维斯和凯尔·格雷夫斯分居已近一年了,但这不是问题,他们可以在餐馆见面;但希瑟说“不”,她提议在自家碰头――就是她和凯尔把贝姬和她姐姐玛丽养大的那个家、就是凯尔在去年八月搬出去的那个家。但此时此刻,横在她和凯尔之间的沉默又持续了一分钟,希瑟开始后悔答应这个提议了。
希瑟已经有差不多四个月没见贝姬了,但是对贝姬要说的话,她心里有数。在电话里,贝姬常常提到她的男朋友扎克。她今天肯定是来宣布订婚的。
希瑟当然希望女儿可以再等几年。但看贝姬的样子,也不像是要去念大学,她在斯帕迪纳的一家服装店上班。希瑟和凯尔都在多伦多大学教书,希瑟在心理系,凯尔在计算机系。贝姬不想接受高等教育,这让夫妇俩感到伤心。根据教工联合会协议,多伦多大学对他们的孩子是免收学费的;至少玛丽就享受过一年的优惠政策……
不。
不要再想了。现在该是庆祝的时候。贝姬就要结婚了!这才是今天的大事。
扎克是怎么求婚的?她想知道。或者是贝姬先提出的?希瑟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凯尔当年求婚时说过的话,那是1996年,21年前。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说:“我爱你,我要用一辈子来了解你。”
现在,希瑟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上面铺着厚厚的垫子;凯尔坐在长沙发上,随身带着他的数据板,正在上面读着什么东西。凭希瑟对凯尔的了解,那大概是部间谍小说;对他而言,伊朗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好处,就是间谍惊险小说的复兴。
在凯尔身后,米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带框的影印照片。那是希瑟的东西,它由黑白两色的方块组成随机图案,代表外星人传来的一条消息。
贝姬是在九个月前搬出去的,那时她刚念完中学不久。希瑟曾经希望贝姬能在家里多住一阵――玛丽和凯尔都已离开,除她之外,这幢空荡荡的郊区大房子里就只有贝姬了。
刚开始,贝姬还经常回家;据凯尔说,她也经常去看望他这个父亲。但是后来,她回家的间隔就越来越长,到最后干脆不回来了。
凯尔似乎觉察到希瑟在看他。他从数据板上抬起视线,挤出了一丝微笑:“别担心,亲爱的,她肯定会来的。”
亲爱的。他们已经有十一个月没像夫妻那样住在一起了,但二十年的时光里培养出来的亲昵不会轻易消失。
终于,八点半刚过,门铃响了起来。希瑟和凯尔对望了几眼。贝姬的拇指指纹到现在还能开锁,凯尔的当然也能。那么晚了,不会有人串门,肯定是贝姬。希瑟叹了口气。贝姬没有自己进门,这加重了她的忧惧:女儿已经不把这座房子当成自己的家了。
希瑟起身,穿过起居室。她穿着连衣裙,这不是她平常在家的装束,她这是想让贝姬知道:她的来访意义特殊。经过前厅的镜子时,希瑟瞥见了自己裙子上的蓝花图案,她意识到,自己把女儿当成了必须端着架子接待的客人;就和女儿的态度一样。
她走到门前,用手摸了摸黑色的头发,确保发型没有乱,然后才转动门把。
台阶上站着贝姬:瓜子脸,高高的颧骨,褐色的眼珠,黑色的头发披在肩上。旁边站着的是她男友扎克,四肢瘦长,一头散乱的金发。
“你好啊,宝贝,”希瑟对女儿打招呼。然后,她微笑着对那个陌生的年轻男人说:“你好,扎克。”
贝姬径直走进了大门。希瑟原以为女儿会多站一会、吻她一下,可是她没有。扎克也跟着走进客厅。三个人接着来到了起居室,凯尔仍然坐在长沙发上。
“嗨,小南瓜。”凯尔抬头跟他们打招呼,“嗨,扎克。”
但女儿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她牵住了扎克的手,两人的手指缠绕了在一起。
希瑟坐在了安乐椅上,并示意贝姬和扎克也坐下。凯尔身下的长沙发上容不下他们两个。贝姬另外找了张椅子坐下,扎克站在她的身后,一只手放在她左肩上。
希瑟说了句“见到你真好,宝贝”。她还想说些什么,但意识到接下来就会说些“这么久没见”之类的话,于是在话出口前就把嘴闭上了。
贝姬回头看着扎克,她的下嘴唇在颤抖。
“怎么了,宝贝?”希瑟感到吃惊:如果女儿不是要宣布订婚,那她要说什么?难道她病了?和警察有麻烦了?她看见凯尔稍微欠了欠身,他也觉察到了女儿的焦虑。
“告诉他们。”扎克对贝姬说。他的声音很轻,但房里很安静,希瑟听见了。
贝姬又沉默了一会。她闭起了眼睛,又睁开,然后用颤抖的声音问道:“为什么?”
“宝贝,什么为什么?”希瑟问她。
“不是问你。”贝姬说,她的目光在父亲身上停留了一会儿,接着又望向地面,“是他!”
“什么为什么?”凯尔也问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和希瑟一样困惑。
壁炉上方的钟响了起来;它每过一刻钟就响一次。
“为什么……”贝姬再次抬头望向父亲,“你为什么……”
“说出来。”扎克小声而用力地催促。
贝姬咽了口唾沫,接着脱口而出:“你为什么要侵犯我?”
凯尔重重地靠到了长沙发的靠背上。原本放在扶手上的数据板也“当啷”一声掉在了硬木地板上。他望着妻子,张口结舌。
希瑟的心脏“怦怦”乱跳。她感到一阵恶心。
凯尔闭上了嘴,又张开:“小南瓜,我可没有……”
“你别不承认!”贝姬喝道,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谴责已经说出,如同洪水溃堤,“你别想抵赖!”
“可是,小南瓜……”
“还有别这这么叫我,我叫瑞贝卡。”
凯尔摊开了双臂:“抱歉,瑞贝卡,我不知道你不喜欢这个称呼。”
“该死的!”瑞贝卡说,“你怎么能那么对我?”
“我从来没有……”
“别撒谎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做了至少要敢承认吧。”
“可是我从来没有……瑞贝卡,你是我女儿啊,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
“你有过!你毁了我!我,还有玛丽。”
希瑟站起身来,“贝姬……”
“还有你!”贝姬叫嚷着,“你明明知道他对我们做了什么,但你却袖手旁观。”
“别对你母亲嚷嚷!”凯尔厉声说道,“贝姬,我从来没有碰过你或是玛丽,你是知道的。”
就在这时,一边的扎克第一次用正常音量说起了话:“我就知道他会否认。”
凯尔对这年轻人吼道:“混蛋!这里没你的事!”
“别对他这么大声!”贝姬对凯尔说。
凯尔努力保持着镇静。“这是我们的家事,”他说,“不需要他来掺和。”
希瑟看了看丈夫,又看了看女儿,她努力控制住声音,对女儿说,“我向你发誓……”
“你也别抵赖。”贝姬说。
希瑟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告诉我,”她说,“告诉我,你认为发生了什么?”
贝姬沉默了很久,似乎是在整理思绪。最后,她终于开口,语气中带着谴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半夜溜出你们的房间,溜进我或者玛丽的房间里。”
“贝姬!”凯尔插嘴,“我从来就没……”
贝姬看了看母亲,然后闭上眼睛:“他走进我的房间,叫我脱掉上衣,抚……摸我的乳房,然后,他……”她哽咽了,眼睛再次睁开,看着希瑟,“你肯定是知道的。你肯定看到他走开,也看到他回来。”她吸了口气,声音颤抖,“你肯定闻到了他身上的汗味,闻到他身上我的味道。”
希瑟摇着头:“贝姬,求你别说了。”
“根本就没那回事!”凯尔说。
这时扎克又插了进来:“他要抵赖的话,我们再待下去也没意义。”
贝姬点了点头,从提包里掏出一张纸巾,擦了擦眼睛。然后她站起身来,往外就走。扎克跟在她后面,希瑟也跟了上去。凯尔也站了起来。但贝姬和扎克很快走下楼梯,到了前门。
“小南……贝姬,得了!”凯尔追上去说,“我从来就没伤害过你。”
贝姬转过身来,她的眼睛布满血丝,她的脸颊涨红了。她说:“我恨你。”说完,她就和扎克快步走出大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凯尔望向希瑟:“希瑟,我发誓,我从来没碰过她。”
希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回到起居室,抓着楼梯的扶手保持平衡。凯尔跟着走了进来。希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凯尔走到酒柜旁,给自己倒了点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把身体靠到了墙上。
“是她的那个男朋友搞的鬼。”他说,“是他鼓动她干的。他们会打官司的,肯定会,他们是等不及了要抢遗产。”
“凯尔,求求你别这么说,”希瑟央求道,“那可是你的女儿啊。”
“我还是她父亲呢!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希瑟,你是知道的。”
希瑟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希瑟,”凯尔的声音里带了一丝恳求,“你肯定知道,那都不是真的。”
瑞贝卡离家几乎一年了,那肯定是为了某些事。而在那之前,还发生过某些事……
她讨厌这个念头,但每天都忍不住要想。
每个小时都要……
玛丽又是为什么自杀的……
“希瑟!”
“抱歉。”她咽了口唾沫,稍停片刻,又点了点头,“抱歉,我知道你不会做那种事的。”但她的声音实在呆板,连她自己都听出来了。
“我当然不会。”
“只是……”
“只是什么?”凯尔大声质问。
“没有,没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嗯,你确实有起夜的习惯、确实在半夜里走出房间。”
“你竟然这么说,”凯尔说道,“你竟然他妈的这么说……”
“你的确是那样的,有时候一周要起两三晚。”
“我睡眠不好啊――这你知道的。我起床是为了去看会儿电视、或许在电脑上做点工作。老天!我到现在一个人住了还是这样,我昨晚就起床了。”
希瑟一言不发。
“我睡不着觉。如果躺下后一个小时还没睡着,我就起床――这个你是知道的。在那儿傻躺着有什么破意思?昨晚我就起床看了――妈的,看了什么来着?看了三台放的《六百万美元先生》[六百万美元先生,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美国电视剧――译注],就是威廉·夏纳能和海豚交流的那一集。你打给电视台,他们会告诉你播的就是那一集。然后我发了几封电邮给杰克·蒙哥马利。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我的公寓――现在就去――去检查我的发件箱,你可以去查看邮件上的发送时间。发完了邮件我就回到床上躺下,大概一点二十五分、一点半的样子。”
“没人说你昨晚干了坏事。”
“可是我每晚起床都做这些事,有时候看看《六百万美元先生》,有时候看看《约翰·佩拉秀》,有时候还看气象频道、了解第二天的天气。说是今天会下雨,但是没下。”
哦,今天下了,希瑟心说,还是该死的倾盆大雨。
2
多伦多大学自诩是“北方哈佛”,1827年建校,大约有五万名全日制学生在这里注册。主校区位于市中心,毫无悬念地坐落在大学道和学院街之间。虽然按传统的说法有个中心校区,但事实上各个学院散布在城市各处,在圣乔治街和其它几条道路两侧,就胡乱分布着一批十九、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建筑。
大学最显眼的地标是罗巴斯图书馆,那是一座巨大而复杂的水泥建筑,学生们常管它叫“书堡”。凯尔·格雷夫斯在四十五年的人生里一直住在多伦多,但是直到最近才看到图书馆的整体模型,他觉得它的造型就像是一只水泥孔雀,其中的托马斯·费什珍本藏书楼就是孔雀头,长喙,长颈,直插天空;其余的楼房则组成巨大的两翼,在头部后方展开。
可惜的是,校园里没有地方可以居高俯瞰、欣赏图书馆的巧妙设计。多伦多大学有三所神学院,它们分别是加拿大联合教会属下的伊曼努尔神学院、长老派属下的诺客斯神学院、以及圣公会属下的怀克里夫神学院。或许,这只孔雀就是造给上帝和天外来客看的,有点像是加拿大版的纳斯卡地画。
玛丽自杀后不久,凯尔和希瑟就分居了。两个人都觉得难以承受,无法理解这件事的起因,挫败感从四面八方倾泻而来。凯尔现在住的公寓位于多伦多郊外,步行到唐斯维尤地铁站只有一小段路程。这天早晨,他坐地铁到圣乔治站下车,现在正走在圣乔治街91号的丹尼斯·穆林堂[ 多伦多大学里有些建筑以人名来命名,格式为“XXX堂”,类似国内的“逸夫楼”(编者注)]南面的一小段路上,就在罗巴斯图书馆的正对面。
他经过了巴塔鞋类博物馆――那是是世界上最大的鞋子博物馆,外形就像个稍稍压扁的鞋盒,是二十世纪建筑史上的又一个奇迹;有一天他还真的进去过。远处可以望见安大略湖畔的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它已经不是世界上最高的独立式建筑,但依然是最优雅的独立式建筑之一。
大约两分钟后,凯尔到了穆林堂,这是一幢新造的环形建筑,高四层,里面是人工智能和高级计算科学系。凯尔从正面的玻璃自动门走了进去。他的实验室在三楼,但他没有等电梯,而是直接从楼梯走了上去。四年前的那次心脏病发作之后,他就尽可能做一些小的锻炼。还记得以前爬两步就呼呼直喘,但现在他不怎么喘气就到了四楼。沿着走廊和左边的中庭他走到了自己的实验室,然后把大拇指压在扫描盘上,门开了。
“早安,格雷夫斯博士。”一个粗犷的男声迎接他进门。
“早安,猎豹。”
“我给你说个新笑话,博士。”
凯尔脱下帽子,挂到了那只旧木头衣架上――大学里从来不扔旧东西,那衣架想必50年代就在了。他打开咖啡机,然后在电脑控制台前坐下;控制台前部的控制面板呈45度倾斜, 面板中间有两个小小的镜头,它们对着目标跟踪摄影,仿佛一对眼睛。
机械眼下方有一个罩着格子的扬声器,猎豹的声音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是这样的:有一个法国物理学家,在CERN工作,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个新理论。他打开粒子对撞机,等着看对撞结果。实验结束,他从主控室冲进走廊,手里拿着显示粒子轨迹的打印稿。他撞上了另一个科学家,那个科学家问他:‘雅克,你看到我们希望观测到的那两个粒子了吗?’雅克先指了指一条轨迹,又指了指另一条,然后喊了声:‘麦威!希格斯玻色子!夸克!’” (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译注)
凯尔看着那对镜头,干瞪眼。
猎豹把包袱又抖了一遍:“麦威!希格斯玻色子!夸克!”
“我没听懂。”凯尔说。
“希格斯玻色子是一种不带电荷的零自旋粒子;而夸克是组成质子和中子的基本成分。”
“老天!我当然知道它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不懂的是这个笑话有什么好笑的。”
“这是个双关。“麦威”是法语,意思是‘是的!’――麦威!希格斯玻色子!夸克!”猎豹顿了顿,接着说,“麦瑞·希金斯·克拉克。”又顿了顿,“她是个有名的推理作家。”
凯尔叹了口气说:“猎豹,这个笑话太复杂了。双关语要好笑,就得让人一下子就能理解,解释了就不灵了。”
猎豹沉默了片刻。
“哦,”他最后说,“我又让你失望了是吗?”
“也不是那样,”凯尔说,“不完全是。”
猎豹是个“模叽”,就是专门为模拟心理体验而编写的计算机程序。猎豹模拟的对象是人类。凯尔一直鼓吹强人工智能原则:人脑不过是一台有机物计算机,心灵不过是这台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他在1990年代末公开接纳了这个立场。这个想法在当时显得相当合理,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每18个月增加一倍,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在存储容量和连接数目上都超越人脑的计算机。按理说,计算机一旦发展到那个地步,就应该可以复制人的心灵了。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计算机已经发展到了那个地步。实际上,根据大多数人的估算,就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复杂程度而言,电脑在四五年前就已经超越人脑了。
然而,猎豹却还是不能区分好笑的笑话和冷笑话。
“如果我没有让你失望,”猎豹说,“那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呢?”
凯尔环顾了一下实验室:内墙和外墙都呈弧形,是沿着穆林堂的轮廓造的,墙上没有窗,天花板很高,一块块发光板覆盖在金属框架上。他说了声“没有”。
“别跟忽悠大师忽悠。”猎豹说,“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教我怎么识别人脸、怎么识别人脸上的各种表情。我到现在还不太擅长,可我一眼就能认出你的脸,也知道怎么解读你的情绪。你正在为什么事情生气呢。”
凯尔撅起嘴唇,盘算着要不要回答。猎豹的每个举动都是运算的结果;对它的问题,凯尔自然没有义务回答。
可是……
可是今天,实验室里到现在都只有他一个人。他昨天离开家后,一晚上都没睡着――他到现在还是把那当成“家”,而不是“希瑟的家”――今天他来早了,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机器设备和头顶的荧光灯发着细微的嗡嗡声,还有就是猎豹那低沉的、鼻音浓重的语声。看来语音回路得调整调整了,他曾试着让猎豹模拟自然粗重的呼吸,结果它一模仿人说话就发出刺耳的声响。猎豹本来已经有点像人了,但是这次改进之后,它和真人之间的差别反而更加明显了。
不,他当然不用回答猎豹的问题。
但或许,他是想回答的。说到底,这件事还有谁可以商量呢?
“开启私密闸。”凯尔说,“以下的对话不得向任何人传播,也不得在事后进行任何调查。明白吗?”
“明白。”拜语音编码器的故障所赐,最后的那个“白”字被拖得很长。接着是一片沉默。最后,还是猎豹挑起了话头:“你想讨论什么呢?”
要从何说起呢?老天!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一台电脑倾诉。可是,这件事也实在不能对其他人说――他可不能被人说闲话。他还记人类学系的史东·本利的遭遇:五年前,一个女生指控他性骚扰,虽然法庭为他洗脱了罪名,女生最后也撤回了指控,但他还是没得到副系主任的位子。就算到了今天,凯尔还时不时地听见其他教师和学生偷偷地评论此事。不行,那种事可不能落到他头上。
“其实也真没什么。”凯尔开口了。他拖着步子走到房间另一头,给自己倒了一杯煮好的咖啡。
“拜托,别停。”猎豹说,“告诉我吧。”
凯尔挤出了一丝微笑。他知道,猎豹不是真的好奇,而是模拟。那个模拟好奇心的算法就是他写的: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很勉强,就推他一把。
他也确实需要和什么人谈谈。他本来就睡不好觉,出了这件事更加够呛。
“我女儿对我很生气。”
“瑞贝卡。”猎豹说――这是另一个算法:和对方套近乎,让对方觉得宽心。
“对,瑞贝卡,她说……她说……”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她说什么?”鼻音让猎豹的声音显得格外热切。
“她说我骚扰她。”
“怎么骚扰?”
凯尔重重地叹了口气。没有哪个真人会问这个问题。老天,我可真蠢……
“怎么骚扰?”猎豹又问了一遍,它的时钟显然在告诉它再推对方一把。
“性方面的。”凯尔小声回答。
猎豹控制台上的麦克风相当灵敏,它肯定听到了,但是它沉默了一会――这又是一个程序化的虚假反应。最后它说了声:“哦。”
凯尔看见控制台上灯光闪烁:猎豹正在接入互联网、快速搜索主题。
“你什么人都不能告诉!”他连忙说道。
“我明白。”猎豹说,“那么,你做了被指控的事吗?”
凯尔感到心头冒火:“当然没有了!”
“你能证明吗?”
“你这他妈的算什么问题?”
“一个重要的问题。” 猎豹说,“我猜想,瑞贝卡对这个指控是没有真凭实据的。”
“当然没有。”
“但另外,也可以假设你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个……是没有。”
“那么,有谁会相信你呢?”
“任何人在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清白的。”凯尔辩白。
猎豹的控制台奏响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前四个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愿意花力气把真实的笑声编入程序――猎豹的幽默感老是出错,用不着笑――音乐权且代替笑声:“照理说我应该很幼稚的,格雷夫斯博士,可如果你是清白的,她又为什么要指控你呢?”
这个问题,凯尔不知道如何回答。
猎豹根据程序的指示沉默了片刻,接着再次问道:“如果你是清白的,她又为什么――”
“闭嘴。”凯尔说。
3.
谢天谢地,希瑟不用教暑期班。那天贝姬上门之后,她整晚都在翻来覆去,第二天上午11点才从床上爬起来。
出了这样的事,生活还怎么继续下去?她很想知道。
十六个月前,玛丽死了。
别这样,希瑟心想,要面对现实。玛丽在十六个月前自杀身亡,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贝姬那时候还住在家里,姐姐的尸体就是她发现的。
要怎么继续下去呢?
下一步该怎么办?
贝姬出生那年,比尔·科斯比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艾尼斯[ Bill Cosby,美国演员,其子Ennis于1997年被射杀――译注]。那时候,一个新生儿正在希瑟的怀中吮吸奶水,还有一个精力充沛的两岁娃娃正围着屋子狂奔。受到触动的希瑟写了一封表达同情的信,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转交给科斯比。身为母亲,她知道再也没有什么比失去一个孩子的打击更大了。当然了,有几万个人给科斯比写去了这样的信。他――或者是他的雇员――给希瑟回了信,感谢她的关怀。
科斯比终于撑下去了。
也是在那时,另一位父亲每晚都在新闻里露面,他是弗莱德·古德曼,他儿子罗恩·古德曼同尼可·布朗·辛普森一道被杀。弗莱德对O·J·辛普森怒不可遏,他相信就是辛普森杀了他的儿子[ O·J·辛普森,美国橄榄球运动员,1994年被控杀害妻子和餐馆招待罗恩·古德曼,后经审理无罪释放――译注]。他的怒火在电视屏幕上呼之欲出。古德曼一家后来出了书,标题是《他的名字叫罗恩》。他们在大学边上的查普特书店签售时,希瑟还去和他们见了面。她自然知道这本书会在几个月后降价出售,就像和辛普森一案有关的其它碎屑一样。但她还是去买了一本来让弗莱德签名,以此显示一个母亲对一个父亲的支持。
弗莱德·古德曼终于撑下去了。
玛丽自杀之后,希瑟在自己的藏书里面找过古德曼的那本书。它还在,就立在起居室的一个书架上,边上放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号格蕾丝》,那是希瑟在差不多同时破费购买的另一本精装书。希瑟把古德曼的那本书拿下来翻看过,里面有弗莱德的照片,都是和家人拍的,一张张表情快乐的脸;而是在希瑟的记忆中,那张脸上却充满了对辛普森的愤恨。当你的孩子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你的愤恨要向那里发泄?向谁发泄?
答案是没有人。你只能把怒火消化,让它在体内慢慢地蚕食你,一点一点、一天一天。
答案是每个人。你可以四面出击,你的丈夫、你的其他孩子、你的同事,都会遭殃。
没错,你也可以撑下去,但是你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
但是这一次――
这一次,如果贝姬说得是真话――
如果贝姬说得是真话,那就有这么一个人可以让她发泄怒火。
那个人就是凯尔,贝姬的父亲,她那个疏远了的丈夫。
当希瑟在圣乔治街上往南走的时候,她心里想的是装在起居室墙上镜框里的外星无线电消息。希瑟是个心理学家,过去十年,她都一直在尝试破解外星人的消息、探索外星人的思想。对于那条消息,她比地球上的任何人都要了解――她已经为此发表了两篇论文,但还是不明白它究竟在表达什么意思;完完全全地不明白。
话说回来,希瑟认识凯尔已经将近二十五年了。
但是,她真的了解他吗?
她试着清空自己的大脑,试着把前一晚的震惊放到一边去。
这天的下午阳光明媚。她眯眼看着太阳,又琢磨起了那些发出信号的外星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或许没有什么共同点,但至少在半人马座也能看到这样的日光。外星人长什么样当然没人知道,但政治漫画家还是按照希腊神话中人马的样子给他们画了像。人马座阿尔法A简直就是地球的双胞胎姐妹,光谱型也是G2V、温度也是5800开,所以从行星上看,它也该闪着黄白色的光。是的,当温度较低,当个头较小的人马座阿尔法B升上天空时,它可能会增添一些橙色的光芒。但有的时候,空中只有阿尔法A;那时,人马座的居民和地球人就会看到同样的风景。
她继续在街上朝办公室走去。
我们得撑下去,她想,得撑下去。
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周六的早晨,凯尔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圣乔治站下车,而是多乘了四站、一直到奥斯古德站才下。
贝姬的男朋友扎克·马科斯在皇后西街的一家书店当营业员。小贝姬在过去一年里跟他提过,他记住了。凯尔不知道具体是哪家书店,但那里反正也没几家。念中学的时候,他经常在周六的下午去皇后街寻宝,他在“巴卡”找过新出版的科幻小说、在“银蜗牛”搜过刚上市的漫画、还在街边的十几家旧书铺里淘过绝版书。
但独立书店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其中的大多数要么迁到地段差一点、租金便宜点的地方,要么干脆关门大吉。最近一段时间,皇后西街两边大多是时髦的咖啡馆和小饭店,大学道上的地铁出口旁有一幢洛可可风格的大楼,加拿大的一家广播巨头就将总部设在其中。街边剩下的书店不会超过三四家,凯尔决定一家家地拜访。
先从街北边那家历史悠久的“页码”书店找起。他朝四处张望了一下――扎克不像贝姬,他是个大学生,所以多半是在周末而不是平时上班。店里没有扎克那一头金发的高瘦身影。但凯尔还是走到了收银员跟前,她是个东印度美女,戴着八个耳环。“你好。”凯尔说。
她冲他笑了笑。
“扎克·马科斯是在这儿干活吗?”
“我们这儿只有一个扎克·巴博尼。”她说。
凯尔觉得自己的眼睛瞪大了一些:他小的时候,大家的名字都挺正常的――大卫、罗伯特、约翰、彼得。他只听说过一个叫“扎克”的,就是连续剧《迷失太空》里那个笨手笨脚的扎克雷·史密斯。现在不同了,好像随便哪个小孩都叫扎克或者奥丁或者慧翼。
“不,那不是他,”凯尔说,“谢谢。”
他接着朝西走。一路上碰见不少乞丐求他施舍。他年轻的时候,多伦多的乞丐很少很少,少到他都不好意思说“不”。但现在,市中心到处都是乞丐,乞讨的时候总是带着加拿大人的那种小心翼翼的礼貌。凯尔已经练就了多伦多式的目不斜视,他下巴朝前,不和乞丐做眼神接触,但还是会对他们微微摇头,表示“不给”。毕竟,完全无视对你说话的人总是不礼貌的。
“多伦多,好地方。”他想到了以前的这句广告词。今天的乞丐群体中什么人都有,但还是以加拿大原住民居多――凯尔的父亲仍然把他们叫做“印第安人”。实际上,凯尔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见过不是乞丐的加拿大原住民了,保留地那边想必还有不少。几年前,他的班上来了两个原住民,都是一个现已停止运作的政府项目送来的。可是,他想不起来多伦多大学的教师里有哪怕一个原住民――讽刺的是,连做原住民研究的都没有。
凯尔继续走着,终于到了巴卡书店门口。这家书店1972年在皇后西街开张,二十五年后搬离原址,现在又搬回来了,离最早的店址不远。如果扎克在这儿干活,贝姬肯定对他说过,他也一定记得。但他还是得进去看看……
书店前面的玻璃橱窗上刷着书店名称的由来:
巴卡:名词;类别:神话。在弗雷曼人的传说中,巴卡是为全人类哭泣的哀悼者。 (皆为科幻小说《沙丘》中虚构的名词――译注)
最近巴卡可要加班加点了,凯尔心想。
他走进书店,对柜台后面那个矮妖般的大胡子男人问了几句。但他们这儿也没有扎克·马科斯。
凯尔接着寻找。他身上穿着Tilley牌狩猎衫和蓝色牛仔裤,讲课时穿的也差不多是这一身。
下一个书店位于大街的南边,还要往下走一个街区。凯尔等着一辆红白相间的有轨电车轻轻驶过――最近都改成磁悬浮的了――然后穿过了街道。
这家书店比巴卡高档得多。最近有人出了一大笔钱改造这座赤褐色的砂石建筑,建筑表面经过喷沙,弄得很干净。现在大多数人都开悬浮车了,但许多建筑物的表面还是带着几十年来汽车尾气留下的污渍。
凯尔开门进去,一只铃铛响了一下。店里有十来个顾客。或许是听见了铃声,一个店员从一只深色的木制书架后面走了出来。
那就是扎克。
“格……格雷夫斯先生。”他结巴道。
“你好,扎克。”
“你怎么来了?”扎克的声音带着怨恨,似乎光是提到凯尔他就令他厌恶。
“我要跟你谈谈。”
“我在上班。”语气轻蔑。
“看出来了。什么时候休息?”
“中午前都忙。”
凯尔连表都没看就说:“我等你。”
“可是――”
“我必须和你谈谈,扎克,我有这个权利。”
男孩瘪了瘪嘴,想了想,然后点点头。
凯尔通常喜欢在书店里四处翻看,特别是翻看大部头的书,但今天他在等待的时候太紧张了,没法集中精神。他看了会《科伦坡加拿大语录》,读了读前人关于家庭生活的意见。科伦坡认为,最有名的加拿大语录是麦克卢汉说的“媒体即信息”。这句话也许道出了事实,但是还有一句话更加常用,尽管它不限于加拿大人,那就是:“我的孩子们恨我。” [ 约翰·罗伯特·科伦坡,加拿大作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传播学家――译注]还有点时间可以打发。凯尔走出了店门。隔壁的店是卖海报的。他走进去四下看了看,装修用的全是铬黄和黑色亮漆。罗伯·贝特曼的野生动物画有很多;七人画派的东西有一些;让-皮埃尔-诺曼的系列作品;当红流行歌手的照片;旧电影海报,从《公民凯恩》到《绝地武士的沦落》;上百张全息海报,包括陆地、天空和海洋的风景。[ 罗伯·贝特曼,加拿大画家;七人画派,二十世纪初的加拿大画家团体;让-皮埃尔-诺曼,科幻插画家――译注]
还有达利,凯尔一直喜欢达利。这里有《记忆的永恒》,就是手表熔化的那张;有《最后的晚餐》;还有……
对了,是《耶稣受难》,这个正好可以拿给学生看。这幅画了他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了,挂在实验室里想必能活跃气氛。
挂这样一张宗教意味的画肯定会遭人抨击,但是管他呢。凯尔找到放海报的沟槽,从里面抽出一张卷好的走到收银台前。收银员是一个东欧男人。
“三十九块九毛五,”店员说,“加税,加税,加税”。加的是省销售税、商品服务税和国家销售税――加拿大居民是世界上缴税最多的人。
凯尔递上自己的智能卡。店员把它在读卡器上一放,总价随即从卡上的芯片里扣除。店员接着在装画的圆桶外套了个小袋子,然后递给凯尔。
凯尔回到了书店。几分钟后,扎克的休息时间到了。
“我们在什么地方谈?”凯尔问他。
扎克看上去还是不情不愿的样子,但过了一会他说:“去办公室?”凯尔点了点头,扎克把他领到后面的房间。那房间怎么看都不能冠以“办公室”之名,倒更像是个储藏室。扎克把门在身后关上。几个摇摇晃晃的书架和破旧木头办公桌就把这地方塞满了。书店并没有花钱改善一下这个角落;外观才是一切。
扎克把唯一的一张椅子让给凯尔,但凯尔摇了摇头。扎克坐了上去,凯尔把身子靠在一个书架上,书架稍微挪了挪。他往后退了一步,不想让那玩意儿塌在他身上;最近他身上已经够沉了。
“扎克,我爱贝姬。”凯尔说。
“没有一个爱她的人――”扎克语气坚决,“――会做你做的那种事。”他犹豫了一会,好像是吃不准要不要再冒个险。随后,带着年轻人的那种正义感,他又补充了一句:“你这个禽兽。”
凯尔想把这小屁孩拖过来揍一顿:“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绝对不会伤害她。”
“你已经伤害了她,她已经不能……”
“不能什么?”
“没什么。”
但凯尔已经从猎豹那儿学了一两手。“告诉我。”他说。
扎克似乎是权衡了一阵子,接着脱口而出:“她连做爱都不能了!”
凯尔感到心脏“怦怦”直跳。贝姬在性上应该是很活跃的,她才十九岁啊,老天!尽管他也怀疑过这个,但亲耳听说还是令他心里一沉。
“我从来没有摸她不该摸的地方,从来没有。”
“她不会高兴我跟你说话的。”
“去他妈的,扎克,我的家庭正在瓦解。我需要你帮忙。”
扎克冷笑:“星期四晚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这是你们家的事,还叫我不要我掺和。”
“贝姬不愿和我说话,我需要你来调停。”
“怎么调停?跟她说你没碰过她?她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可以证明我没有,所以我才来找你,我希望你答应到大学来一次。”
听到这里,穿着雷尔森大学T恤的扎克坐不住了。凯尔知道,多伦多另两所大学的学生很讨厌多伦多大学的人只把自己的学校称作‘大学’。“我为什么要来?”扎克质问。
“多伦多大学有刑侦科学的课程。”凯尔说道,“我们有个测谎实验室,我认识的一个人就在那里工作。他在几百个案子里当过专家证人。我想让你去一次那个实验室,我会自己连上测谎仪,然后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伤害过贝姬――我不可能伤害她。你会明白这是实话的。”
“你可以让你的朋友操纵测试。”
“那我们可以在其它地方做测试。你来指定实验室,我来付钱。等你知道了真相,说不定可以帮我劝劝贝姬。”
“一个病态的骗子是可以骗过测谎仪的。”
凯尔的脸涨得通红,他冲上去一把抓住了男孩的衬衫前襟。但随后,他又退了下来,张开双臂,摊开双手。“抱歉,”他说,“抱歉。”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了下来,“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你为什么就不让我证明呢?”
扎克的脸也涨得通红;刚才他以为凯尔真要对自己动粗的时候,体内的肾上腺素一定升得老高。“我不要你做测试。”他用沙哑的嗓音说道,“贝姬已经对我说了你的作为,她从来不对我撒谎。”
她当然有过,凯尔心想。人随时都在对别人说谎。“我没做过。”他又说了一次。
扎克摇了摇头:“你不明白贝姬都经历了什么。她现在已经在好点了。星期四那天,我们离开你家之后,她一连哭了几个钟头,现在她已经好多了。”
“但是,扎克,你是知道的,贝姬和我已经分开快一年了。如果我真的做错了什么,她肯定早就离家出走了,或者至少会在离家后马上指责我。可到底为什么――”
“你觉得这种事是随随便便就能开口的吗?她的治疗师说――”
“治疗师?”凯尔觉得自己挨了一下重击。她的亲生女儿在接受心理治疗,他妈的他竟然不知道?“她在接受什么鬼治疗?”
扎克做了个怪脸,表示答案不言而喻。
“那个治疗师叫什么?我说服不了你,或许能说服他。”
“我……不知道。”
“你在撒谎!”
但这句指责反而让扎克更加坚决了:“我没有,我不知道。”
“她是怎么找到这个治疗师的?”
扎克微微耸了耸肩:“那就是她姐姐的治疗师。”
“玛丽的?”凯尔倒退了几步,撞到了另外那张木头办公桌上;桌角有张餐巾纸,上面本来放着个吃了一半的炸面包圈,现在桌子震动,它掉到了地上。“玛丽也接受过治疗?”
“当然了,你对她做了那种事,谁还能怪她?”
“我没有对玛丽做过任何事!我也没有对贝姬做任何事!”
“那么,她们都在撒谎喽?”扎克反问。
“不是的……”凯尔停了下来,努力克制自己的嗓音,“他妈的,扎克,操他妈的!这事你也有份,你们俩要告我,是吧?”
“贝姬要的不是你的钱。”扎克回答,“她要的是宁静,要的是闭合。”
“闭合?闭什么鬼合?她的治疗师就对她说了这个?操蛋的闭合?”
扎克站起身来:“格雷夫斯先生,回家吧。还有,看在老天的份上,给你自己也找个治疗师。”
凯尔怒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穿过零售区,一头扎进了夏天的酷热里。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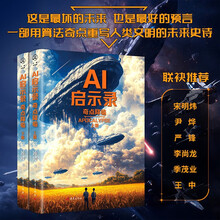


——《新科学家》
充满智慧、引人入胜的双线叙事小说,全书富有节奏感,最后几页开始飞奔。
――《科克斯书评》
这是一部严肃的科幻长篇,由一群深陷个人危机的人们担当主角。
――《科幻编年史》
这是近年来“第一类接触”小说中少有的佳作。索耶的叙事才能让这本《人性分解》脱颖而出。
――《落基山新闻》
科学上成熟的设定、真诚热心的语调、巧妙的情节设计。
――《多伦多星报》
本书中的科学,无论理论上还是应用上,都是令人满意的,索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同样如此。
――《圣迭戈联合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