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的一个下午,简?惠特克前往商店买些牛奶和鸡蛋的途中,走着走着,竟然忘记了自己是谁。
当时,她站在坎布里奇和鲍登大街的交汇处,一眼便认出这是波士顿闹市区。她很清楚自己身居何处,至于自己是谁,却毫无头绪,一无所知。这一切来得十分突然,毫无征兆。她确信自己是在去杂货店买牛奶和鸡蛋的途中。她本打算用牛奶和鸡蛋做个巧克力蛋糕,而为什么要做蛋糕、为谁做,她却说不上来了。她清楚地记得做个蛋糕需要多少速溶巧克力布丁,却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她不知道自己是已婚还是单身,丧偶还是离异,有无孩子。她记不起自己的身高体重,眼睛的颜色,就连自己的生日或是年龄,她也全然不知。她能辨认出各种树叶的颜色,但想不起自己头发的颜色。她知道自己要去的大致方向,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去过哪里。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鲍登大街上的车辆徐徐停了下来,仿佛有块磁石把她身边的行人一下子都吸到了大街对面。只有她,脚底像生了根似的独自站在原地,无法挪动半步,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低下头,脸蹭着风衣的领子,偷偷地向左右张望了一下。路人行色匆匆,似乎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男男女女的脸上没有露出犹豫的神情,步子没有丝毫的迟疑。只有她静静地站在原地,不愿——也无法——移动脚步。她听见各种声音——汽车引擎嗡嗡的轰鸣声,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人们的说笑声,他们经过她身旁时鞋子交替发出的拖沓声和咔哒声,以及车辆重新开动时陡然停止的脚步声。
忽然,一个女人低低的怒骂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小贱人!”那个女人压低嗓音厉声骂了一句。一时间,简以为那个女人在议论自己。可是,那女人正与闺密聊得火热,她俩都没发觉简近在咫尺。难道她会隐身不成吗?
就在这时,她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有些荒唐的想法:说不定自己已经死了,就像那部老电影《阴阳魔界》里的一个片段——一个女人被困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她急疯了,忙给父母打电话;没成想,对方告诉她,他们的女儿早死于一场车祸,还责问她是谁,为什么深更半夜打电话骚扰他们。就在这当儿,几秒钟前还撅着嘴骂“贱人”的那个女人终于察觉到简的存在,对她报以天使般的微笑之后,便转过头,和闺密一起走开了。
显然,她没有死,也不会什么隐身术。可是,为什么她能想起《阴阳魔界》里那些无聊的片段,却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呢?
又有一拨人来到她身边,他们不是用鞋尖叩打着路面,就是来回旋动着脚跟,焦躁地等着穿过马路。不管她是谁,她都无人相伴,没人挽住她的胳膊,也没人站在街对面,焦急地望着,纳闷她为什么会落单。她孑然一身,茕茕孑立,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保持冷静。”她小声说道,想从声音里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可是,就连声音她也觉得陌生。她的声音除了透出一丝焦虑之外,几乎与常人无异,没有任何明显特征,她无法通过声音判断自己的年龄或婚姻状况。为了不引人侧目,说话时她用手紧捂着嘴。“别慌,时间一到,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她有自说自话的嗜好吗?“要紧的事先做。”她接着说。话虽如此,但她完全不明白其中的用意。连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她,如何能挑紧要的事做?“不,不对,”她马上更正。“你并不是一无所知,你知道很多事。别着急,看看情况再说。”她大声地安慰自己,眼睛快速瞄了一下周围,看看是否有人听见自己说话。
一群人朝她走来,他们大约有十个人。他们会把我带回那个我逃出来的地方——这是她心里闪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想法。不一会儿,他们的领队,一个二十一岁左右的年轻女孩,开始说起话来。听到她那浓重的波士顿口音,简感到很熟悉。奇怪的是,她自己倒没有这种口音。她意识到,在那些人眼里,她无关紧要,如同她在之前那两个女人眼里一样。她对任何人都无足轻重吗?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年轻女孩说,“在灯塔山,波士顿人能走路去上班。长久以来,它一直被视为波士顿的黄金社区,陡峭的街道全部用鹅卵石铺成,街道两边是私人别墅和小公寓楼。这些建筑始建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并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些私人别墅和小公寓楼,年轻女孩则继续背诵烂熟于心的讲稿。“近些年,由于住房短缺以及波士顿地区房产价飙升,这里有不少大一些、外形更别致的房子被改为托管公寓。灯塔山过去曾是南北战争中的北美要塞。虽然许多波士顿的古老家族仍住在这儿,但现在它也欢迎不同背景的人……只要他们能付得起房租或贷款。”
一番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和点头称赞过后,人群准备往前走。“对不起,这位女士。”领队喊道。只见她睁大眼睛,扯动嘴角,挤出一个夸张的笑容,宛如一枚栩栩如生的笑脸徽章。“我想,你应该不是我们团的吧?”她的嘴角随着最后几个字的声调而上扬,把陈述句变成了问句。“如果你对城市徒步游感兴趣,你得去波士顿公园的旅游信息中心。他们会为你登记下一轮的旅游。明白吗,女士?”
那枚笑脸徽章看起来有点恼火。
“公园?”她问道。不过,这女孩不假思索地称她为“女士”,说明她看起来至少有三十岁。
“沿着鲍登大街向南走,一直走到灯塔街,你会看到途经州议会大厦——一栋有金色圆屋顶的建筑。那里就是公园,你一定能找到。”
望着旅游团穿过马路,消失在下一条街道,简暗自想:别把话说得这么肯定,如果我想不起自己是谁,我可能会一无所有。
她如蜗牛般缓慢地挪动脚步,仿佛踏进了一片极其陌生、危机四伏的水域。她沿着鲍登街走去,一路上只顾埋头看路,对那些十九世纪的建筑几乎视而不见。她顺利地穿过了德恩大街和阿士柏顿大街。然而这些沿途忽然出现的街道和州议会大厦都没能唤起她的记忆,让她想起自己可能是谁。她拐个弯,来到了灯塔街。
正如笑脸徽章所说,一到灯塔街,波士顿公园就立刻映入她的眼帘。她匆匆穿过游客中心,朝着公共花园走去,对旧谷仓墓园视若无睹,尽管她一下子就想起那里有很多名人的坟墓,比如保罗?里维尔和古斯大妈。她本能地觉得,自己以前经常这样干。也许她对自己一无所知,但对波士顿,却并不陌生。
她感觉膝盖发软,便拖着腿朝一张长椅走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别慌……”她知道周围没人听见,便像念咒语似的大声重复了好几遍。她开始默念一些已知的,但无足轻重的事实。今天星期一,一九九〇年六月十八日。天气冷得反常,只有华氏六十八度。华氏三十二度能让水结冰,一百摄氏度能煮熟鸡蛋。2乘以2等于4,4乘以4等于16,16乘以16等于256;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E=mc?;365的平方根是……她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不过直觉告诉她这没关系——以前她可没有这样的感觉。她用手抚平棕色外衣的皱褶,感到手指在纤细修长的大腿上滑过,又说了一句,“别慌。”这些她能记得的基本常识,让她心里踏实了不少。一个能记住这些常识的人怎能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呢?她会想起来的,这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小女孩张开双臂,从公园的另一头朝她跑过来,胖乎乎的黑人保姆在后面一路紧随。一时间,她猜想这小女孩可能是自己的孩子,本能地把手伸向她;保姆却迅速地把小女孩拉走,把她带到了附近荡秋千的地方,并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我有孩子吗?”她问自己,不明白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忘了自己的孩子。
她看了看手,至少手上的戒指能告诉自己是否结过婚。可是,光洁的手指上空无一物,只有左手无名指上有一圈细细的印痕,或许那里曾经有过一枚戒指。虽然她再三研究,仍然不敢确定。不过,她发现桃红色的指甲油已经剥落,指甲被咬得露出了嫩肉。接着,她把目光投向了双脚。她穿着一双骨色的低跟漆皮鞋,右脚的大脚趾被鞋子夹得生疼。她脱下右鞋,发现内侧印着“查尔斯?卓丹”的字样,是九码的鞋,这说明她身高至少一米七二。从紧紧裹在身上的风衣和垂在身体两侧的胳膊来判断,她应该很苗条。她还能发现什么别的吗?她知道自己是白种女人,也许结过婚,早已不止二十一岁。此外,她还知道什么?
这时,两个女人手挽着手走过,她们的挎包拍打着身体。挎包!她舒了一口气。挎包会揭开所有的秘密——她是谁,住在哪儿,用什么颜色的唇膏。挎包的钱夹里会有她的身份证、驾照和信用卡。她会重新知道自己叫什么,家住哪里,何年出生,开什么样的车——如果她开车的话。挎包里藏着所有的秘密,她只需打开挎包!
打开挎包之前,她要做的就是找到它!
她胡乱套上鞋子,靠在公园深绿色的长椅上,不得不接受她心知肚明却害怕承认的事实——她没有挎包。当她开始这次怪异之旅之际,不管她带有什么身份证明,现在都找不到了。为了确保自己坐下来时没有把包乱扔到地上,她细心查看四周,反反复复检查脚下的草地,甚至还围着长椅转了几圈。她的奇怪举动,再次引起在附近陪孩子荡秋千的黑人保姆的怀疑。简朝着皮肤黝黑的保姆笑了笑,便转身离开了。几秒钟后,简回头看了看,发现保姆正催促孩子离开那里,孩子大声抗议,不愿离开。“瞧,你吓着她了。”简大声地喊道,不自觉地用手摸了摸脸,检查脸上是否有吓人的疤痕。还好,她的脸好像没有什么疤痕。于是,她继续像盲人一样用手摸索着自己脸的轮廓。
她有张窄小的鹅蛋脸,颧骨很高,有点突出,眉形完美。她的鼻子小巧玲珑,睫毛上涂了一层厚厚的睫毛膏。但也许她手重,涂得不够均匀;也许她揉过眼睛,弄得睫毛膏粘住了一些睫毛;但也说不定她曾哭过,眼泪黏住了睫毛。
忽然,简挺直肩膀站起来,大步流星地走出公园,来到大街上,对红灯视而不见,逆着车流朝灯塔街街角一家银行跑去。她使劲地敲打着玻璃门,引起了经理的注意。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有些秃顶。他头小身子大,与身材相比,他的脑袋似乎要小好几号。他西装革履,系着领带。“对不起,”他彬彬有礼地说,把门打开一条缝,刚够他的大鼻子探出来,“现在已经四点多了,我们三点就关门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绝望之下,简问了一个自己也颇感吃惊的问题。
那个男人皱起眉头,以为简要求特殊待遇。“真对不起。”他的声音明显透出不安的情绪。“我保证,如果您明天来的话,我们会为您提供服务的。”他笑了笑,接着固执地撅起嘴,表示没有商量的余地,转身回到办公桌旁。
她站在玻璃门外,盯着里面的银行职员,害得他们开始小声嘀咕起来。他们知道她是谁吗?这时,经理气得双臂疯狂地胡乱比划着。在他的干预下,职员们这才把注意力转回到电脑和收支清单上,对她置之不理,仿佛她不存在似的。她真的存在吗?
她深吸几口气,沿着灯塔街一直走到环河街,重新朝陡峭的铺满鹅卵石的大街走去。街道两边耸立着一座座私人别墅和小公寓楼;她在那里惊醒,也在那里迷失自我。她就住在其中一栋十九世纪的房子里吗?她有钱付房贷或房租吗?她在不在乎钱?她是不是腰缠万贯?她是替人打工还是自己做老板?也许她并不住在这些漂亮的老房子里,她只是个清洁工而已。
不对,她穿着入时,不会是个清洁工。虽然样子有点邋遢,可是她双手柔软,没长老茧,不是习惯劳作的人。也许她不是清洁工,而是卖房子的。说不定她是为了卖房子,才来到这里。也许她是来见客户,向他们展示刚翻修好的房子……嗯?难道她被落下来的砖头砸中了?想到这里,简赶紧摸摸脑袋,看看头上是否起了大包。幸运的是,她没摸到肿块,只是辫子有些松了,胡乱地搭在肩上。
她在弗农山街右转,然后在柏树街左转,希望某样东西会向她的大脑传递必要的信号,唤起她的记忆。到了里维尔路,她又拐个弯,向堤坝路走去。“快冒出点让我眼熟的东西来吧。”她对着绿树成荫的大街轻声哄劝。太阳躲在一大片乌云后面。虽然气温没有变化,她还是觉得有点冷,想起去年冬天气温相对温和,专家预测今年会一个酷暑。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温室效应。温室、绿色和平组织、酸雨、拯救雨林、拯救鲸鱼、节约用水——与朋友一起淋浴。
她突然觉得筋疲力尽,双脚酸疼,右脚大拇指完全麻木,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她多久没吃东西了?说到吃,她喜欢什么样的食物?她会做饭吗?也许她被某种古怪的饮食损伤了大脑。也许她嗑了药或喝了酒,亢奋不已。她喝醉了吗?她以前喝醉过吗?她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醉了?
简双手捂住眼睛,希望自己头痛恶心,预示她很快醉意大发。这时,她想起了雷?米兰主演的电影《失去的周末》,在心里琢磨,既然她能记住雷?米兰,她应该会是多大年纪。“帮帮我吧,”她捂着脸小声地说,“请帮帮我吧。”
她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腕,发现快到五点了。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晃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却仍然没发现任何有关自己身份的线索。一切都很陌生,周围也没有人认出她。
不一会儿,她发现自己来到查尔斯街。这里有各式各样既舒适又诱人的商店,上至珠宝古董店下到杂货店,里面的商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从五金器具到艺术品应有尽有。她要来这里买牛奶和鸡蛋吗?
这时,一个男人与她擦肩而过,对她笑了笑。这不是忙碌一天后,一个疲惫不堪的人对另一个同样疲惫不堪的人露出的笑容,两个人谈不上认识。即使这样,简还是很想抓住他的肩膀,恳求他做些暗示,表示他知道她是谁。必要的话,猛摇他的肩膀,让他说出她是谁。但简并没有骚扰这个路人,她不能跟街上的陌生人搭讪——他们说不定会给警察打电话,把她关起来。这样的话,世上又会多个想找回自己的疯女人!
她真的疯了吗?她是刚从收容所还是监狱逃出来?她在逃亡吗?她不禁嘲笑自己太会演戏了。如果这场戏开始前她还神志清醒,等到结束时她肯定会疯掉。这场戏会结束吗?
她推开一家便利店的门,走了进去。如果她就住在附近,她可能经常光顾这家小店。最起码,她希望自己以前来过很多次,柜台后面的那个男人和她很熟络。于是,她慢慢地穿过罐头食品的货架,向那个男人走去。
商店老板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扎着马尾辫,脸上坑坑洼洼,嘴唇很薄。客人们正把他团团围住,争先恐后说自己排在第一位。她站在最后,只看见小伙子转身拿烟时瘦骨嶙峋的后背。
她扭头朝左边望去,看见一排杂志,封面上一个个年轻靓丽的女孩也在盯着她看。她走近杂志架,盯着一本杂志封面上那个模特性感的脸庞。辛迪?克劳馥,旁边有一行亮粉色的字,超级模特。毫无疑问,谁都知道她是谁。
她从架上拿起杂志,仔细端详起这位超级模特的脸:棕色的双眸,棕色的头发,微张的双唇左边有颗黑痣,正是它让她从千百位同样美丽的女人中脱颖而出。她想,这女人真是明艳动人、朝气蓬勃、信心十足。
她突然又想起,对自己的长相,她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年龄,她毫无概念。她紧紧抓住杂志两侧,书边都被她卷了起来。“嘿,女士。”一个男人大声喊道。她转过身,看见店老板挥动手指警告她,“如果你不买,就别碰它们。”
简羞愧难当,像偷糖时被人当场抓住的孩子。她点头表示理解店规,却仍站在原地不动,把杂志紧贴在胸口,仿佛它是根救命稻草。
“喂,你到底买不买?”年轻人问道。此时,其他顾客已经离去,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这可能是解开“她是谁”这个谜团的唯一最佳时机。
她走向柜台,看到他迅速地后退一步。“你认识我吗?”简问道,语气尽量显得平静。
他站在原地,眯起眼盯着简,然后歪起头,辫子扫过右边肩膀,笑容爬上他的嘴角,他的嘴巴慢慢弯成了半圆。“你是哪个明星大腕?”他问道。
她是吗?她自己也纳闷。不过,她一声不吭,屏住呼吸,等着他往下说。
他把简的沉默当成了默认。“哦,我知道,现在有几部电影在波士顿拍摄。”他向右走了几步,仔细打量她的侧面。“我不常去电影院,也没在电视节目里见过你。喂,你是不是演过肥皂剧?我知道,女演员会到购物中心这类地方购物。我姐就曾让我带她去那里,她想见在《后生可畏》里扮演阿什利?艾伯特的演员。不过,我管它叫《后生无用》。你演过那部肥皂剧吗?”
她摇摇头。让这毫不知情的家伙猜来猜去有什么意义?显然,他对她的了解不比她自己多。
她注意到小伙子全身紧张,肌肉僵硬。“唔,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不是明星大腕,都得掏钱买杂志,两块九毛五,一分不少。”
“我……我忘带钱包了。”她小声嗫嚅,心里感到忐忑不安。
小伙子看起来很生气。“什么,你以为你演过什么愚蠢的电视节目,就不必像我们一样带钱逛街?你以为你长得漂亮,想要什么我就会白送吗?”
“不,当然不是……”
“要么买杂志,要么走人,别浪费我的时间,我可不想别人拿我穷开心。”
“我没想拿你开心,真的。”
“两块九毛五。”他又重复一遍,同时伸出手。
简知道,只要自己把书还回去就万事大吉了。她却像中了魔似的,死死不肯放开那本书。辛迪?克劳馥看起来那么可爱,那么开心,那么自信。她是希望辛迪的自信能感染自己吗?她把手伸进风衣口袋,希望自己带着零钱。她很快从一个口袋摸到另一个口袋,不敢相信自己找到了什么。最后,她把手拿出来,看见手里满是沙沙作响、崭新的百元大钞。
柜台后面的男人吃惊地吹了声口哨。“喔,你抢银行啦?”他顿了一下又说,“你是印钞票的,还是别的什么?”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惊奇地盯着手中的钞票。
“不管怎样,我用不着这么多一百块的票子。我给你找开一百元,瞧,现在我都没零钱找给别人了。对了,你有多少张这样的大钞?”
简感到自己呼吸急促,几乎喘不上气。天啊!她用这两口袋的大钞干什么?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你没事吧,女士?”柜台后面的男人紧张地朝门口望去。“你不会生病了吧?”
“能借用一下你的卫生间吗?”
“卫生间不对外开放。”他一口回绝。
“求求你啦!”
一定是她绝望的语气打动了他,他抬起一只胳膊,指着右边说:“喏!我刚刚才把那里弄干净,千万别弄脏地板,明白吗?”
她很快找到了储物区里的小卫生间。房间狭小,里面有个旧马桶,脏兮兮的水槽上方挂着一面破镜子。它的四面都是壁柜,柜里塞满了装着物品的大箱小盒。门口放着个装了半桶水的水桶和一把挂在桶边摇摇欲坠的拖把。
她冲到水槽边,把杂志夹在胳膊下,拧开冰冷的水龙头,快速掬起凉水往脸上扑,感觉可以渐渐直起腰,不再眩晕。到底出了什么事?如果这是个噩梦——真是个噩梦的话——她也该醒了。
她紧抓水槽两边,撑住身体,在镜前慢慢仰起脸。镜里的女人也盯着她看,那是张完全陌生的面孔,连似曾相识都算不上。她仔细打量镜中人:苍白的皮肤,深棕色的眼睛,小巧微翘的鼻子,丰满的嘴唇,比双眸颜色略浅的棕色头发被梳成了马尾辫,用镶有宝石的发卡固定在脑后。不过,辫子早已松散,发卡也快掉下来了。她松开发卡,晃了晃脑袋,头发便似瀑布般柔顺地披在了肩上。
这是一张迷人的脸,她想,说得具体一点,像杂志封面上的超模辛迪?克劳馥一样明艳动人。按那个年轻小伙子的说法,她相当漂亮。实际上,她五官匀称,模样周正,完美的比例可谓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比他的评价更胜一筹。她估计自己的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很想知道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还是小。“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她对着镜中人小声说,镜中人似乎也屏住呼吸,“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镜中人答道。两个女人都低下头,盯着白瓷水槽上脏兮兮的洗手盆。
“噢!天哪!”她低声叫道,感到体内有个热泡泡炸开了。“千万别晕倒,”她哀求,“不管你是谁,千万别晕倒。”
然而,热浪继续漫过她的身体,掠过大腿和腹部,沿着胳膊和脖子,涌到了喉咙口。她感觉自己正在由里到外地融化,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她把更多的水扑到脸上,却未能让它平息下来。她开始撕扯风衣扣子,想把身体从衣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给自己更多的喘息空间。胳膊下的杂志滑落到地板上,她迅速弯下腰把它捡起来,起身时,无意中扯开了风衣扣子。
她深吸一口气。忽然,她怔住了。
她宛如一只木偶,被一股无名的力量牵引着,缓缓低下头。她看到自己的蓝色连衣裙上赫然沾满了血渍。其实,她刚才蹲在地上捡杂志时就看到了,却试图视而不见。
她倒抽一口冷气,低低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宛如一只小动物落入了陷阱。叫声很快转成呻吟,最后变成了尖叫。她听到脚步声和其他声音,感觉自己被人围住,淹没在人群里。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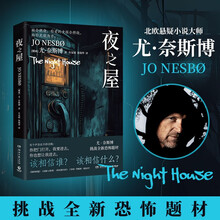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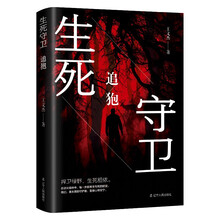




——美国《出版周刊》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现实的人物,菲尔丁敏锐地把握住了小说的节奏,读者感受到了心理悬疑,被引导着走向一个出人意料却又让人满意的结局。
——《图书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