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与伊丽莎白再次见面是当天下午。他看到她出现在花园里,和她的女伴们在晚餐前散步。“我要暂时离开宫廷,作为服丧,”他面色庄重,“我想我会回克佑花园的房子。您想见我的话随时可以去那里找我,我也可以来见您。”
她将手搭在他的臂上。“很好。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古怪,罗伯特?你并不悲伤吧?你并不在意吧?”他仔细打量她精致的面庞,仿佛她突然间变成了陌生人。“伊丽莎白,她是我十一年的妻子。我肯定会为她伤心。”
她撅了撅嘴。“但你曾经不顾一切地想要抛弃她。你还想为了我和她离婚。”
“是的,确实如此,我是想过这么做,但这样比离婚带来的丑闻要好。可是我半点也不希望她死去。”“人们都觉得她在过去的两年间简直生不如死,”她说,“每个人都说她生了可怕的病。”
他耸了耸肩。“谣言人人会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觉得她病了。她可以旅行;她可以骑马外出。她没有什么病,只是这两年她过得非常不开心;这都是我的错。”
她故意表现出自己的恼火。“看在诸位圣徒的份上,罗伯特!要不是她死了,你根本不会爱她!”她嘲弄着他,“你该不会突然发现她之前有这么多你忽略的优点吧?”“我爱过她,那时她还年轻,我也一样,”他激动地说,“她是我的初恋。她陪伴我走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给她带来的艰难与危险。等到您继承王位以后,我也恢复了从前的地位,而她还是没有抱怨过您一句。”“为什么她会抱怨我?”伊丽莎白大声问道,“她怎么敢抱怨我?”“她的嫉妒心很强,”他客观地说,“而且她知道自己有理由嫉妒。而且我对她不算很好,也不算慷慨。我想让她解除和我的婚姻关系,而且我对她很无情。”
“现在她死了,你觉得很对不起她,但如果她还在世,你还是会对她这么无情下去。”她嘲弄地对他说。
“是的,”他坦言道,“我觉得所有可悲的丈夫都会说同样的话--他们都知道其实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但今天的我感到自己很卑鄙。我确实很高兴自己能够恢复单身。但我并不希望她死去。她是多么无辜的人啊!没有人会希望她死去。”
“你自荐的本事可不太高明,”伊丽莎白狡黠地将话题转到他们的恋爱关系上,“听起来你根本就不像是一位好丈夫!”
罗伯特一时没有想到该如何回应她。他看向远处,越过河水看向库姆诺的方向,目光黯淡。“是的,”他说,“对她来说,我确实不是一位好丈夫,但上帝知道,她是男人所能拥有的最温柔、最优秀的妻子。”一旁等候的宫人发出轻微的骚乱声,一位穿着达德利家族制服的信使走进花园,站在一旁。达德利转身看到了来人,径直走了过去,伸手接过了他递上的信。
一旁的朝臣们看到达德利接过信,撕开火漆,再将信展开,又看到他读信的时候脸色变得惨白。伊丽莎白飞快地向他走去,其他人都为她让出一条路来。“怎么了?”她急切地问,“当心点!每个人都在看着你!”
“那儿将会召开公审,”他的嘴唇几乎没有动,声音低得像是呼吸,“每个人都说这并非意外。他们一致认为艾米死于谋杀。”
艾米死去的当天,托马斯·布朗特赶到了库姆诺庄园,逐个地调查了所有的仆从。然后他巨细靡遗地汇报给罗伯特,说他们都觉得艾米反复无常,在星期日的早上让所有人都遣去了市集,甚至包括她的同伴奥丁赛尔太太和佛斯特太太,虽然她们并不愿意去。
“没必要再提起这件事。”罗伯特·达德利回信给他,他不希望听到别人质疑他的妻子是否神智正常,虽然他知道自己迫使她陷入了绝望。
托马斯·布朗特顺从地没有再提起过艾米的古怪行为。但他提到女仆皮尔托太太说起过艾米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每天都会祈祷,希望自己死去。“也不要再提起这件事了,”罗伯特·达德利回信给他说,“不是要召开公审吗?阿宾登的人有能力处理这么敏感的事件吗?”
托马斯·布朗特从主人潦草的字迹中读出了他的焦虑,他答复说那里的人们对达德利家并没有偏见,而且佛斯特先生的名声也很好。不会有人直接下结论说这是谋杀;不过当然了,肯定每个人都这么想。一个女人不可能从只有六级的楼梯上跌下来摔死,也不可能摔下来之后兜帽整齐、衣裙平整。人们都认为是有人扭断了她的脖子,将她丢在地板上。所有事实都指向了谋杀。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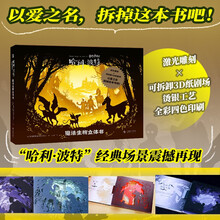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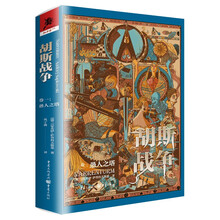







——《每日邮报》
“菲利帕·格里高利的讲述令人着迷,故事精彩绝伦。”
——《星期日电讯报》
“菲利帕·格里高利在撰写一个时代的传奇时总能扣人心弦,这令人惊叹。大量可信的细节与对话,仿佛让人亲临恐怖幽深的宫廷王室。她的书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可读性。”
——《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