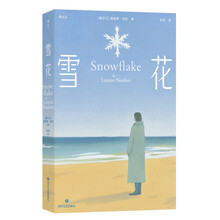黎明降临,安杰洛已醒来,他无忧无虑,默不作声。这地方夏天露水很少,加之有山冈保护,他身上没沾上露水。他抓了把欧石南擦了擦马,将鞍囊卷起来。
他走下小山谷。山谷里,鸟儿纷纷醒来。即使在夜色依然深浓的谷底,也并不凉爽。天空被急急冲出的朦胧晨光照亮。最后,一轮红日从森林中升起,但被高草般的乌云挤得扁扁的。
尽管安杰洛已感到异常闷热,但他仍想吃些热乎乎的东西。他走到一个大谷地,谷地这一边是他露宿的丘陵,另一边是一个更高更荒凉的山丘,在他前面二三法里,朝晖照在高原上,照得高大挺拔的橡树金光闪闪。他看见路边有一座小农庄,牧场上,一个穿红衬裙的妇女正在把夜里晾的衣服收起来。
他走过去。她胸衣外面穿一件粗布内衣,露着肩膀和胳膊,挺着晒成褐色的丰满的胸脯。“对不起,太太,”他说,“能不能给我喝点咖啡?我会付钱的。”她没立即回答,他意识到他刚才说的话过于文质彬彬。“说‘我付钱’也很蠢,”他心里想道。“我能给您咖啡,”她说,“跟我来。”她身材高大,但非常笨重,转起身来慢得像条船。“门在那边。”她指着树篱的尽头说。
厨房里只有一个老头,还有许多苍蝇。有一个矮墩墩的炉子,炉火烧得很旺,旁边有一小锅猪食,但在炉子上,咖啡壶送出浓郁的香味,以至于尽管屋里黑得像炭,安杰洛仍觉得它非常可爱。昨晚,他啃了些干面包,现已饥肠辘辘,即使是猪食,也令他馋涎欲滴。
他喝了碗咖啡。那女人矗立在他面前,他清楚地看见她那肉乎乎的有着一个个小窝的肩膀,甚至看见了紫黑色的乳头。她问他是不是坐办公室的。“当心,”安杰洛想道,“她后悔给我咖啡了。”“噢,不是!”他说(有意避免叫她“太太”),“我是在马赛做生意的。我去德龙,那里有我的客户,乘机散散心。”那女人的脸色变得更加和蔼可亲,尤其当他问她去巴农如何走的时候。“您吃个鸡蛋吧。”她说。她已把猪食锅往一边推了推,将平底锅放到火上。
他吃了一个鸡蛋和一块肥肉,另加四片雪白雪白的面包,他感到这些面包片轻如羽毛。此刻,那妇人慈母般地在他身边忙忙碌碌。她身上散发着汗臭味,她抬起胳膊,将发髻弄牢一些,于是露出了浓密的红棕色腋毛;他闻到了她的汗味,看到了她的腋毛,惊讶自己竟能忍受。她不让他付钱,见他坚持要付,甚至格格笑出声来,并且毫不客气地把钱包推开。安杰洛为自己的笨拙和可笑而感到十分尴尬:他真的很想付钱,这样,他走的时候,就可摆出一副冷漠的神态,他习惯用冷漠的神态来保护他的腼腆。他赶紧说了几句客气话,便把钱包放进了口袋。
那妇人给他指了路。那条路穿过山谷,爬上高地,消失在橡树林中。安杰洛穿过绿油油的牧场,在这小平原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很久。他刚才吃的食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感到回味无穷。最后,他叹了口气,便策马飞奔起来。
太阳高挂,天气炎热,但阳光并不强烈。那阳光很白很白,完全碎成了粉末状,仿佛在用稠厚的空气涂抹大地。安杰洛早已上了山坡,走在橡树林中。他沿着一条小路前进,路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马儿每走一步,都会扬起无数尘土,有如掀起滚滚浓烟,久久不落。在每一个拐弯处,透过干枯焦黄的林下灌木丛,可见他路过的痕迹依然停留在下面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树木没有带来丝毫凉意。相反,坚硬的橡树叶子反射着热和光。树林的阴影让人感到耀眼和闷热。
在被太阳烧得露出骨头的山坡上,几株白色的矢车菊在他经过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仿佛马蹄踩得周围金属般的大地微微颤动。除了这微弱的椎骨颤动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尽管厚厚的尘土使马蹄声减轻了,但那声音听上去依然响亮;周围一片寂静,那些默默无声的大树,仿佛成了幻景。马鞍滚烫滚烫。系马鞍的肚带一动一动,溅出汗水。那畜牲嗍着马嚼子,不时晃晃脑袋,轻咳一声。气温越来越高,仿佛是从无情地塞满了煤炭的炉子里升起来的,发出嗡嗡的声音。橡树嘎吱作响。那光秃秃干枯枯的灌木丛,犹如教堂的地板,淹没在白色的阳光中,那阳光虽不强烈,但已变成粉末状,刺得人睁不开眼,马走在这灌木丛中,慢慢地转动着长长的黑影。道路蜿蜒曲折,拐弯越来越急,从覆盖着白色地衣的古老岩石中间向上攀登,有时迎着太阳前进。这时,在白垩般的天空中,会出现一条异乎寻常的磷光闪闪的深渊,一股火炉中和发烧时才有的黏黏糊糊的气息从里面冒出来,可以看到那黏糊而浓稠的物质在颤动。一棵棵大树在这炫目的光线下消失,一片片橡树林被阳光淹没,只露出一丛丛土色的树叶,朦朦胧胧,看不清轮廓,几乎是透明的,炎热的气温突然将一个慢慢晃动的黏乎乎亮晶晶的旋流覆盖在它们身上。接着,小路向西拐弯,突然变得更加狭窄,成了羊肠小道,路旁挤满了光灿灿的树木,树干成了金晃晃的柱子,弯弯扭扭的树枝成了金光闪闪劈啪作响的干茎,静止不动的树叶也镀上了一层金色,犹如一面面镶嵌着纤纤金丝的小镜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