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画像
时间已是午夜了,我如果现在不开始把一些事记下来的话,我以后可能永远都没有勇气再把它写下来。一个晚上了,我一直坐在这里,强迫自己开始回忆,但是想得越多,越让我感到羞愧、恐惧和压力。
我此刻带着忏悔去寻找原因,寻找我为什么会如此粗暴地对待珍尼特·德·贝拉佳。实际上,我更希望向一位有同情心、有想象力的聆听者倾诉。这位聆听者应该是温柔的、应该是善解人意的。只要我自己不会太过不安或者泣不成声,我要向他诉说这段不幸的生活,包括每一个细节。
如果我能更坦率一点的话,我会承认,现在最令我懊悔的,不仅是自己的羞愧感,更是对珍尼特的伤害。我愚弄了自己,也愚弄了所有的朋友,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幸仍被他们称为朋友。多么可爱的人啊,他们过去经常到我的别墅来。现在必定都把我当做邪恶的、睚眦必报的小人了。唉!那伤害对一个人确实很严重。希望你们真能理解我!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属于这样一类人,有文化、有钱、有时间,正处中年,是一位有魅力、有风度的学者。我因慷慨大方而受到许多朋友的尊敬。我主要从事美术鉴赏工作,但我的欣赏口味与众不同。我们这类人单身汉非常多,又不想与紧紧围着自己的女人发生什么,对自己的肯定占据了生活中的大多数时间。当然也有不满、有挫折、有遗憾,但那毕竟很少。
我自己就不介绍太多了,坦率就行。你对我大致会有个判断。
如果你看完下面这个故事,你也许会说我自责的太过了,那个叫做格拉迪·帕森贝的女人才是最该谴责的。这一切,毕竟是她招来的。
本来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但那晚我送她回家了,她回到家后和我谈起了那个人、那件事。所以一切都发生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去年二月的事了。那天,我们在埃森顿别墅吃饭,那是一家可爱的、能看见锦丝公园一角的别墅,许多人都来了。
席间,一个人一直陪着我,她就是格拉迪·帕森贝。饭后,我当然要主动送她一程。到家后,她礼貌地让我进屋。我被人认为是个过于沉闷的人,与司机打了个招呼就进屋了。进屋后,她倒了两杯白兰地:“为我们回来一路顺风干一杯。”她这样说。
她是个矮个子女人,大概不足四英尺九英寸。我站她旁边真有滑稽之感,就像站在桌子上居高临下一样。这个寡妇面部松弛,毫无光彩,小脸上堆满了肥肉,挤得下巴、嘴、鼻子无处可藏。幸好她还有一张会讲话的嘴,时刻提醒着我,不然,我真会把她当成一条鳗鱼。
在客厅,我们谈了一会儿今天晚宴上发生的事,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想告辞。
“雷欧纳,坐下,”她说,“再来一杯。”
“我得走了。”
“坐下,先坐下,你该陪我喝一会儿吧,我还要再喝一杯。”
她身体微晃着走向壁橱,她把酒杯举在胸前,看着她又矮又宽的身材,让我有一个错觉:她膝盖以下胖的似乎连腿都看不见了。
“你笑什么呢,雷欧纳?”她侧过身来问,顺便为我倒了酒,因为一直注意我的动静,所以洒了几滴白兰地在杯子外。
“没,没笑什么。”我忙道。
“过来看看我最近的一幅画像吧。”她目光盯在那张挂在壁炉上的大画上。其实,刚进屋时我就看见了,我一直假装看不见。我想那肯定是一幅糟蹋艺术的作品,而且一定是由那位名震一时的画家约翰·约伊顿所作。因为在这幅画里用了圆滑的笔法,这让帕森贝太太在画像里看起来成了个有魅力、高挑的女人。
“画得很漂亮!”我言不由衷地道。
“我很高兴你喜欢它,它确实很漂亮。”
“太迷人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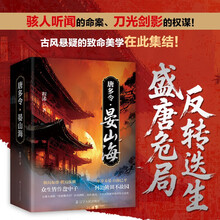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
在悬念片和恐怖片领域里,希区柯克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的影片就好比一本没有理论的电影教科书被传诵至今,成为心理恐怖影片的典范。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美国著名导演)
这个人去世了,但这位电影艺术家并没有死。他的电影连续不断地流传开来,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
——弗朗索瓦·特吕弗(法国"新浪潮"电影创始人)
如果把电影从我身上减去,那我就只剩下零了,如果希区柯克离开了电影,就不成其为真正的希区柯克了。
——黑泽明(日本电影大师)
我们在近十年间目睹了希区柯克成为一种理论现象——无穷无尽的书籍、论文、大学课程和研讨会,这是绝佳的"后现代"现象。
——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