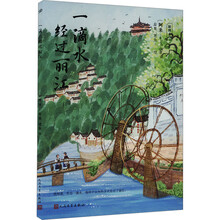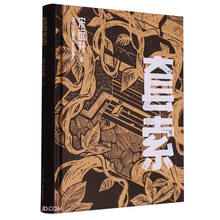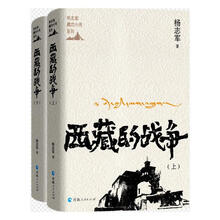册封大典接过金册的那一刻,意味着她正式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
献容仿佛听到身后人丛中,有个轻微的叹息声传来。
永康元年十一月初七,换算成公元纪年是300年12月4日。这个日子后来被载入史册,羊献容这个名字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入冬时节,一早天色便是阴霾晦暗,终日不见一丝阳光。
赵王府临时改成闺房的花楼内,即便白日也红烛高照。
天尚未大亮,一群命妇蜂拥而来,为彻夜未眠的献容洗漱打扮。
她如同一尊精致的布娃娃,随她们摆布,要坐要站,怎样都行。
捣鼓了许久,她里三层外三层套上了金线织就的团锦嫁衣,飞云髻上插着对称的两枚九重凤凰步摇,最后戴上璀璨的珠冠,一身行头重得能压垮她的脖子和身板。
如此雍容华贵的打扮,越发衬得肤如凝脂。
加上她本身的气质,真是端庄淑贤,仪态万方。
只是,肿胀的红眼圈无论施多少粉也遮盖不住。
吉时未到,献容枯坐在榻上,任由命妇们簇拥着调笑,一句话都懒得回。
直到春儿出现,她的麻木神情方才转变,首次行使皇后权力:让这帮无聊的长舌妇出去!
“父亲怎样了?”
待到屋中只剩下她与春儿,献容迫切追问。
从那夜羊府被抄,春儿代替她被抓,整整过去了一个月,两人才第一次见上。
春儿红肿着眼睛,低声道:“老爷已被接到太极殿等候嘉礼大典。”
献容松了一口气,旋即想到:“你们在刑部可有受委屈?”
春儿摇了摇头:“只听说二老爷一家被提出刑部,在别处受了刑,回来后倒是有太医来诊治,如今伤势该是无碍。其余人只是精神愁苦些,身上没吃什么苦头。”
二老爷指的是献容的叔叔,羊玄之亲弟。
献容没想明白为何叔叔会受刑,春儿也完全不知情。
见春儿仍在瑟瑟发抖,献容安慰她:“你放心,等今日典礼结束,羊家所有人就能回府了。”
春儿握住献容的手,急切说道:“小姐,我跟你去宫里!”
献容摇头:“你马上要跟羊军成亲了,何必——”
春儿匆匆打断她:“羊军跟我说,若我执意要跟着小姐,他便另娶他人。
他说,小姐的前途难料,他只愿过安生日子。”
她说了一半便哭起来,献容心疼地轻拍她肩头:“羊军说得没错。
那是个火坑,跳进去便一辈子出不来。此刻你还有的选择。”
春儿收住抽泣,鄙夷地“呸”了一声:“那个没担当的烂账男人,现在看清了他反而是好事。”
她看向献容,神色坚决,“我跟小姐一同长大,小姐无论去哪儿,我都要跟着。
那里纵然是个火坑,那也先烧死我,还能给小姐挡一挡。”
献容感动至极,话语未出泪先流。
突然“哐当”一声,门被用力推开,屏风后转出一个华丽丽的美男来。
二十出头的年纪,头戴亮闪闪的金冠,身穿一身亮泽的青黛色宽袍。
青黛色需用西域来的青金石磨粉染色,非富贵人家消费不起。
而况此人袍子上还以金线密密织就繁复的饕餮纹图案,边缘饰以齐整的玉石片。
通身的华丽装扮却没有土豪的俗气,加上不错的身材与颜值,难怪这位孔雀王走到哪里都有大票女粉丝狂热追捧。
不过献容可没时间欣赏时装秀,这个时候,成都王司马颖怎会来这里?献容急忙抹去眼泪,起身行礼。
司马颖指着垂头站在献容身后的春儿,得意地微笑:“你这位贴身丫鬟,可是由本王亲自从刑部大牢带出来送还给你的。”
献容吃了一惊。自被迎入这座花楼,她一直处于明里尊贵实为囚徒的状态。
她向身边人要求传话给司马伦:释放她的贴身丫鬟,她得有个信得过的人带入皇宫。
不料这么点小事居然劳动了司马颖。
献容嘴上说着感激的话,脑中却是飞速转动,揣测孔雀王的目的。
司马颖慵懒地挥手,让春儿出去,举手投足尽显明星范儿。
春儿暗暗着急,装作没看懂司马颖的手势。
献容还未成礼,哪有丈夫未见先见小叔的道理。
她若是离开,孤男寡女独处一室,即便两人是叔嫂关系,也于礼不合。
司马颖见春儿不肯离开,放下那张尽职的明星脸,上前揪住春儿的衣领往外拖。
这般蛮横的举动跟他平日的人设实在太不一致,春儿惊愕地被他像小鸡崽一般拎着推到门外。
献容气恼地质问:“成都王你这是做什么?”
司马颖将门重重合上,转头对她冷笑:“本王想与你说话,这贱婢居然敢拦着。
再不识相,别怪本王开杀戒!”
说这话时他眼里满是阴狠的戾气,说完后又恢复了时尚明星的人设,摆出姿态最美的造型。
这转换太自如了,若是让他那些粉丝们撞见,不知作何感想。
司马颖眼下跟赵王一路,不宜与他硬碰硬。
献容冷静下来,沉声问道:“成都王想与我说什么?”
司马颖用那双描了眼线的丹凤眼上下打量献容,啧啧叹气:“本王曾向羊府求亲,却无端遭羊侍郎拒绝,让本王至今耿耿于怀。”
献容脑中警铃大响,后退几步:“是献容粗鄙,不堪匹配成都王。”
“都说羊侍郎文韬武略,本王看来也不过尔尔。
若那时便将你嫁与我,羊侍郎何至今日的下场?”
司马颖向她步步逼近,身上香气逼人,丹凤眼愈发邪魅狷狂,“若只是嫁个寻常傻子倒也罢了,可如今,你那至尊之位能坐得了几天?真是可惜了这张漂亮脸蛋。”
献容被逼到角落退无可退,她摆出庄重的面容,厉声斥责道:“成都王慎言!如此大逆不道之语,请勿再提!”
“你以为你这个皇后能有多大分量?本王想见你就见,想说什么就说,又有哪个敢来阻拦?”
献容的斥责在司马颖眼中只是色厉内荏,他继续凑上前,一手撑在墙上摆出壁咚的造型,两眼肆无忌惮盯着献容精致的五官,拉扯出一个倾倒众生的笑容,“本王今日前来,是给你一条生路,走不走就看你了。”
献容不语,目光四下搜索。身边只有一盏落地青铜宫灯,几支红烛在烛台顶上燃着。
司马颖目光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逡巡,伸手捞起她佩戴的香囊,凑在鼻下深深一嗅。
这么暧昧的姿态与动作能让少女心爆棚的粉丝心醉,但献容满心只有惊骇,大叫:“殿下请自重!”
她的音量很大,足以让屋外层层叠叠的人听到,却无人入内阻拦。
献容明白了,司马颖定是获得了司马伦某种程度上的默许。
她这个皇后果然是人人都能欺负,还未成礼,便有人堂而皇之要给皇帝戴绿帽子。
献容不禁为尚未谋面的丈夫悲哀,更为自己悲哀。
司马颖浓烈的香气将献容笼罩住,赤裸裸地表达他的勾引意愿:“只要本王愿意,不知天下有多少女子迫不及待献身。本王能看上你,是你的幸运。本王这辈子已不可能娶你,但露水夫妻总能做得。”
献容气得浑身发抖。
这话真是无耻至极,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这是将她看作什么了!无论此人皮相有多好看,包装有多精美,献容此刻只想作呕,恨不得将这张自以为是个女人就会跪舔的俊脸踢爆。
司马颖却愣是看不出献容对他嫌恶到极点,凑得更近,目光迷离,用舌头舔自己的唇,舔得一片润泽光亮:“无论你在宫里发生何事,自有本王护得你周全。”
献容深呼吸几下,稳一稳情绪。
此刻不易动怒,必须探明他的真实目的。
她不露声色问道:“我是有夫之妇,更是皇后,成都王冒如此大风险,怕是不只想做露水夫妻吧?”
司马颖笑了,长眉一挑,回答得轻描淡写:“也不需要你做什么,帮本王传递些宫内消息即可。”
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他封地远,万一皇城有变故,他怕来不及反应。
她身为皇后,总比那些内侍宫女消息灵通。妙龄少女被逼嫁给又老又丑的傻子,定会春心难耐,他稍一诱惑便能上钩。
端的是好心思,可惜,献容从来都不是他的粉丝。
她狠了狠心,将身边那盏落地宫灯推倒。
红烛掉在地上,刚好落在她的拖地嫁衣上。
那些金丝和绸缎最经不得火,立即燃起火苗,延烧到地毯上。
司马颖被吓到了,急速跺脚退开好几步,此刻他已管不了摆造型,生怕火苗蹿到他自己身上。
献容不顾裙摆正冒着烟,向大门跑去,冲着屋外大喊:“快来人,走水啦!”
司马颖又气又恼,知道自己的算盘不能得逞,咬牙切齿手指献容:“你等着,迟早你会跪着来求本王!”
大门被打开,有人战战兢兢探了一眼,见到果真有火苗在献容身后蹿动,慌忙大喊:“快担水来!”
有这么多人在外守着,闺房内的小小火灾很快便被扑灭。
这消息后来在洛阳城中传开,好事之人都在咬耳朵:将要举办婚礼之时,婚服竟然起火,这可是有多不吉利。
日后当羊献容苦苦挣扎,几次三番生死悬于一线时,信奉谶纬者便摇头叹气,这皇后之位大凶,从她出嫁那天婚裙起火便已埋下预兆。
花轿在通往宫门的铜驼大街缓缓行进,周边的内侍宫女还有宿卫军队伍,前后望不见尽头。
这条大道乃曹魏时期修建,铺着方形地砖,路两旁有魏明帝所铸铜驼,这街名亦是由此而来。
道路两旁站满了人,踮着脚尖透过层层防卫看向硕大的十六抬大花轿。
洛阳城内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人们在窃窃私语:花季少女嫁给跟自己父亲一般年龄的人,这人还是个傻子,就算位于九五之尊,从婚姻角度来看,这女孩一生幸福就此陨没,真真可悲可叹。
一干吃瓜群众正在扼腕痛惜,一支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来,轿旁众人未及反应,那箭已穿入花轿。
抬轿的十六人受了惊吓,有几个腿软了,花桥倾斜着停了下来。
宿卫军校尉大喊一声,一队人朝着箭射来的方向追赶过去,剩余护卫将花轿团团围住。
校尉快步来到花轿前跪拜:“皇后娘娘可无恙?”
花轿内传来柔和的声音:“无事。”
厚重的帘子被掀开一角,皇后的贴身丫鬟探头出来,将一支箭交给校尉:“恐是小儿恶作剧,没有伤到人。将军请速进宫,莫要耽误良辰。”
那支箭不但去掉了箭头,还包了一层棉布,必无伤人之意。
校尉松了口气,看向箭射来的方向。
那是洛阳城内有名的酒肆,足有三层楼,射箭之人该是藏身在最高处。
能将一支无头箭准确射入花轿且计算好不伤到人,这份臂力与眼力绝不可能是小儿所为。
校尉提高警戒等待片刻,却是再无动静。
去追踪的那队人也回来了,说没有搜查到可疑之人。
不可再耽搁时辰,校尉挥手命令花轿继续前行。
花轿中,羊献容稳稳坐着,脸上被厚厚的脂粉遮盖,看不出任何表情。
春儿坐在一旁的小几凳上,实在按捺不住,轻声问道:“小姐,到底是什么?”
羊献容从宽大的衣袖下伸出手,摊开手掌。
掌心中是一块翠色布条,已经很陈旧了,染有锈迹一般的血痕。
春儿讶异:“这是……”
羊献容没有回答,只是攥紧拳头,将这块布条牢牢握住,仿佛溺水之人捞到了一块浮木。
想起刚刚受到小叔子的欺凌,她除了自残毫无办法。
若那时有他在,定然会拼死护她周全吧?她的手在微微颤抖,眼里泪光闪现,又即刻用指甲掐自己的掌肉。
疼痛让她甩开心头刚起的软弱。
那是她的仇人,绝不可以再有念想,纠缠不清。
眼里的泪光隐没不见,她又恢复成面无表情的布娃娃。
巳时三刻,迎亲队伍到达皇宫正门——阖闾门。
平日紧闭的正门如今严正敞开,献容被搀扶下花轿。
又换了一批内侍和宫女,改乘四人小轿经由正大门入内。
正中是条石铺就的御道,只有帝后有资格在上行走。
此刻御道铺起了红毯,小轿被抬上御道,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细碎的脚步声,更显庄严肃穆。
一路行进,到达前方高大的夯土台前,至此献容得下轿步行。
高大的阙楼耸立两旁,这是曹魏时期建成的铜雀台。
正面高台上耸立着一座恢宏的大殿,碧瓦金砖,光辉耀目。
这就是太极殿,整座宫城中最重要的正殿,重要的议事,登基与册封等大典皆在此完成。
殿外悬着诸多大件乐器,编钟、玉磬、笙、铙,叮叮咚咚响起,献容在庄严却单调的音乐声中被宫娥搀扶着一步步踏上高台。
她仰起头,透过眼前碍事的串串珠帘望去,太极殿气势恢宏,却是压抑迫人。
大殿前站了乌泱泱许多人,正中头戴皇冠的肥胖中年男子满脸欢笑,已迫不及待向她伸出手来。
这就是她的丈夫,号称天子,名义上掌握着这个庞大帝国。
这是她第一次见他,如此近距离,虽不能抬眼直视,却也瞧了个大概。
献容不由心下哀恸。
果真如传言所说,皇帝神情憨呆,行动迟缓。
四十多岁的人了,眼神仍如稚子般没半分遮掩。
献容眼光一直在搜索,直到看见一个高瘦的身影立于人群之中,方才将心落回原位。
她已有许多天没见过父亲,再次见到,不由哽咽。
父亲身穿朝拜吉服,脸颊消瘦了许多,胡须似是新修整过,双目深陷于眼窝中,疲倦而无神。
见到献容望过来,羊玄之不能有任何言语动作,只得勉强浮起一丝笑容。
眼里神情仿佛在宽慰献容,让她莫要担心自己。
皇帝司马衷身边始终跟着一个年近五旬的近臣,神情恭谨,时不时提点皇帝行止。
此人名叫嵇绍,官任侍中,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儿子。
嵇康因反对司马篡魏,被司马昭杀死,他的儿子嵇绍却忠心辅佐司马衷。
嵇绍主持大典,让皇帝与献容在几案后并排跪下,持香拜祭天地。
他们俩一跪下,身后那群人也一同跪下磕头。
皇帝在嵇绍小声提示下,磕磕巴巴念完了一篇册封诏书,将皇后金册与宝文交给献容。
接过金册的那一刻,意味着她正式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
献容仿佛听到身后人丛中,有个轻微的叹息声传来。
昏黄烛光下,阿乐如一摊烂泥倚在榻上,几案上丢着好几个空酒壶。
门“吱呀”一声推开,阿乐扭头见是阿曜,浑不在意,拿起酒壶昂头灌入嘴中。
阿曜将他手中酒壶夺去:“别喝了,有太多事情要做,你没时间在这里借酒消愁。”
阿乐摇晃着脑袋嘟哝:“还能做什么?都成定局了。”
阿曜沉着脸在几案对面坐下:“这世上哪有什么定局,我要救她出来。”
阿乐一惊,差点从榻上滑下来:“怎么救?那可是皇宫,咱们连宫门都混不进去!”
“知道蚍蜉撼大树吗?”
阿曜眼里闪着熠熠光芒,声音坚定,“就算力量再微小,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总有一天能让她重获自由。”
阿乐顿时清醒了许多,疑虑道:“你已经想好了要怎么做?”
“明日你秘密去一趟羊府。”
这么多酒居然没让阿乐头脑麻痹,他立时醒悟:“不错,她父亲一定会救她。”
猛地想到什么,他眼神闪烁,说得犹豫,“你说,她现在会不会……毕竟那是个皇帝……”
“她不会。”
阿曜知道他想说什么,语气极为肯定,“你别忘了她有多狡猾。”
阿乐看向窗外的夜色,目光变得温柔,嘴角浮起笑意:“是啊,那条滑不溜秋的小狐狸……”
阿乐沉入回忆浮想联翩,阿曜却在仔细打量他。
一道精光从阿曜眼中闪过,又很快隐没不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