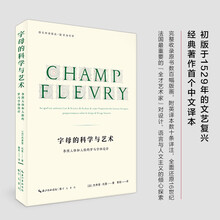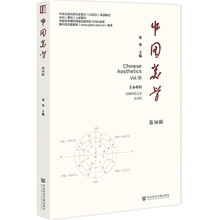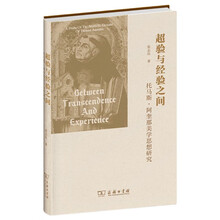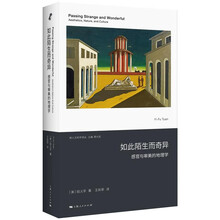五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美感与联想
美感与快感之外,还有一个更易惹误解的纠纷问题,就是美感与联想。
什么叫做联想呢?联想就是见到甲而想到乙。甲唤起乙的联想通常不外起于两种原因:或是甲和乙在性质上相类似,例如看到春光想起少年,看到菊花想到节士;或是甲和乙在经验上曾相接近,例如看到扇子想起萤火虫,走到赤壁想起曹孟德或苏东坡。类似联想和接近联想有时混在一起,牛希济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词就是好例。词中主人何以“记得绿罗裙”呢?因为罗裙和他的欢爱者相接近;他何以“处处怜芳草”呢?因为芳草和罗裙的颜色相类似。
意识在活动时就是联想在进行,所以我们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起联想。听到声音知道说话的是谁,见到一个词知道它的意义,都是起于联想作用。联想是以旧经验诊释新经验,如果没有它,知觉、记忆和想象都不能发生,因为它们都得根据过去的经验。从此可知联想为用之广。
联想有时可用意志控制,作文构思时或追忆一时记不起的过去经验时,都是勉强把联想挤到一条路上去走。但是在大多数情境之中,联想是自由的,无意的,飘忽不定的。听课读书时本想专心,而打球、散步、吃饭、邻家的猫儿种种意象总是不由你自主地闯进脑里来,失眠时越怕胡思乱想,越禁止不住胡思乱想。这种自由联想好比水流湿,火就燥,稍有勾搭,即被牵绊,未登九天,已人黄泉。比如我现在从“火”字出发,就想到红,石榴,家里的天井,浮山,雷鲤的诗,鲤鱼,孔夫子的儿子等等,这个联想线索前后相承,虽有关系可寻,但是这些关系都是偶然的。我的“火”字的联想线索如此,换一个人或是我自己在另一时境,“火”字的联想线索却另是一样。从此可知联想的散漫飘忽。
联想的性质如此。多数人觉得一件事物美时,都是因为它能唤起甜美的联想。
在“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的人看,芳草是很美的。颜色心理学中有许多同类的事实。许多人对于颜色都有所偏好,有人偏好红色,有人偏好青色,有人偏好白色。据一派心理学家说,这都是由于联想作用。例如红是火的颜色,所以看到红色可以使人觉得温暖;青是田园草木的颜色,所以看到青色可以使人想到乡村生活的安闲。许多小孩子和乡下人看画,都只是欢喜它的花红柳绿的颜色。有些人看画,欢喜它里面的故事,乡下人欢喜把孟姜女、薛仁贵、桃园三结义的图糊在壁上做装饰,并不是因为那些木板雕刻的图好看,是因为它们可以提起许多有趣故事的联想。这种脾气并不只是乡下人才有。我每次陪朋友们到画馆里去看画,见到他们所特别注意的第一是几张有声名的画,第二是有历史性的作品如耶稣临刑图、拿破仑结婚图之类,像伦勃朗所画的老太公、老太婆,和后期印象派的山水风景之类的作品,他们却不屑一顾。此外又有些人看画(和看一切其他艺术作品一样),偏重它所含的道德教训。道学先生看到裸体雕像或画像,都不免起若干嫌恶。记得詹姆士在他的某一部书里说过有一次见过一位老修道妇,站在一幅耶稣临刑图面前合掌仰视,悠然神往。旁边人问她那幅画何如,她回答说:“美极了,你看上帝是多么仁慈,让自己的儿子去牺牲,来赎人类的罪孽!”
在音乐方面,联想的势力更大。多数人在听音乐时,除了联想到许多美丽的意象之外,便别无所得。他们欢喜这个调子,因为它使他们想起清风明月;不欢喜那个调子,因为它唤醒他们以往的悲痛的记忆。锤子期何以负知音的雅名?因他听伯牙弹琴时,惊叹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李顽在胡茄声中听到什么?他听到的是“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白乐天在琵琶声中听到什么了他听到的是“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苏东坡怎样形容洞箫了他说:“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谷之潜蛟,泣孤舟之馨妇。”这些数不尽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多数人欣赏音乐,都是欣赏它所唤起的联想。
联想所伴的快感是不是美感呢?
历来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可分两派,一派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派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争辩就是在文艺思潮史中闹得很凶的形式和内容的争辩。依内容派说,文艺是表现情思的,所以文艺的价值要看它的情思内容如何而决定。第一流文艺作品都必有高深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这句话本来是不可辩驳的。但是侧重内容的人往往从这个基本原理抽出两个其他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题材的重要。所谓题材就是情节。他们以为有些情节能唤起美丽堂皇的联想,有些情节只能唤起丑陋凡庸的联想。比如做史诗和悲剧,只应采取英雄为主角,不应采取愚夫愚妇。第二个结论就是文艺应含有道德的教训。读者所生的联想既随作品内容为转移,则作者应设法把读者引到正经路上去,不要用淫秽卑鄙的情节摇动他的邪思。这些学说发源较早,它们的影响到现在还是很大。从前人所谓“思无邪”、“言之有物”、“文以载道”,现在人所谓“哲理诗”、“宗教艺术”、“革命文学”等等,都是侧重文艺的内容和文艺的无关美感的功效。
这种主张在近代颇受形式派的攻击,形式派的标语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们说,两个画家同用一个模特儿,所成的画价值有高低;两个文学家同用一个故事,所成的诗文意蕴有深浅。许多大学问家、大道德家都没有成为艺术家,许多艺术家并不是大学问家、大道德家。从此可知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如果你不是艺术家,纵有极好的内容,也不能产生好作品出来;反之,如果你是艺术家,极平庸的东西经过灵心妙运点铁成金之后,也可以成为极好的作品。印象派大师如莫奈、凡·高诸人不是往往在一张椅子或是几间破屋之中表现一个情深意永的世界出来么?这一派学说到近代才逐渐占势力。在文学方面的浪漫主义,在图画方面的印象主义,尤其是后期印象主义,在音乐方面的形式主义,都是看轻内容的。单拿图画来说,一般人看画,都先问里面画的是什么,是怎样的人物或是怎样的故事。这些东西在术语上叫做“表意的成分”。近代有许多画家就根本反对画中有任何“表意的成分”。看到一幅画,他们只注意它的颜色、线纹和阴影,不问它里面有什么意义或是什么故事。假如你看到这派的作品,你起初只望见许多颜色凑合在一起,须费过一番审视和猜度,才知道所画的是房子或是崖石。这一派人是最反对杂联想于美感的。
这两派的学说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究竟何去何从呢?我们否认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分开来讲(这个道理以后还要谈到),不过关于美感与联想这个问题,我们赞成形式派的主张。
就广义说,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艺术不能离开知觉和想象,就不能离开联想。但是我们通常所谓联想,是指由甲而乙,由乙而丙,辗转不止的乱想。就这个普通的意义说,联想是妨碍美感的。美感起于直觉,不带思考,联想却不免带有思考。在美感经验中我们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上面,联想则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不专一,使心思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物上面去。在审美时我看到芳草就一心一意地领略芳草的情趣;在联想时我看到芳草就想到罗裙,又想到穿罗裙的美人,既想到穿罗裙的美人,心思就已不复在芳草了。
联想大半是偶然的。比如说,一幅画的内容是“西湖秋月”,如果观者不聚精会神于画的本身而信任联想,则甲可以联想到雷峰塔,乙可以联想到往日同游西湖的美人,这些联想纵然有时能提高观者对于这幅画的好感,画本身的美却未必因此而增加,而画所引起的美感则反因精神涣散而减少。
知道这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许多通常被认为美感的经验其实并非美感了。假如你是武昌人,你也许特别欢喜崔颖的《黄鹤楼》诗;假如你是陶渊明的后裔,你也许特别欢喜《陶渊明集》;假如你是道德家,你也许特别欢喜《打鼓骂曹》的戏或是韩退之的《原道》;假如你是古董贩,你也许特别欢喜河南新出土的龟甲文或是敦煌石窟里面的壁画;假如你知道达·芬奇的声名大,你也许特别欢喜他的《蒙娜·丽莎》。这都是自然的倾向,但是这都不是美感,都是持实际人的态度,在艺术本身以外求它的价值。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