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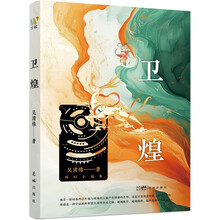

★雨果奖、星云奖、轨迹奖、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代表作;
★《星球大战》女导演维多利亚·马奥尼正在制作剧集;
★《你一生的故事》作者特德·姜和《雷切帝国》作者安•莱基推崇并追随的写作导师;
★吴岩、刘宇昆、奥普拉、约翰·格林、尼迪·奥科拉弗、N·K·杰米辛赞誉并推荐的作家;
★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深刻地以外星人的视角审视人类的局限性、矛盾与未来;
★或许人类只有在濒临灭绝之时,才会了解自己的高贵与渺小之处;
★一个关于基因工程、物种进化与人类未来的畅想;
★《启示人类进化新阶段的20部精华著作》之一;
★《莉莉丝的孩子》系列不仅长期作为小说和写作课程的主教材(康涅狄格大学、佛罗里达大学、杜克大学),还被用于人类学(MIT)、哲学(密歇根州立大学)、性别教育(布朗大学)和其它跨学科课程。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莉莉丝从长达几十年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自己身处外星人欧安卡利人的太空飞船上。欧安卡利人从因战争毁于一旦的地球上救下了所有幸存的人。他们想与人类做一笔“交易”,若人类同意,他们将会帮助人类重建地球,若人类不同意,他们将任由人类慢慢消亡。莉莉丝被选为领导者,去唤醒一批还在沉睡的人类同胞,开始“交易计划”……
她坐在床上,穿着衣服,等待着,疲惫不堪——是比身体上的疲惫更深沉、更空虚的精神倦怠。反正迟早会有人跟她说话。她等得太久。当一个声音叫她的名字时,她都快躺着睡着了。
“莉莉丝?”那种熟悉的、柔和的、雌雄莫辨的声音。
她深深地、疲倦地吸了一口气,“干什么?”她问道。但是当她说话的时候,她意识到这个声音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从上方传下来。她一骨碌坐起来,环顾四周。在一个角落里,她发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一名瘦瘦的长发男子。
那么,是因为他他们才给了她衣服?他似乎穿着一套类似的服装。当他俩都熟悉对方时,就把它给脱了?天哪!
“我想,”她轻轻地说,“你就是那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不是来伤害你的。”他说。
“不。你当然不是。”
“我是来带你出去的。”
她立刻站起来,使劲地瞪着他,希望光线能更明亮一点儿。
他是在开玩笑吗,或者是在嘲笑她?
“出去干吗?”
“教育,工作,开始崭新的生活。”
她向他走近了一步,然后停了下来。他让她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她无法强迫自己靠近他。“这不对劲,”她说,“你是谁?”
他略微动弹了一下:“我是什么?”
她跳了起来,因为她刚才差点儿就要这么说了。
“我不是个男人,”他说,“我也不是人类。”
她往后退到床边,但没有坐下:“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
“我就是来告诉你……来向你展示的。你现在想看看我吗?”
因为她就在看他——它,于是她皱了皱眉头:“这光线……”
“当你做好准备时,灯会调亮的。”
“你是……什么东西?从别的世界来的吗?”
“我来自其他一些世界。在讲英语的人中,只有几个从没想过自己落入了外星人手中,你是其中之一。”
“我其实想过,”莉莉丝低声说,“还想过我可能被关在监狱里,在疯人院里,在 FBI、CIA或克格勃的手里。只是,似乎不管怎样,其他的可能性都没这么荒谬。”
那个生物什么也没说。它一动不动地站在角落里。她从多次清醒中知道,直到她按照它的意愿行事,它才会再次与她谈话——直到她说她准备好要看它,然后,在更明亮的光线下,强迫她看一眼。这些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都非常善于等待。她让这一位等上了几分钟。它不仅仅是沉默,而是连一块肌肉都不动。是纪律使然还是生理原因?
她并不害怕。早在被捕之前,她就克服了因被“丑陋”的面孔吓到而产生的恐惧。未知吓到了她,关她的笼子吓到了她。她宁愿和各种丑陋面孔朝夕相处,也不愿意被困在笼子里。
“好吧,”她说,“让我看看。”
如她所想的那样,灯光亮了起来,那似乎高瘦的类人生物,它没有鼻子——没有鼻梁,也没有鼻孔——只有扁平的灰色皮肤。它全身都是灰色的,皮肤是浅灰色的,头上的毛发是深一些的灰色。毛发顺着它的眼睛、耳朵和喉咙周围长出来。那么多毛发盖住了眼睛,这让她想不明白这个生物是怎么看东西的。长长的、浓密的耳毛似乎从耳朵里和耳朵周围生长出来,往上和眼部的毛发接在一起,往下和往后与头发连成一片。喉部的一团毛发似乎在轻微摆动,她想那可能是这个生物呼吸的地方——一种天然的气管造口术。
莉莉丝瞥了一眼那个人形体,想知道它到底有多像人。“我无意冒犯,”她说,“但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假设我一定具有某种你熟悉的性别,这是有问题的。”它说,“但碰巧的是,我是位男性。”
很好。“它”又可以变成“他”了。少了些尴尬。
“你应该注意到,”他说,“你看到的像是头发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头发,我没有头发。这似乎会让人类感到迷惑不解。”
“什么?”
“你走近点看看。”
她不想离他再近哪怕一丝一毫。她之前不知道是什么阻止她上前,现在她确信这是因为他是个异类,他的异乎寻常,他完全就不是地球生物。她发现自己仍然无法再向他迈出一步。
“天哪!”她喃喃道。毛发动了——管它到底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些似乎在朝她飘过来,就像给风吹来一样——尽管房间里没有空气流动。
她皱起眉头,紧张地观察着,想搞明白。然后,突然间她就明白过来。她退避着,绕过床夺路而逃,直退到远处的墙边。她不能再离得更远了,就靠墙站着,瞪着他。美杜莎。
那些“毛发”各自蠕动着,如同一窝受惊的蛇,四散逃窜。她厌恶地把脸转向墙壁。
“它们不是独立的动物,”他说,“它们是感觉器官,并不危险,跟你的鼻子或眼睛一样。它们对我的意愿、情感或外界刺激做出反应是很自然的。我们的身体上同样分布着这种感觉器官,我们需要它们,就像你需要耳朵、鼻子和眼睛一样。”
“可是……”她再次面向他,无法相信。为什么他需要这种像触须一样的东西来完善他的感官呢?
“如果可以的话,”他说,“走近点,再看看我。我曾让你们人类相信过他们在我头上看到的是类似人类的感觉器官,当他们意识到自己错了的时候,就会冲我发火。”
“我做不到!”她嘀咕道,尽管现在她挺想这么做。她会不会真错了,被自己的眼睛欺骗了?
“你能的,”他说,“我的感觉器官对你来说并不危险。你会习惯它们的。”
“不!”
触须十分灵活。在她的喊声中,有的触须延长了向她伸过来。她想到巨大的、缓慢蠕动的、垂死的夜行爬虫,沿着雨后的人行道蜿蜒而行。她又想到长着触手的小型海蛞蝓——裸鳃蛞蝓——难以置信地长到了人类的大小和形状,很恶心,可它们似乎比某些人更像人类。她想要听他说话,他却沉默不语,完全不像个人类。
她咽了口唾沫:“听着,别对我沉默。说话!”
“嗯?”
“你的英语为什么说得这么好?不管怎样,你至少应该有点儿非同寻常的口音。”
“和你差不多的人教会了我。我会说几种人类语言,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你们这儿还有多少人?这是在哪里?”
“这是我的家。你可以把它称为一艘船——与你们人类建造的飞船相比,这是一艘太空巨舰。我无法解释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称之为‘船’,你会容易理解。它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略微超出了月球轨道。至于这里有多少人,你们所有战争中的幸存者都在。我们尽可能多地收集他们……